狱的监守人(原译称为“十一名裁判官的仆从”,中译简称“监守”。)
伊奇 斐多啊,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服毒那天,你和他在一起吗?还是说,那天的事是你听别人讲的?
斐多 我和他一起在监狱里,伊奇。
伊奇 那么我问你,他临死说了些什么话?他是怎么死的?我很想听听。因为近来弗里乌斯(Phlius)人一个都不到雅典去了,弗里乌斯也好久没外地人来。那天的事没人讲得清楚,只说他喝了毒药死了。所以我们对详细情况没法儿知道了。
斐多 你连审判都没听说过?审判怎么进行的也没听说过?
伊奇 听说过。有人讲了。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巳经判处了死刑,还迟迟没有处死。斐多,这是什么缘故呀?
斐多 伊奇,这是偶然。雅典人送往得洛斯(Delos)(1)的船,恰好在他受审的头天“船尾加冕”(2)。
伊奇 什么船呀?
斐多 据雅典人传说,从前悌修斯(Theseus)(3)等一伙十四个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去的时候,就乘的这条船。他救了自己,也救了同伙的性命。据这个传说,当时雅典人对阿波罗发誓许愿,假如这伙童男女能保得性命,雅典人年年要派送使者到得洛斯去朝圣。从那个时期直到今天,他们年年去朝圣。按雅典的法律,出使得洛斯的船往返期间,城里该是圣洁的,不得处决死囚。这段时期有时很长,因为船会碰到逆风。阿波罗的祭司为船尾加冕,就是出使的船启程了。我不是说吗,那只船是苏格拉底受审的前一天加冕的,所以苏格拉底判了死刑以后,在监狱里还待了很久才处死。
伊奇 斐多,他临死是怎么个样儿?说了些什么话?干了些什么事? 个朋友和他在一起?监狱的监管人让他的朋友们进监狱吗?还是他孤单单地死了?
斐多 不孤单,有几个朋友和他在一起,好几个呢。
伊奇 你要是不太忙,请把当时的情况给我讲讲,讲得越仔细越好。
斐多 我这会儿没事,我会尽量仔仔细细地讲给你听。因为,不论是我自己讲苏格拉底,或是听别人讲,借此能想起他,总是我莫大的快乐。
伊奇 好啊,斐多,我的心思正和你的一样,希望你尽量仔仔细细地讲。
斐多 我呀,陪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感情很特殊。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要死了,我心里准是悲伤的,可是我并哪几不。因为瞧他的气度,听他的说话,他是毫无畏惧、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所以我想,他即使是到亡灵居住的那边去,一路上也会有天神呵护;假如那种地方也有谁会觉得好,那么他到了那里,他的境遇一定是好的。就为这个缘故,我并不像到了丧事场合、自然而然地满怀悲悯,我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我也并不能感到往常听他谈论哲学的快乐,而我们那天却是在谈论哲学。我的心情非常奇怪。我想到苏格拉底一会儿就要死了,我感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喜交集。当时我们在场的一伙人心情都很相像。我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尤其是阿波(Apollodorus)——(尔认识他,也知道他的性格。
伊奇 我当然知道。
斐多 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也和别人一样,都很激动。
伊奇 斐多,当时有哪些人在场?(4)
斐多 有几个雅典本地人。阿波之外,有克里(Grito)和他的儿子以及贺莫(Hermogenes)、艾匹(Epiganes)、依思(Aeschines )和安悌(Antisthenes )。皮阿尼亚(Paeania)区的泽西(Ctesippus )也在,还有梅内(Menexenus)和另外几个雅典人。不过柏拉图(Plato)没在,我想他是病了。
伊奇 有外地人吗?
斐多 有底比斯(Thebes)人西米(Simmias)、齐贝(Cebes)和斐东(Phaedonides);麦加拉(Megara)的尤克(Euclides)和式松(Terpsion)
伊奇 嘿?阿里(Aristippus)和克琉(Cleombrotus)没在那儿?
斐多 他们没在。听说他们俩当时在爱琴岛(Aegina)。
伊奇 还有别人吗?
斐多 我想差不多全了。
伊奇 好吧,你们谈论些什么呢?
斐多 我且给你从头讲起。我和他们一伙前些日子就经常去看望苏格拉底。监狱附近就是他受审的法庭。天一亮我们就在那儿聚会。监狱开门是不早的。我们说着话儿等开门。门开了我们就进监狱去看苏格拉底,大半天的时光都和他在一起。末后那天的早晨,我们集合得特早,因为前一天黄昏,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听说开往得洛斯的船回来了。所以我们约定大清早就到老地方去会合。我们到了监狱,往常应门的监守出来拦住我们,叫我们等等,等他来叫我们。他说:“因为这时候那十一位裁判官正为苏格拉底卸下锁链,并指示今天怎么处他死刑。”过了一会,监守回来叫我们进去。我们进了监狱,看见苏格拉底刚脱掉锁链。任娣(Xanthippe(5),你知道她的,她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抱着他的小儿子。她见了我们,就像女人惯常的那样,哭喊着说:“啊,苏格拉底,这是你和你朋友们交谈的末一遭了呀!”苏格拉底看了克里一眼说:“克里,叫人来送她回家。”她捶胸哭喊着给克里家的几个佣人送走了。苏格拉底从他的卧铺上坐起来,蜷起一条腿,用手抚摩着,一面说:“我的朋友啊,我们所谓愉快,真是件怪东西!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看上来,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谁也不会同时候和这两个一起相逢的。可是谁要是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就势必碰到那一个。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我想啊,假如伊索(Aesop)(6)想到了这一对,准会编出一篇寓言来,说天神设法调解双方的争执却没有办法,就把两个脑袋拴在一起,所以这个来了,那个跟脚也到。我现在正是这个情况。我这条腿给锁链锁得好痛,现在痛苦走了,愉快跟着就来了。”
讲到这里,齐贝插嘴说:“嗨,苏格拉底,我真高兴,你这话提醒了我。你把伊索寓言翻成了诗,又作诗颂扬阿波罗,许多人问起这事呢。前天,艾凡(Evenus(7)就问我说,你从来没作过诗,怎么进了监狱却作起这些诗来了。他一定还要问呢。等他再问,假如你愿意让我替你回答,你就教我怎么回答。”
苏格拉底说:“齐贝,你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我作这几首诗,并不想和他或他的诗媲美,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试验一下我做的有些梦是什么意思。我屡次在梦里听到一个督促我的声音,叫我作作诗,和文艺女神结交。我生怕疏忽了自己的责任,想知道个究竟。我且说说我的梦吧。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梦是各式各样的,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它说‘苏格拉底啊,创作音乐!培育音乐!’我以前呢,以为这是督促我、鼓励我钻研哲学。我生平追随的就是哲学,而哲学是最高尚、最优美的音乐。梦督促我的事,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就好比看赛跑的人叫参赛的人加劲儿!加劲儿!可是现在呢,我巳经判了罪,因为节日而缓刑,正好有一段闲余的时间。我想,人家通常把诗称为音乐,说不定梦里一次次叫我创作音乐就指作诗,那么我不该违抗,应该听命。我是就要走的人了,该听从梦的吩咐,作几首诗尽尽责任,求个心安。所以我就作了一首赞美诗,歌颂这个节期的神(8)。然后我想,一个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或创造者(9)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我不会创造故事,就把现成熟悉的伊索寓言改成诗。齐贝,你把这话告诉艾凡吧,说我和他告别了;并且劝告他,假如他是个聪明人,尽快跟我走吧。看来我今天得走了,因为这是雅典人的命令。”
西米说:“什么话呀!苏格拉底,给艾凡捎这种话!我和他很熟,据我对他的认识,我敢说,他除非万不得巳,绝不会听你的劝告。”
苏格拉底说:“为什么呢?艾凡不是哲学家吗?”
西米说:“我想他是的。”
“那么,艾凡会听从我的劝告。任何人如果对哲学真有爱好,都会听取我的劝告。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不该自杀。据说,这是不容许的。”苏格拉底一面说话,一面把两脚垂放下地。他从这时起,直到我们谈话结束,始终这么坐着。
伊奇 斐多啊,苏格拉底在监狱里服毒那天,你和他在一起吗?还是说,那天的事是你听别人讲的?
斐多 我和他一起在监狱里,伊奇。
伊奇 那么我问你,他临死说了些什么话?他是怎么死的?我很想听听。因为近来弗里乌斯(Phlius)人一个都不到雅典去了,弗里乌斯也好久没外地人来。那天的事没人讲得清楚,只说他喝了毒药死了。所以我们对详细情况没法儿知道了。
斐多 你连审判都没听说过?审判怎么进行的也没听说过?
伊奇 听说过。有人讲了。不过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他巳经判处了死刑,还迟迟没有处死。斐多,这是什么缘故呀?
斐多 伊奇,这是偶然。雅典人送往得洛斯(Delos)(1)的船,恰好在他受审的头天“船尾加冕”(2)。
伊奇 什么船呀?
斐多 据雅典人传说,从前悌修斯(Theseus)(3)等一伙十四个童男童女到克里特去的时候,就乘的这条船。他救了自己,也救了同伙的性命。据这个传说,当时雅典人对阿波罗发誓许愿,假如这伙童男女能保得性命,雅典人年年要派送使者到得洛斯去朝圣。从那个时期直到今天,他们年年去朝圣。按雅典的法律,出使得洛斯的船往返期间,城里该是圣洁的,不得处决死囚。这段时期有时很长,因为船会碰到逆风。阿波罗的祭司为船尾加冕,就是出使的船启程了。我不是说吗,那只船是苏格拉底受审的前一天加冕的,所以苏格拉底判了死刑以后,在监狱里还待了很久才处死。
伊奇 斐多,他临死是怎么个样儿?说了些什么话?干了些什么事? 个朋友和他在一起?监狱的监管人让他的朋友们进监狱吗?还是他孤单单地死了?
斐多 不孤单,有几个朋友和他在一起,好几个呢。
伊奇 你要是不太忙,请把当时的情况给我讲讲,讲得越仔细越好。
斐多 我这会儿没事,我会尽量仔仔细细地讲给你听。因为,不论是我自己讲苏格拉底,或是听别人讲,借此能想起他,总是我莫大的快乐。
伊奇 好啊,斐多,我的心思正和你的一样,希望你尽量仔仔细细地讲。
斐多 我呀,陪他在监狱里的时候,感情很特殊。如果我看到一个朋友要死了,我心里准是悲伤的,可是我并哪几不。因为瞧他的气度,听他的说话,他是毫无畏惧、而且心情高尚地在等死,我觉得他是快乐的。所以我想,他即使是到亡灵居住的那边去,一路上也会有天神呵护;假如那种地方也有谁会觉得好,那么他到了那里,他的境遇一定是好的。就为这个缘故,我并不像到了丧事场合、自然而然地满怀悲悯,我没有这种感觉。不过我也并不能感到往常听他谈论哲学的快乐,而我们那天却是在谈论哲学。我的心情非常奇怪。我想到苏格拉底一会儿就要死了,我感到的是一种不同寻常的悲喜交集。当时我们在场的一伙人心情都很相像。我们一会儿笑,一会儿哭,尤其是阿波(Apollodorus)——(尔认识他,也知道他的性格。
伊奇 我当然知道。
斐多 他简直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也和别人一样,都很激动。
伊奇 斐多,当时有哪些人在场?(4)
斐多 有几个雅典本地人。阿波之外,有克里(Grito)和他的儿子以及贺莫(Hermogenes)、艾匹(Epiganes)、依思(Aeschines )和安悌(Antisthenes )。皮阿尼亚(Paeania)区的泽西(Ctesippus )也在,还有梅内(Menexenus)和另外几个雅典人。不过柏拉图(Plato)没在,我想他是病了。
伊奇 有外地人吗?
斐多 有底比斯(Thebes)人西米(Simmias)、齐贝(Cebes)和斐东(Phaedonides);麦加拉(Megara)的尤克(Euclides)和式松(Terpsion)
伊奇 嘿?阿里(Aristippus)和克琉(Cleombrotus)没在那儿?
斐多 他们没在。听说他们俩当时在爱琴岛(Aegina)。
伊奇 还有别人吗?
斐多 我想差不多全了。
伊奇 好吧,你们谈论些什么呢?
斐多 我且给你从头讲起。我和他们一伙前些日子就经常去看望苏格拉底。监狱附近就是他受审的法庭。天一亮我们就在那儿聚会。监狱开门是不早的。我们说着话儿等开门。门开了我们就进监狱去看苏格拉底,大半天的时光都和他在一起。末后那天的早晨,我们集合得特早,因为前一天黄昏,我们离开监狱的时候,听说开往得洛斯的船回来了。所以我们约定大清早就到老地方去会合。我们到了监狱,往常应门的监守出来拦住我们,叫我们等等,等他来叫我们。他说:“因为这时候那十一位裁判官正为苏格拉底卸下锁链,并指示今天怎么处他死刑。”过了一会,监守回来叫我们进去。我们进了监狱,看见苏格拉底刚脱掉锁链。任娣(Xanthippe(5),你知道她的,她正坐在苏格拉底身边,抱着他的小儿子。她见了我们,就像女人惯常的那样,哭喊着说:“啊,苏格拉底,这是你和你朋友们交谈的末一遭了呀!”苏格拉底看了克里一眼说:“克里,叫人来送她回家。”她捶胸哭喊着给克里家的几个佣人送走了。苏格拉底从他的卧铺上坐起来,蜷起一条腿,用手抚摩着,一面说:“我的朋友啊,我们所谓愉快,真是件怪东西!愉快总莫名其妙地和痛苦联在一起。看上来,愉快和痛苦好像是一对冤家,谁也不会同时候和这两个一起相逢的。可是谁要是追求这一个而追到了,就势必碰到那一个。愉快和痛苦好像是同一个脑袋下面连生的两个身体。我想啊,假如伊索(Aesop)(6)想到了这一对,准会编出一篇寓言来,说天神设法调解双方的争执却没有办法,就把两个脑袋拴在一起,所以这个来了,那个跟脚也到。我现在正是这个情况。我这条腿给锁链锁得好痛,现在痛苦走了,愉快跟着就来了。”
讲到这里,齐贝插嘴说:“嗨,苏格拉底,我真高兴,你这话提醒了我。你把伊索寓言翻成了诗,又作诗颂扬阿波罗,许多人问起这事呢。前天,艾凡(Evenus(7)就问我说,你从来没作过诗,怎么进了监狱却作起这些诗来了。他一定还要问呢。等他再问,假如你愿意让我替你回答,你就教我怎么回答。”
苏格拉底说:“齐贝,你就把真实情况告诉他。我作这几首诗,并不想和他或他的诗媲美,因为我知道这是不容易的。我只是想试验一下我做的有些梦是什么意思。我屡次在梦里听到一个督促我的声音,叫我作作诗,和文艺女神结交。我生怕疏忽了自己的责任,想知道个究竟。我且说说我的梦吧。我过去常做同一个梦。梦是各式各样的,可是说的总是同一句话。它说‘苏格拉底啊,创作音乐!培育音乐!’我以前呢,以为这是督促我、鼓励我钻研哲学。我生平追随的就是哲学,而哲学是最高尚、最优美的音乐。梦督促我的事,正是我一直在做的事,就好比看赛跑的人叫参赛的人加劲儿!加劲儿!可是现在呢,我巳经判了罪,因为节日而缓刑,正好有一段闲余的时间。我想,人家通常把诗称为音乐,说不定梦里一次次叫我创作音乐就指作诗,那么我不该违抗,应该听命。我是就要走的人了,该听从梦的吩咐,作几首诗尽尽责任,求个心安。所以我就作了一首赞美诗,歌颂这个节期的神(8)。然后我想,一个诗人,如果是真的诗人或创造者(9)他不仅把文字造成诗句,还该创造故事。我不会创造故事,就把现成熟悉的伊索寓言改成诗。齐贝,你把这话告诉艾凡吧,说我和他告别了;并且劝告他,假如他是个聪明人,尽快跟我走吧。看来我今天得走了,因为这是雅典人的命令。”
西米说:“什么话呀!苏格拉底,给艾凡捎这种话!我和他很熟,据我对他的认识,我敢说,他除非万不得巳,绝不会听你的劝告。”
苏格拉底说:“为什么呢?艾凡不是哲学家吗?”
西米说:“我想他是的。”
“那么,艾凡会听从我的劝告。任何人如果对哲学真有爱好,都会听取我的劝告。不过,话又说回来,他不该自杀。据说,这是不容许的。”苏格拉底一面说话,一面把两脚垂放下地。他从这时起,直到我们谈话结束,始终这么坐着。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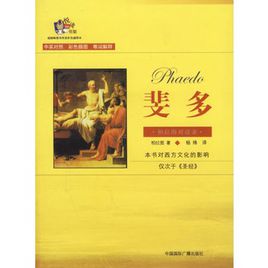 作者:柏拉图(古希腊)
作者:柏拉图(古希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