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之末流,病莫急於“好大喜功”。好大则不切实际,偏激者夸诞,拟想者附会,美之曰“无往而不圆融”。喜功则不择手段,淫猥也可,卑劣也可,美之曰“无事而非方便”。圆融方便,昔尝深信不疑,且以此为佛教独得之秘也。七七军兴,避难来巴之缟云山。间与师友谈,辄深感於中国佛教之信者众,而卒无以纾国族之急,圣教之危,吾人殆有所未尽乎!乃稍稍反而责诸己。
二十七年冬,梁漱溟氏来山,自述其学佛中止之机曰∶“此时、此地、此人”。吾闻而思之,深觉不特梁氏之为然,宋明理学之出佛归儒,亦未尝不缘此一念也。佛教之遍十方界,尽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广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任重致远之行,而竞为“三生取办”,“一生圆证”,“即身成佛”之谈,事大而急功,无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吾心疑甚,殊不安。时治唯识学,探其源於《阿含经》,读得“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句,有所入。释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详此土,立三世而重现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释尊之本教,初不与末流之圆融者同,动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吾为之喜极而泪。
二十九年,游黔之诛垣,张力群氏时相过从。时太虚大师访问海南佛教国,以评王公度之“印度信佛而亡”,主“印度以不信佛而亡”,与海南之同情王氏者辩。张氏闻之,举以相商曰∶“为印度信佛而亡之说者,昧於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强,固不可。然谓印度以不信佛而亡,疑亦有所未尽。夫印度佛教之流行,历千六百年,时不为不久;遍及五印,信者不为不众,而末流所趋,何以日见衰竭?其或印度佛教之兴,有其可兴之道;佛教之衰灭,末流伪杂有以致之乎”?余不知所以应,姑答以“容考之”。释慧松归自海南,道出诛垣,与之作三日谈。慧师於“无往不圆融”、“无事非方便”,攻难甚苦。盖病其流风之杂滥,梵佛一体而失佛教之真也。
自尔以来,为学之方针日定,深信佛教於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链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来,动机之所出,於身心国家实益之所在,不为华饰之辩论所蒙,愿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
治印度佛教不易,取材於 译之经论,古德之传记,支离破碎甚,苦无严明条贯之体系,足资依循。察印度佛教之流变,自其事理之特徵,约为五阶而束之为三时。三时之证有四∶
一、经典之暗示∶声闻藏不判教。性空大乘经判小、大二教,以空为究竟说。真常与唯心之大乘经判三教∶初则详无常、实有之声闻行;次则说性空、幻有之菩萨行;後则说真常、妙有(不空)之如来行,以空为不了义。昔以一切经为佛说,则三者为如来说教之次第;今以历史印证之,则印度佛教发展之遗痕也。
二、察学者之从违∶凡信声闻藏者,或有不信大乘经为佛说;信大乘经者,必信声闻藏。信声闻及大乘性空经者,多有拒斥“真常论”与“唯心论”;信“真常唯心论”者,必以空为佛说。此以後承於前故必信;前者不详後,见後说之有异於前,故或破之。
三、符古德之判教∶印华古德之约理以判教者,并与此三期之次第合。尝为“三期佛教与判教”一文,揭之於海潮音(见二十二卷十二期)。
四、合传译之次第∶“经”则自汉迄东晋之末,以《般若》、《法华》(以《法华》为真常论,隋智者牵合於《涅盘》而後盛说之。前此之宋慧观、梁法云辈,不闻此说)、《十地》、《净名》、《首楞严三昧经》等为盛,并性空之经也。东晋末,觉贤译《如来藏经》;北凉昙无谶译《涅盘》、《金光明》、《大集》;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深密》、《法鼓》、《胜 经》,真常与唯心之经,东来乃日多。以言“论”,西晋竺法护创译龙树之性空论。北魏,宋、齐、梁间乃有弥勒、无著、坚慧等真常与唯心论。传说之《大乘起信论》,则谓出於陈真谛之译。
印度之佛教,初则无常论盛行,中则性空论,後乃有真常论盛行,参证史迹有如此,不可以意为出入也。印度佛教之仅存者,多断片,支离破碎甚,吾人实无如之何。欲为印度佛教史之叙述,惟有积此支离破碎之片断,以进窥错综复杂之流变。离此,实无适当之途径可循。
印度佛教发展之全貌,时贤虽或有异说,而实大体从同。即此以探其宗本,自流变以批判其臧否,则以佛教者行解之庞杂,势必纷呶不已。海南佛教者,以声闻行为究竟;藏卫来者,以“无上瑜伽”为特高。中国佛教之传统学者,以“真常论”为根基(“三论”、“天台”融真常於性空,“唯识”则隐常於真常。“贤”、“禅”、“密”为彻底之真常者。“净”则随学者所学而出入之)。 不暇辩诘,请直述研求之所见∶“佛教乃内本释尊之特见,外冶印度文明以创立者”。故流变之印度佛教,有反释尊之特见者,辟之可也。非适应无以生存,其因地、因时、因人而间不同者,事之不可免,且毋宁视为当然。以是,海南佛教者忽视佛教正常之开显,方便之适应,指责一切大乘道,非佛意也。然“方便”云云,或为正常之适应,或为畸形之发展,或为毒素之羼入,必严为料简,正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滥之。
释尊之特见,标“缘起无我说”,反吠陀之常我论而兴。後期之佛教,日倾向於“真常、唯心”,与常我论合流。直就其理论观之,虽融三明之哲理,未见其大失;即绳墨之,亦见理未彻,姑为汲引婆罗门(印度教)而谈,不得解脱而已。若即理论之圆融方便而见之於事行,则印度“真常论”者之末流,融神秘、欲乐而成邪正杂滥之梵佛一体。在中国者,末流为三教同源论,冥镪祀祖,扶鸾降神等,无不渗杂於其间。“真常唯心论”,即佛教之梵化,设以此为究竟,正不知以何为释尊之特见也!
印度之佛教,自以释尊之本教为淳朴、深简、平实。然适应时代之声闻行,无以应世求,应学释尊本行之菩萨道。中期佛教之缘起性空(即缘起无我之深化),虽已启梵化之机,而意象多允当。龙树集其成,其说菩萨也∶1.三乘同入无馀涅盘而发菩提心,其精神为“忘己为人”。2.抑他力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为“尽其在我”。3.三阿僧只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致远”。菩萨之真精神可学,略可於此见之。龙树有革新僧团之志,事未成而可师。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後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
中国佛教为“圆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神秘”、“欲乐”之说,自西而东,又日有泛滥之势。乃综合所知,编《印度之佛教》为诸生讲之。僻处空山,参考苦少,直探於译典者多;於时贤之作,惟内院出版之数种,商务本之《佛教史略》,《印度哲学宗教史》而已。不复一一注出,非掠美也。书成,演培、妙钦、文慧等诸学友劝以刊行,且罄其仅有之一切为刊费,心不忍却,允之。得周君贯仁、蒙君仁慈为任校印之责。学友之热忱可感有如此,令人忘其庸病矣!民国三一、一0、三,印顺自序於合江法王学院。
二十七年冬,梁漱溟氏来山,自述其学佛中止之机曰∶“此时、此地、此人”。吾闻而思之,深觉不特梁氏之为然,宋明理学之出佛归儒,亦未尝不缘此一念也。佛教之遍十方界,尽未来际,度一切有情,心量广大,非不善也。然不假以本末先後之辨,任重致远之行,而竞为“三生取办”,“一生圆证”,“即身成佛”之谈,事大而急功,无惑乎佛教之言高而行卑也!吾心疑甚,殊不安。时治唯识学,探其源於《阿含经》,读得“诸佛皆出人间,终不在天上成佛也”句,有所入。释尊之为教,有十方世界而详此土,立三世而重现在,志度一切有情而特以人类为本。释尊之本教,初不与末流之圆融者同,动言十方世界,一切有情也,吾为之喜极而泪。
二十九年,游黔之诛垣,张力群氏时相过从。时太虚大师访问海南佛教国,以评王公度之“印度信佛而亡”,主“印度以不信佛而亡”,与海南之同情王氏者辩。张氏闻之,举以相商曰∶“为印度信佛而亡之说者,昧於孔雀王朝之崇佛而强,固不可。然谓印度以不信佛而亡,疑亦有所未尽。夫印度佛教之流行,历千六百年,时不为不久;遍及五印,信者不为不众,而末流所趋,何以日见衰竭?其或印度佛教之兴,有其可兴之道;佛教之衰灭,末流伪杂有以致之乎”?余不知所以应,姑答以“容考之”。释慧松归自海南,道出诛垣,与之作三日谈。慧师於“无往不圆融”、“无事非方便”,攻难甚苦。盖病其流风之杂滥,梵佛一体而失佛教之真也。
自尔以来,为学之方针日定,深信佛教於长期之发展中,必有以流变而失真者。探其宗本,明其流变,抉择而洗链之,愿自治印度佛教始。察思想之所自来,动机之所出,於身心国家实益之所在,不为华饰之辩论所蒙,愿本此意以治印度之佛教。
治印度佛教不易,取材於 译之经论,古德之传记,支离破碎甚,苦无严明条贯之体系,足资依循。察印度佛教之流变,自其事理之特徵,约为五阶而束之为三时。三时之证有四∶
一、经典之暗示∶声闻藏不判教。性空大乘经判小、大二教,以空为究竟说。真常与唯心之大乘经判三教∶初则详无常、实有之声闻行;次则说性空、幻有之菩萨行;後则说真常、妙有(不空)之如来行,以空为不了义。昔以一切经为佛说,则三者为如来说教之次第;今以历史印证之,则印度佛教发展之遗痕也。
二、察学者之从违∶凡信声闻藏者,或有不信大乘经为佛说;信大乘经者,必信声闻藏。信声闻及大乘性空经者,多有拒斥“真常论”与“唯心论”;信“真常唯心论”者,必以空为佛说。此以後承於前故必信;前者不详後,见後说之有异於前,故或破之。
三、符古德之判教∶印华古德之约理以判教者,并与此三期之次第合。尝为“三期佛教与判教”一文,揭之於海潮音(见二十二卷十二期)。
四、合传译之次第∶“经”则自汉迄东晋之末,以《般若》、《法华》(以《法华》为真常论,隋智者牵合於《涅盘》而後盛说之。前此之宋慧观、梁法云辈,不闻此说)、《十地》、《净名》、《首楞严三昧经》等为盛,并性空之经也。东晋末,觉贤译《如来藏经》;北凉昙无谶译《涅盘》、《金光明》、《大集》;刘宋求那跋陀罗译《楞伽》、《深密》、《法鼓》、《胜 经》,真常与唯心之经,东来乃日多。以言“论”,西晋竺法护创译龙树之性空论。北魏,宋、齐、梁间乃有弥勒、无著、坚慧等真常与唯心论。传说之《大乘起信论》,则谓出於陈真谛之译。
印度之佛教,初则无常论盛行,中则性空论,後乃有真常论盛行,参证史迹有如此,不可以意为出入也。印度佛教之仅存者,多断片,支离破碎甚,吾人实无如之何。欲为印度佛教史之叙述,惟有积此支离破碎之片断,以进窥错综复杂之流变。离此,实无适当之途径可循。
印度佛教发展之全貌,时贤虽或有异说,而实大体从同。即此以探其宗本,自流变以批判其臧否,则以佛教者行解之庞杂,势必纷呶不已。海南佛教者,以声闻行为究竟;藏卫来者,以“无上瑜伽”为特高。中国佛教之传统学者,以“真常论”为根基(“三论”、“天台”融真常於性空,“唯识”则隐常於真常。“贤”、“禅”、“密”为彻底之真常者。“净”则随学者所学而出入之)。 不暇辩诘,请直述研求之所见∶“佛教乃内本释尊之特见,外冶印度文明以创立者”。故流变之印度佛教,有反释尊之特见者,辟之可也。非适应无以生存,其因地、因时、因人而间不同者,事之不可免,且毋宁视为当然。以是,海南佛教者忽视佛教正常之开显,方便之适应,指责一切大乘道,非佛意也。然“方便”云云,或为正常之适应,或为畸形之发展,或为毒素之羼入,必严为料简,正不能率以“方便”二字混滥之。
释尊之特见,标“缘起无我说”,反吠陀之常我论而兴。後期之佛教,日倾向於“真常、唯心”,与常我论合流。直就其理论观之,虽融三明之哲理,未见其大失;即绳墨之,亦见理未彻,姑为汲引婆罗门(印度教)而谈,不得解脱而已。若即理论之圆融方便而见之於事行,则印度“真常论”者之末流,融神秘、欲乐而成邪正杂滥之梵佛一体。在中国者,末流为三教同源论,冥镪祀祖,扶鸾降神等,无不渗杂於其间。“真常唯心论”,即佛教之梵化,设以此为究竟,正不知以何为释尊之特见也!
印度之佛教,自以释尊之本教为淳朴、深简、平实。然适应时代之声闻行,无以应世求,应学释尊本行之菩萨道。中期佛教之缘起性空(即缘起无我之深化),虽已启梵化之机,而意象多允当。龙树集其成,其说菩萨也∶1.三乘同入无馀涅盘而发菩提心,其精神为“忘己为人”。2.抑他力为卑怯,“自力不由他”,其精神为“尽其在我”。3.三阿僧只劫有限有量,其精神为“任重致远”。菩萨之真精神可学,略可於此见之。龙树有革新僧团之志,事未成而可师。能立本於根本佛教之淳朴,宏阐中期佛教之行解(梵化之机应慎),摄取後期佛教之确当者,庶足以复兴佛教而畅佛之本怀也欤!
中国佛教为“圆融”、“方便”、“真常”、“唯心”、“他力”、“顿证”之所困,已奄奄无生气;“神秘”、“欲乐”之说,自西而东,又日有泛滥之势。乃综合所知,编《印度之佛教》为诸生讲之。僻处空山,参考苦少,直探於译典者多;於时贤之作,惟内院出版之数种,商务本之《佛教史略》,《印度哲学宗教史》而已。不复一一注出,非掠美也。书成,演培、妙钦、文慧等诸学友劝以刊行,且罄其仅有之一切为刊费,心不忍却,允之。得周君贯仁、蒙君仁慈为任校印之责。学友之热忱可感有如此,令人忘其庸病矣!民国三一、一0、三,印顺自序於合江法王学院。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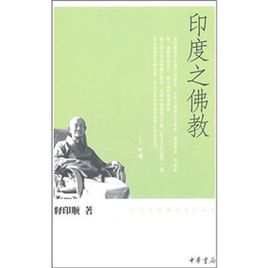 作者:释印顺(当代)
作者:释印顺(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