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 序
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雨季几乎过去了;我第二次来到印度。森林花园的围墙满溢着深绿色。暗红色的花深深地隐藏起来。我和另外十几个人等在师傅的门口;橘黄色的袍子,宁静的、忧虑的面容,少许的交谈,就象夜晚动物在森林的家里发出沙沙的声音一样。我什么也不期待;各种期望以及它们的成百上千的复制品和阴影都歇在一边;我们彼此厌倦──这些期望和我──已经超过了厌倦之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互相抵消了。我们等待了很久。在过去十五个月里,我竭尽全力地静心──最后两个星期是强化释放疗法(primal therapy )。在释放疗法中,我从“婴儿体”喊出一阵一阵的痛苦,婴儿体在我里面作为所有人生戏剧的提示和指引。一些小的恐惧在我的身体上荡漾开来,然后消失,然后再荡漾开来。我注视着呼吸轻柔地起伏过我的身体──它是自然的,我几乎执着于它。
最后我们经过大门,走上房子旁边一条黑暗的碎石路,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绕道到了走廊,猛然看见师傅坐在灯光下一张暗色椅子上,灯光围绕着他,浅色的袍子,深色的皮肤,以及周遭合抱的灯光和夜晚。一只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其中一只脚没有穿凉鞋,一只雕琢出奇的生动的脚,美丽的、黄褐色的,人们向它行礼──脱掉鞋子,我们急急忙忙地,欣喜的脚踏上大理石的地砖,就象被磁石吸引一样,来到他的脚边,静静地坐在他的注视之下。去感觉透明、单独、不存在和完全在这里──跟他在一起,属于他,在他里面。
他在微笑。我们在他的脚边坐成半圆,就象围绕着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一棵圣诞树──那是一种不可能地致密而集中的爱。他的微笑是一个孩子的微笑,那么天真、那么全然,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微笑──他是一个如此没有隐蔽、如此丰满、如此了悟、如此成熟的成人,以至于他已经再次爆发成孩童。他在我们面前那么充满人性,所以他是一个超人──他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完美的荣耀和最彻底的深度的全部。所有执着于头脑的思想都被他的光辉熄灭了。我只能注视着。思想变成身体里面一种无望的运动。我注视着自己想要跟他在一起、想要感觉他的话进入我。
他跟我们中间的几个人谈了一些关于爱、静心和怎么做的问题,有人感到很恐惧,师傅叫他们做一种静心,说“啊!”,同时感觉声音从恐惧的中心发出来,然后安静地躺下来,就象躺在母亲的胸上,感觉那个能量。
然后他看着我。他不等我说什么,就出乎意料地说:“玛都莉──这对你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的晚上。”是的,我说,我点点头,好象我知道似的,因为我又知道又不知道。他拿来一盏小小的闪光灯,上面有一道狭窄的光线,他说:“现在安静地坐着,把眼睛闭上。”他用它照进我的第三只眼:前额的中心,在眉毛上面。我在里面注视着光的行动,好象一道光突然照在黑暗的、爬来爬去的昆虫上面,或者照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蟑螂或者蛾子窝上。它们四散飞扬,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能量的绽放、轻微的行动,有一些是流动的,有一些是阻塞的。热量压进了中心。然后它就结束了。我睁开我的眼睛。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存在看着我,生动地、友善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完全地平凡。”
我说是的、哦,我点头,我是一种不存在的透明的困惑、一种不在那里的惊讶,沉浸在光里面,象一个白痴似的张口结舌地等着,他说:
“只要完全地平凡。以完全平凡的方式行动──就象你所感觉的那样行动。你要放下所有的未来、所有的目标。对于你,没有未来。要快乐。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你要放下所有的努力。”
那么──我是否应该静心呢?我问。
“如果你感觉想要静心的话。”他说。他是那么明亮、当下而全然,我被弄得眼花缭乱,我一直想把眼睛垂下来,然后再看。“但是你不能对静心做任何努力。如果你想要静心,你就静心;但是要纯粹地享受,你哪里也不去──甚至在你不想静心的时候,也不要感觉内疚。不要再有‘玛都莉需要释放疗法。’不。结束了。记住──没有应该。我对你所说的就是放松。只要放松。”
他注视着我说:“不要再有问题了。永远不要再把问题带到这里来。好吗?你明白吗?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要放下所有的控制。好吗,玛都莉?很好!”好象在说──足够了。
我在点头,我的头脑在狼吞虎咽,我说我猜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信任只要……而他说:“你只要放松。保持平凡。”──似乎在漠视我制造问题的努力。我合掌而拜,然后退回我的位置,一面笑着,有一半崩溃了,一面观照,他以完全的关注和爱沿着半圆一一跟我们会合。
当达圣(darshan )结束的时候,我在笑,当他走回房间的时候,我跟其他人一起向他鞠躬,当我套上凉鞋的时候,我在笑,我身轻如燕地跑过小路、跑出大门,在黑暗中骑在自行车上笑着回家。
我不再去想我曾经认为我必须不平凡。但是第二天我发现自己感到愤怒、憎恨、身陷罗网。我感到每一条逃跑的路都被切断了。没有应该!再也没有问题!我再也不能问他怎么办!但是我必须失去控制!必须吗?不,连这样也不是。没有应该!要放松!要快乐!要没有问题!没有所谓的没有问题!他已经切断了我所有的花招。我是急性子,我被炸裂了,然后平静下来,第二天发生了、第二天又发生了、一直发生到今天。
那正是长久的静心。
那就是老子。
他所说的话还在往里面下沉。要平凡。我的奋斗的自我、一生的伴侣,在它企图奋斗的时候,必须看它自己一百次,必须信任那个奋斗已经结束了。就象信任在峡谷上面走绳索──信任再也不需要担心了一样。努力已经变成我的一个习惯、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有很多思想在它的周围飞来飞去,那些我能记得的思想是从各个地方──从书本、从别人、从学校被培养出来的、被邀请而来的。我的头脑总是在说──只要你再努力一点点──只要你做这个──你就会突破。而这才是后面的秘密思想──那么,他们就会爱你、喜欢你、知道你。
现在奥修说不要演戏。当下的、空的、自然的行动──把头脑看成是昆虫的外壳,它是仆人、朋友、旧外套──宁可在思想之间运动,也不要进入它们。在连续练习派坦迦利瑜珈方法的三个月里,我重新经验了每一样可能从头脑里拉出来的东西。在静心里面,我潜入各种神经病、意象、一层又一层的记忆,从身体组织里解开它们,在它们消失的时候,感觉那种爆炸。当我进入内在的时候,我到处碰到我自己的鼻子。在静心上,我是一个成就迷──绞尽脑汁地寻找更多的东西吞下去。我的人生就是为了更多的记忆、更多的感觉、更多的痛苦的奋斗。那些关于我是一个多么好的静心者、一个多么好的女孩、一个多么勤劳的工作者、一个多么狂热的宗教信徒的微妙思想在增长。我是一个假虔诚的人;或许我会永远如此。只有那个惊讶和思想之间的运动不是这样。
那是一个温暖的夜晚。雨季几乎过去了;我第二次来到印度。森林花园的围墙满溢着深绿色。暗红色的花深深地隐藏起来。我和另外十几个人等在师傅的门口;橘黄色的袍子,宁静的、忧虑的面容,少许的交谈,就象夜晚动物在森林的家里发出沙沙的声音一样。我什么也不期待;各种期望以及它们的成百上千的复制品和阴影都歇在一边;我们彼此厌倦──这些期望和我──已经超过了厌倦之点──因为现在,我们已经互相抵消了。我们等待了很久。在过去十五个月里,我竭尽全力地静心──最后两个星期是强化释放疗法(primal therapy )。在释放疗法中,我从“婴儿体”喊出一阵一阵的痛苦,婴儿体在我里面作为所有人生戏剧的提示和指引。一些小的恐惧在我的身体上荡漾开来,然后消失,然后再荡漾开来。我注视着呼吸轻柔地起伏过我的身体──它是自然的,我几乎执着于它。
最后我们经过大门,走上房子旁边一条黑暗的碎石路,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世界里,绕道到了走廊,猛然看见师傅坐在灯光下一张暗色椅子上,灯光围绕着他,浅色的袍子,深色的皮肤,以及周遭合抱的灯光和夜晚。一只腿架在另一只腿上,其中一只脚没有穿凉鞋,一只雕琢出奇的生动的脚,美丽的、黄褐色的,人们向它行礼──脱掉鞋子,我们急急忙忙地,欣喜的脚踏上大理石的地砖,就象被磁石吸引一样,来到他的脚边,静静地坐在他的注视之下。去感觉透明、单独、不存在和完全在这里──跟他在一起,属于他,在他里面。
他在微笑。我们在他的脚边坐成半圆,就象围绕着一个讲故事的人,或者一棵圣诞树──那是一种不可能地致密而集中的爱。他的微笑是一个孩子的微笑,那么天真、那么全然,我们大多数人从来没有看见过这样的微笑──他是一个如此没有隐蔽、如此丰满、如此了悟、如此成熟的成人,以至于他已经再次爆发成孩童。他在我们面前那么充满人性,所以他是一个超人──他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完美的荣耀和最彻底的深度的全部。所有执着于头脑的思想都被他的光辉熄灭了。我只能注视着。思想变成身体里面一种无望的运动。我注视着自己想要跟他在一起、想要感觉他的话进入我。
他跟我们中间的几个人谈了一些关于爱、静心和怎么做的问题,有人感到很恐惧,师傅叫他们做一种静心,说“啊!”,同时感觉声音从恐惧的中心发出来,然后安静地躺下来,就象躺在母亲的胸上,感觉那个能量。
然后他看着我。他不等我说什么,就出乎意料地说:“玛都莉──这对你将是一个非常具有决定性的晚上。”是的,我说,我点点头,好象我知道似的,因为我又知道又不知道。他拿来一盏小小的闪光灯,上面有一道狭窄的光线,他说:“现在安静地坐着,把眼睛闭上。”他用它照进我的第三只眼:前额的中心,在眉毛上面。我在里面注视着光的行动,好象一道光突然照在黑暗的、爬来爬去的昆虫上面,或者照在一个黑暗的角落里蟑螂或者蛾子窝上。它们四散飞扬,什么也没有了,只有能量的绽放、轻微的行动,有一些是流动的,有一些是阻塞的。热量压进了中心。然后它就结束了。我睁开我的眼睛。他以他的全部力量和存在看着我,生动地、友善地对我说:“从现在开始,你只要完全地平凡。”
我说是的、哦,我点头,我是一种不存在的透明的困惑、一种不在那里的惊讶,沉浸在光里面,象一个白痴似的张口结舌地等着,他说:
“只要完全地平凡。以完全平凡的方式行动──就象你所感觉的那样行动。你要放下所有的未来、所有的目标。对于你,没有未来。要快乐。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你要放下所有的努力。”
那么──我是否应该静心呢?我问。
“如果你感觉想要静心的话。”他说。他是那么明亮、当下而全然,我被弄得眼花缭乱,我一直想把眼睛垂下来,然后再看。“但是你不能对静心做任何努力。如果你想要静心,你就静心;但是要纯粹地享受,你哪里也不去──甚至在你不想静心的时候,也不要感觉内疚。不要再有‘玛都莉需要释放疗法。’不。结束了。记住──没有应该。我对你所说的就是放松。只要放松。”
他注视着我说:“不要再有问题了。永远不要再把问题带到这里来。好吗?你明白吗?从今天晚上开始,你要放下所有的控制。好吗,玛都莉?很好!”好象在说──足够了。
我在点头,我的头脑在狼吞虎咽,我说我猜我不知道我是否能够信任只要……而他说:“你只要放松。保持平凡。”──似乎在漠视我制造问题的努力。我合掌而拜,然后退回我的位置,一面笑着,有一半崩溃了,一面观照,他以完全的关注和爱沿着半圆一一跟我们会合。
当达圣(darshan )结束的时候,我在笑,当他走回房间的时候,我跟其他人一起向他鞠躬,当我套上凉鞋的时候,我在笑,我身轻如燕地跑过小路、跑出大门,在黑暗中骑在自行车上笑着回家。
我不再去想我曾经认为我必须不平凡。但是第二天我发现自己感到愤怒、憎恨、身陷罗网。我感到每一条逃跑的路都被切断了。没有应该!再也没有问题!我再也不能问他怎么办!但是我必须失去控制!必须吗?不,连这样也不是。没有应该!要放松!要快乐!要没有问题!没有所谓的没有问题!他已经切断了我所有的花招。我是急性子,我被炸裂了,然后平静下来,第二天发生了、第二天又发生了、一直发生到今天。
那正是长久的静心。
那就是老子。
他所说的话还在往里面下沉。要平凡。我的奋斗的自我、一生的伴侣,在它企图奋斗的时候,必须看它自己一百次,必须信任那个奋斗已经结束了。就象信任在峡谷上面走绳索──信任再也不需要担心了一样。努力已经变成我的一个习惯、一个根深蒂固的模式。有很多思想在它的周围飞来飞去,那些我能记得的思想是从各个地方──从书本、从别人、从学校被培养出来的、被邀请而来的。我的头脑总是在说──只要你再努力一点点──只要你做这个──你就会突破。而这才是后面的秘密思想──那么,他们就会爱你、喜欢你、知道你。
现在奥修说不要演戏。当下的、空的、自然的行动──把头脑看成是昆虫的外壳,它是仆人、朋友、旧外套──宁可在思想之间运动,也不要进入它们。在连续练习派坦迦利瑜珈方法的三个月里,我重新经验了每一样可能从头脑里拉出来的东西。在静心里面,我潜入各种神经病、意象、一层又一层的记忆,从身体组织里解开它们,在它们消失的时候,感觉那种爆炸。当我进入内在的时候,我到处碰到我自己的鼻子。在静心上,我是一个成就迷──绞尽脑汁地寻找更多的东西吞下去。我的人生就是为了更多的记忆、更多的感觉、更多的痛苦的奋斗。那些关于我是一个多么好的静心者、一个多么好的女孩、一个多么勤劳的工作者、一个多么狂热的宗教信徒的微妙思想在增长。我是一个假虔诚的人;或许我会永远如此。只有那个惊讶和思想之间的运动不是这样。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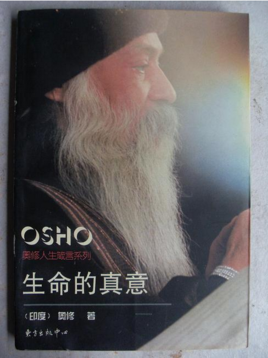 作者:奥修(印度)
作者:奥修(印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