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 要(1)
早在公元300至500年,具有性爱宝典性质的《欲经》在印度应运而生了。在作者犊子氏看来,性爱是复杂的游戏,它可以在多种层面上展开,针对各色女人,性爱的花样也各不相同,《欲经》对此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和精致的描述。抛去其繁琐的性爱花样分类,我们看到,犊子氏对性爱的基本态度是:性爱并不是情和欲的泛滥,而是要克制自我的激情,要在对自我情欲的严格控制之下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性爱。据说,犊子氏正是在进行了严格的禁欲之后才创作了《欲经》。和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同,性爱虽然是温柔与激情交织在一起的生活艺术,但犊子氏却认为,性爱的最高境界却是淡然无情。这种观点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从印度密教的角度说则是司空见惯了。
在大多数的宗教中,爱常常被神圣化。与爱相关的性,则基本上被抑止并消失不见了。印度密教则正好相反,它在将性事神圣化的同时,与性相关的爱不仅没有被神圣化,反而成了性的对立面而被加以抑止。在密教经典中,爱不起什么作用,密教特别强调对各种关系形式包括心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爱的拒绝,人类感情意义上的爱对于修行密教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因为爱是一种感情或激情,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行为,只有自私者才会爱;而密宗则将性爱从个人和社会中独立出来,认为不带情感、不带功利的世俗的性行为才是最神圣的,性爱的最高境界恰恰在于:淡然无情。因此,密教仪式中的性事并不表现为激情,而是一种非个性化的行为,它是一种无状态的心灵状态和浑然一体的自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无爱。
大概正是与此相关,佛教密宗中的女性神在形象上多表现出怪异的特征,密教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不美,而且是以丑与恶为其典型特征,其目的可能与密教对情与爱的拒绝有相当的关系。宗教文化在对性行为进行非难时,常常将女色与丑陋、邪恶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在心理和感情上对性感到厌恶、恐惧。密教因为是沉醉于性,所以它也沉醉于与性相关的丑陋、邪恶和死亡。密教试图超越美与丑、善与恶的界限,从而使性爱变成一种纯洁而自由的行为。而与情爱相结合的性行为常常使人们在专一的感情中变得自私、狭隘甚至是麻木,因为爱情常常是一个排斥他人的小天地。
密教的这些看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从印度古代文化中自然生成的。印度古代文化多将性爱看成是一种人生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女人不仅是欲望和享乐的化身,而且也是享乐的对象,女人渴望于男人的与男人渴望于女人的都是享乐,因此,男人不要将女人视作什么永恒或美的化身,西方文化中的圣母或永恒的女性美在古代印度文化中是找不到踪影的。印度古代文化认为,性爱游戏诞生于人们过剩的精力,而这种游戏的乐趣和奥秘恰恰在于性爱中的男女要保持旺盛的精力,否则,性爱便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身体耗损了。女人是欲望的化身,她们在性爱方面的旺盛精力是天生固有的,就像木柴一样会越烧越旺,而男人与女人不同,要想使性爱充满乐趣,男人就要克制自己,尤其不要对女人产生爱与激情,因为这二者乃是性爱游戏的大敌,只有克制着情,引导着欲,男人才能保持活力。从印度神秘主义文化的角度说,男女的性爱是阴阳二气在男女双方身体内相推相摩、交互激荡的过程,性事的高妙之处恰恰在于能够使阴阳二“气”处于合和的状态并以使男女双方的体内充溢着盈实圆满之感。
早期印度佛教曾竭力排斥人的性行为,将性爱从僧侣们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僧侣们习惯将身体视为由鲜血、各种体液、粪便和骷髅构成的一整套令人厌恶的整体,将来必会解体。但密教即坦陀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的身体比作一只可以渡过苦海的大船,是众生借以解脱的根本依靠和手段。密教认为,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隐藏着无限和永恒,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便在于爱,但爱若停留于精神的层面,爱便会在静止不动之中逐渐枯竭,人们的身体总是渴望着性爱,性爱体现的虽然是欲望和激情,但它却是通向崇高和解脱的必由之路。
概 要(2)
显然,印度密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唯身论(也译作身谛或身论,即关于身体的真论或真谛),可以说是“我者无它,身体而已”,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神圣的东西的话,那便是身体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密教使印度的宗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在公元五六世纪,色情奥义化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艳欲主义在印度文化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长达数百年之久,直到公元十世纪之后,随着###教的入侵,艳欲主义逐步演变成印度文化潜流,并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在近现代历史中,经过英国清教主义的洗礼,再加上甘地主义的改造,印度似乎早已失去了它真正的艳欲主义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声称他们相信印度的宗教,他们对瑜伽和印度神秘文化的兴趣从来不减。在当今世界,佛教广泛传播,大有复兴之势,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的复兴主要是佛教密宗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复兴。在西方,人们对密教也充满了更多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密教更多地关注于个人生活:密教使印度的宗教复杂化、神秘化的同时也使印度的宗教包括佛教世俗化、普遍化了,使宗教的真谛变成了生活的真谛。
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尤其是奥义书和佛教思想的浸染,叔本华从人之欲望的角度来认识生命存在的意义,认为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的过程。叔本华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尼采,而尼采的思想又直接启迪了福科,福科的一生都在努力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我何以活着?我该向生活学习什么?我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今天这个我而受苦受难?”他对于性的问题尤感兴趣,因为性实际上是人的欲望的最直接的体现:“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连接在一起的线索是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 印度古代文化实际上也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而且探讨得非常深入,甚至远远出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早在公元300至500年,具有性爱宝典性质的《欲经》在印度应运而生了。在作者犊子氏看来,性爱是复杂的游戏,它可以在多种层面上展开,针对各色女人,性爱的花样也各不相同,《欲经》对此做出了详细的划分和精致的描述。抛去其繁琐的性爱花样分类,我们看到,犊子氏对性爱的基本态度是:性爱并不是情和欲的泛滥,而是要克制自我的激情,要在对自我情欲的严格控制之下才能享受到真正的性爱。据说,犊子氏正是在进行了严格的禁欲之后才创作了《欲经》。和我们一般的想象不同,性爱虽然是温柔与激情交织在一起的生活艺术,但犊子氏却认为,性爱的最高境界却是淡然无情。这种观点多少有点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但从印度密教的角度说则是司空见惯了。
在大多数的宗教中,爱常常被神圣化。与爱相关的性,则基本上被抑止并消失不见了。印度密教则正好相反,它在将性事神圣化的同时,与性相关的爱不仅没有被神圣化,反而成了性的对立面而被加以抑止。在密教经典中,爱不起什么作用,密教特别强调对各种关系形式包括心理和社会意义上的爱的拒绝,人类感情意义上的爱对于修行密教的人来说是完全不能相容的,因为爱是一种感情或激情,是一种非常个性化的行为,只有自私者才会爱;而密宗则将性爱从个人和社会中独立出来,认为不带情感、不带功利的世俗的性行为才是最神圣的,性爱的最高境界恰恰在于:淡然无情。因此,密教仪式中的性事并不表现为激情,而是一种非个性化的行为,它是一种无状态的心灵状态和浑然一体的自我,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爱:无爱。
大概正是与此相关,佛教密宗中的女性神在形象上多表现出怪异的特征,密教中女性形象的塑造不仅不美,而且是以丑与恶为其典型特征,其目的可能与密教对情与爱的拒绝有相当的关系。宗教文化在对性行为进行非难时,常常将女色与丑陋、邪恶和死亡联系在一起,使人们在心理和感情上对性感到厌恶、恐惧。密教因为是沉醉于性,所以它也沉醉于与性相关的丑陋、邪恶和死亡。密教试图超越美与丑、善与恶的界限,从而使性爱变成一种纯洁而自由的行为。而与情爱相结合的性行为常常使人们在专一的感情中变得自私、狭隘甚至是麻木,因为爱情常常是一个排斥他人的小天地。
密教的这些看法也不是空穴来风,它是从印度古代文化中自然生成的。印度古代文化多将性爱看成是一种人生游戏。在这种游戏中,女人不仅是欲望和享乐的化身,而且也是享乐的对象,女人渴望于男人的与男人渴望于女人的都是享乐,因此,男人不要将女人视作什么永恒或美的化身,西方文化中的圣母或永恒的女性美在古代印度文化中是找不到踪影的。印度古代文化认为,性爱游戏诞生于人们过剩的精力,而这种游戏的乐趣和奥秘恰恰在于性爱中的男女要保持旺盛的精力,否则,性爱便不是一种游戏而是令人筋疲力尽的身体耗损了。女人是欲望的化身,她们在性爱方面的旺盛精力是天生固有的,就像木柴一样会越烧越旺,而男人与女人不同,要想使性爱充满乐趣,男人就要克制自己,尤其不要对女人产生爱与激情,因为这二者乃是性爱游戏的大敌,只有克制着情,引导着欲,男人才能保持活力。从印度神秘主义文化的角度说,男女的性爱是阴阳二气在男女双方身体内相推相摩、交互激荡的过程,性事的高妙之处恰恰在于能够使阴阳二“气”处于合和的状态并以使男女双方的体内充溢着盈实圆满之感。
早期印度佛教曾竭力排斥人的性行为,将性爱从僧侣们的生活中排除出去。僧侣们习惯将身体视为由鲜血、各种体液、粪便和骷髅构成的一整套令人厌恶的整体,将来必会解体。但密教即坦陀罗却反其道而行之,将人的身体比作一只可以渡过苦海的大船,是众生借以解脱的根本依靠和手段。密教认为,在我们有限的生命中隐藏着无限和永恒,人的最崇高的价值便在于爱,但爱若停留于精神的层面,爱便会在静止不动之中逐渐枯竭,人们的身体总是渴望着性爱,性爱体现的虽然是欲望和激情,但它却是通向崇高和解脱的必由之路。
概 要(2)
显然,印度密教是一种极端形式的唯身论(也译作身谛或身论,即关于身体的真论或真谛),可以说是“我者无它,身体而已”,如果说世界上有什么神圣的东西的话,那便是身体了。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密教使印度的宗教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至少在公元五六世纪,色情奥义化已经成为印度社会生活中存在的普遍现象,艳欲主义在印度文化的发展中占据了主导地位,并长达数百年之久,直到公元十世纪之后,随着###教的入侵,艳欲主义逐步演变成印度文化潜流,并变得面目全非了;而在近现代历史中,经过英国清教主义的洗礼,再加上甘地主义的改造,印度似乎早已失去了它真正的艳欲主义文化传统。
与此同时,自19世纪下半叶以来,也有越来越多的欧洲人声称他们相信印度的宗教,他们对瑜伽和印度神秘文化的兴趣从来不减。在当今世界,佛教广泛传播,大有复兴之势,但大多数学者都认为,佛教的复兴主要是佛教密宗也就是藏传佛教的复兴。在西方,人们对密教也充满了更多的兴趣,这主要是因为密教更多地关注于个人生活:密教使印度的宗教复杂化、神秘化的同时也使印度的宗教包括佛教世俗化、普遍化了,使宗教的真谛变成了生活的真谛。
深受印度古代文化尤其是奥义书和佛教思想的浸染,叔本华从人之欲望的角度来认识生命存在的意义,认为人生是在痛苦和无聊之间像钟摆一样来回摆动着的过程。叔本华的思想直接影响了尼采,而尼采的思想又直接启迪了福科,福科的一生都在努力进行着一场伟大的尼采式的探索:“我何以活着?我该向生活学习什么?我是如何变成今天这个我的?我为何要为做今天这个我而受苦受难?”他对于性的问题尤感兴趣,因为性实际上是人的欲望的最直接的体现:“这么多世纪以来,在我们的社会中,把性与真理的追求连接在一起的线索是什么……在我们这样的社会,性为什么不是一种简单的对种族、家庭和个人进行再生产的手段?为什么它不单单是获取快乐和享受的手段?为什么性最终被认为是我们最‘深刻’的真理藏身和表白的地方?” 印度古代文化实际上也一直在探讨这些问题,而且探讨得非常深入,甚至远远出乎我们现代人的想象。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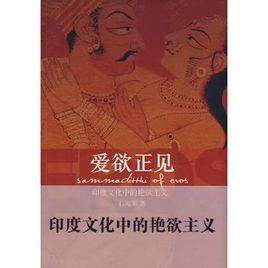 作者:石海峻(现代)
作者:石海峻(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