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像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一样,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震惊。当消息流传到外界,当朝日新闻社记者们开始报道那些大字报,当被捆绑的尸体沿珠江漂流至中国香港,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一半由于信息不通,一半由于缺乏洞察力,我们对这些纷乱的事实不能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后来,事态渐渐明朗化,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已发现并宣布了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1966年7月,他命令党的书记们亲临北京大学去经受这场文化革命。“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
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1]毛泽东对一些在1935年跟随他从江西到延安的干部们说,这些在国内战争很久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更有战斗力的革命者。毛泽东宣称:“闹事就是革命。”[2]
至少对我来说,这类话是意想不到的。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
也许因为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所知甚少,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20世纪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诚然,其他学者,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以及史华兹,已经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所有这些“主义”,仍使我感到不满意,不管对它们的具体论述和思考是多么令人敬佩。譬如,斯图尔特?施拉姆精确证明了毛泽东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某种未必代表人类最终命运的东西”)为什么是其思想中某种“辩证法的癖好”的产物。但是,这种癖好首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就像施拉姆所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癖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3]。
的确,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形象的。但是,当解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时,这样一种描绘就令人困惑不解了。他是一个大胆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用实践的秘诀来解析理论的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像一些人曾谨慎地暗示的那样,他甚至是一个用对抗性矛盾概念来代替阴阳概念的道家辩证论者?
我发现,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可以拒绝认真地对待毛泽东主义。为什么把理论智慧赋予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走向了1949年的胜利吗?为什么由于相信毛泽东的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远非对斯大林理论主张的模仿,就要把他的成功的策略和理智的精妙混为一谈?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使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甚至在掌握社会主义的辞藻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使命。但是,当我愿意承认“战场是[毛泽东的]学校”时,我也就假定了自觉的革命行动是靠理论来指导的。那种思想又受到了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一种假设的理论框架的支持。那些假设及其起源往往能被当事人意识到并直接描绘出来,尤其是在当事人理智地反省的时候。但毛泽东通常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已超出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而牵涉到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由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不得不探究到他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所使用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它们构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独特性——只有被放在历史背景中才讲得清楚。不过,简单的对照是不明智的。总体的归纳(“东方人使自己适应自然,西方人反抗自然”)会把超越时间和无历史意义的特性赋予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果没有具体的大众语言来沟通这些文化,那么总体的归
纳也就只能依赖于那些一般的特性。
诚然,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任何特殊的民族语言都是一种“不断隐喻的过程”。他曾经写道:“语言既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也是一个收藏人类生活与文明化石的博物馆。”[4]因此,毛泽东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语言,我们就能开始懂得一些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假设,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外思想融合在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中的方式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他们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也具有启迪意义。就一种普遍真理本身的要求来说,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他“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像“毛泽东主义”一样,已经变成一种混合体。
为了揭示这种混合性,本书第一部分由几个片断组成。有些仅与毛泽东本人有关:他害怕革命的倒退,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等等。但更多的篇幅则通过非类推的方法,研究了毛泽东和他的政策,以及其他的政治事例。其中有一些是具体的历史,例如清代乡约体制,甚至曾经可以在当代中国产生相似的制度;也有的是抽象的概念,例如卢梭的“大立法者”;或者甚至是含有隐喻的,像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因此,这些片断是充满想象力的:首先,透过表面现象可以看到,毛泽东显然是在为他那种政府理论做掩饰;其次,评价毛泽东本人的政治象征,这些象征往往是与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革命形象相适应的。因为毛泽东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神话创造者,他通过讽喻象征的手法来反映人民的追求。
提供这些片断是为了说明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语言。为了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我使用了一种哲学词汇——其原因并不在于我把它看作是其自身的一种先验的语言,而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更鲜明的对比方式。所以,本书以下几部分试图对中西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出一种逻辑一致的阐明。只对政治上的毛泽东主义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比较零散。既然毛泽东及其同僚那样地低估康有为的理论,为什么还要阐述这种理论的演化呢?这里,我认为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尽管毛泽东不了解康有为思想的错综复杂性,但康的关于“仁”的一元论概念,以及他的有关人类史的三阶段的理论,却渗透到了毛泽东那整整一代人的思想之中,粉碎了儒家关系的专制,为更加激进的社会批判形式开辟了道路。康的这种普遍重要性,是我花费如此多篇幅来讨论他的部分原因。
像大多数研究中国的外国学者一样,1966年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使我震惊。当消息流传到外界,当朝日新闻社记者们开始报道那些大字报,当被捆绑的尸体沿珠江漂流至中国香港,人民共和国似乎已经完全迷失了政治方向。一半由于信息不通,一半由于缺乏洞察力,我们对这些纷乱的事实不能作出一个清晰的判断。后来,事态渐渐明朗化,人们才了解到,毛泽东已发现并宣布了共产党内的阶级斗争。1966年7月,他命令党的书记们亲临北京大学去经受这场文化革命。“去了会被学生包围,要他们包围,你和他们几个人谈话,就
会被包围起来,广播学院被打一百多人,我们这个时代就有这个好处。”[1]毛泽东对一些在1935年跟随他从江西到延安的干部们说,这些在国内战争很久之后才出生的年轻一代,已经成为更有战斗力的革命者。毛泽东宣称:“闹事就是革命。”[2]
至少对我来说,这类话是意想不到的。任何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怎么能够如此轻易地抛弃他自己的政党,即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和具有社会主义觉悟的顶梁柱呢?毛泽东本人又是从哪里推断出他的“继续革命”的思想必然是正确的呢?
也许因为我对毛泽东思想的渊源所知甚少,我觉得很难将这位空想家与那位20世纪30年代务实的革命者协调起来。诚然,其他学者,如斯图尔特?R?施拉姆、陈志让、莫里斯?迈斯纳,以及史华兹,已经对毛泽东思想中的“普罗米修斯主义”、“唯意志论”、“民粹主义”和“雅各宾主义”作了详尽的分析。但是,所有这些“主义”,仍使我感到不满意,不管对它们的具体论述和思考是多么令人敬佩。譬如,斯图尔特?施拉姆精确证明了毛泽东有关共产主义社会的见解(“某种未必代表人类最终命运的东西”)为什么是其思想中某种“辩证法的癖好”的产物。但是,这种癖好首先是怎样形成的呢?我觉得,就像施拉姆所说的,“探索毛泽东思想中辩证法癖好的渊源是思想史上的一个吸引人的——尽管或许是不可能解决的——问题”[3]。
的确,仅就革命战略家这一方面而言,是有可能为毛泽东描绘出一个前后一致的政治形象的。但是,当解释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的理论根基时,这样一种描绘就令人困惑不解了。他是一个大胆走向虚无的存在主义者,还是一个用实践的秘诀来解析理论的浪漫的马克思主义者?或者像一些人曾谨慎地暗示的那样,他甚至是一个用对抗性矛盾概念来代替阴阳概念的道家辩证论者?
我发现,要直截了当地回答这些问题是不可能的。当然,你可以拒绝认真地对待毛泽东主义。为什么把理论智慧赋予一个革命的实用主义者,难道仅仅是因为毛泽东领导共产党走向了1949年的胜利吗?为什么由于相信毛泽东的名著《实践论》和《矛盾论》远非对斯大林理论主张的模仿,就要把他的成功的策略和理智的精妙混为一谈?为什么要把毛泽东变成一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而使简单的事物复杂化?毛泽东毕竟首先是一个革命者;他甚至在掌握社会主义的辞藻之前就发现了这一使命。但是,当我愿意承认“战场是[毛泽东的]学校”时,我也就假定了自觉的革命行动是靠理论来指导的。那种思想又受到了行动者本身通常几乎意识不到的一种假设的理论框架的支持。那些假设及其起源往往能被当事人意识到并直接描绘出来,尤其是在当事人理智地反省的时候。但毛泽东通常不是这样的。
所以,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问题已超出对毛泽东个人的研究,而牵涉到了现代中国思想史。由于毛泽东的最重要的问题是客观历史与主观意志之间的矛盾,因此,我不得不探究到他和他的许多同时代人所使用的关于人与自然的基本假设。这些假设——它们构成了中国的马克思主义革命的独特性——只有被放在历史背景中才讲得清楚。不过,简单的对照是不明智的。总体的归纳(“东方人使自己适应自然,西方人反抗自然”)会把超越时间和无历史意义的特性赋予特殊的文化背景。如果没有具体的大众语言来沟通这些文化,那么总体的归
纳也就只能依赖于那些一般的特性。
诚然,用安东尼奥?葛兰西的话来说,任何特殊的民族语言都是一种“不断隐喻的过程”。他曾经写道:“语言既是一种活生生的东西,也是一个收藏人类生活与文明化石的博物馆。”[4]因此,毛泽东所理解的那种语言,既包含了中国以前固有的观念,又吸收了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新名词。如果从这两个角度去理解这种语言,我们就能开始懂得一些毛泽东主义的基本假设,也能够更好地把握中外思想融合在20世纪中国革命者的思想中的方式了,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对他们具有历史意义,而且对我们也具有启迪意义。就一种普遍真理本身的要求来说,马克思主义采取了民族化的形式,从而使得它能通过承认许多其他“语言”并不接受的分析方式,把普遍性与特殊性结合在一起。事实上,在现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本身像“毛泽东主义”一样,已经变成一种混合体。
为了揭示这种混合性,本书第一部分由几个片断组成。有些仅与毛泽东本人有关:他害怕革命的倒退,他的个人崇拜,以及他对知识分子的态度等等。但更多的篇幅则通过非类推的方法,研究了毛泽东和他的政策,以及其他的政治事例。其中有一些是具体的历史,例如清代乡约体制,甚至曾经可以在当代中国产生相似的制度;也有的是抽象的概念,例如卢梭的“大立法者”;或者甚至是含有隐喻的,像葛兰西的“神话君主”。因此,这些片断是充满想象力的:首先,透过表面现象可以看到,毛泽东显然是在为他那种政府理论做掩饰;其次,评价毛泽东本人的政治象征,这些象征往往是与普通中国人心目中的革命形象相适应的。因为毛泽东既是一个政治家,也是一个神话创造者,他通过讽喻象征的手法来反映人民的追求。
提供这些片断是为了说明存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马克思主义这样两种语言。为了仔细分析它们的区别,我使用了一种哲学词汇——其原因并不在于我把它看作是其自身的一种先验的语言,而在于它可以提供一种更鲜明的对比方式。所以,本书以下几部分试图对中西方思想的哲学基础作出一种逻辑一致的阐明。只对政治上的毛泽东主义感兴趣的读者可能会觉得这些内容比较零散。既然毛泽东及其同僚那样地低估康有为的理论,为什么还要阐述这种理论的演化呢?这里,我认为思想史本身是能够给人以启迪的。尽管毛泽东不了解康有为思想的错综复杂性,但康的关于“仁”的一元论概念,以及他的有关人类史的三阶段的理论,却渗透到了毛泽东那整整一代人的思想之中,粉碎了儒家关系的专制,为更加激进的社会批判形式开辟了道路。康的这种普遍重要性,是我花费如此多篇幅来讨论他的部分原因。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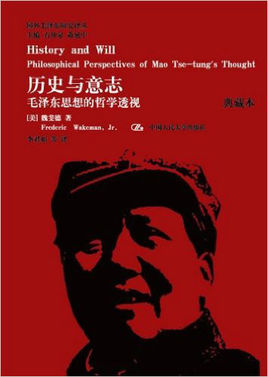 作者:魏斐德(现代)
作者:魏斐德(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