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
1
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平安喜乐。
2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3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日,我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不为轮回,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以上三段文字,是目前流传比较广的所谓“六世达赖喇嘛情歌”,或者叫“仓央嘉措情诗”。
仓央嘉措,这是个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出现的一个名字,这是个明显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名字,是的,他是藏族人,他的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所谓的“诗人”。
无法不感谢以上三段文字的作者,没有这几段精致优美的文字,我们很少有人会记住仓央嘉措这个名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业已存在,如果有人询问其他历世达赖喇嘛的名字,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说出的,而只有第六世,仓央嘉措,广为人知,就如同我们熟悉清朝历代皇帝的年号,却只不过仅仅能叫出玄烨、胤禛等少数几个名字来一样,若问咸丰、同治的名字,大半还是知者甚少。
所以,对以上三段文字的谢意,我们至少可以基于这一点——是它们的流传,让我们知道了仓央嘉措的存在,并与六世达赖喇嘛对号入座,并由此,让我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它的神秘,它的美丽,它的若隐若现的奇迹及由着这奇迹生发的想往。
然而,也仅限如此,因为,这三段文字跟仓央嘉措一点关系都没有——嗯,话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有一点点关系,那就是张冠李戴,它实实在在是个现代的汉族人写的,而被大多数人以为是仓央嘉措的作品。
从三段文字的细微不同可以看出,它业已经过修饰,其原本,最早出现的载体不是诗集,更不是什么仓央嘉措情歌集,而是一张叫做《央金玛》的唱片。
所以,它是首歌词,它的名字叫《信徒》。
而在这张由朱哲琴与何训田合作的唱片中,出现了另一首歌,名字叫《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第一次张冠李戴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信徒”这个名字渐渐不被人知晓,而将其歌词冠以“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题目,之后,题目成了作品属性,就如同《道德经》与《老子》并存一样。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歌词,却确实有仓央嘉措的身影,这首歌词将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诗歌整合在一起,并经过了删改和添加,形成了一首与原作基本无关的歌词。
第二次张冠李戴,则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误会上的有意行为,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体中较有影响的乐队的重新演绎,它将朱哲琴的两首歌——《信徒》与《六世达赖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诗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做《仓央嘉措情歌》。而据说,这种大杂烩的拼盘歌词,也曾经由某位藏传佛教年轻活佛演唱过。
于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为了仓央嘉措诗歌中的一部分——虽然,仓央嘉措跟它没有任何著作权与署名权的关系。
其实,如果仔细地比照《信徒》与业已被学界认定的“仓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文字风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辞之复杂、意境之优美、文字之洗练,在“仓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儿影子。
真正的“仓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于1930年,汉文版本的著作权为我国藏学藏语研究的前辈于道泉先生,这本书版本名号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书名《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它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此后,有1932年刘家驹本、1939年曾缄本和刘希武本等,而且,这几个版本间,也有互相影响的痕迹,再其后的版本,几乎都是以上版本的“润色本”。
而在这些版本中,从来就没出现过“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但它的流传确实太广,让人以讹传讹,直至今天,可以预见的是,它还会误传下去。
1
那一夜,我听了一宿梵唱,不为参悟,只为寻你的一丝气息。
那一月,我转过所有经轮,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纹。
那一年,我磕长头拥抱尘埃,不为朝佛,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我翻遍十万大山,不为修来世,只为路中能与你相遇。
那一瞬,我飞升成仙,不为长生,只为保佑你平安喜乐。
2
那一天,闭目在经殿香雾中,蓦然听见你颂经中的真言。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转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磕长头匍匐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转水转佛塔啊,不为修来生,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3
那一刻,我升起风马,不为祈福,只为守候你的到来。
那一日,我垒起玛尼堆,不为修德,只为投下心湖的石子。
那一月,我摇动所有的经筒,不为超度,只为触摸你的指尖。
那一年,我磕长头在山路,不为觐见,只为贴着你的温暖。
那一世,转山不为轮回,只为途中与你相见。
以上三段文字,是目前流传比较广的所谓“六世达赖喇嘛情歌”,或者叫“仓央嘉措情诗”。
仓央嘉措,这是个在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很难出现的一个名字,这是个明显带有少数民族特征的名字,是的,他是藏族人,他的身份是藏传佛教格鲁派的第六世达赖喇嘛,他的另一个身份是所谓的“诗人”。
无法不感谢以上三段文字的作者,没有这几段精致优美的文字,我们很少有人会记住仓央嘉措这个名字。很有趣的一个现象业已存在,如果有人询问其他历世达赖喇嘛的名字,绝大多数人是无法说出的,而只有第六世,仓央嘉措,广为人知,就如同我们熟悉清朝历代皇帝的年号,却只不过仅仅能叫出玄烨、胤禛等少数几个名字来一样,若问咸丰、同治的名字,大半还是知者甚少。
所以,对以上三段文字的谢意,我们至少可以基于这一点——是它们的流传,让我们知道了仓央嘉措的存在,并与六世达赖喇嘛对号入座,并由此,让我们对藏传佛教产生了兴趣,它的神秘,它的美丽,它的若隐若现的奇迹及由着这奇迹生发的想往。
然而,也仅限如此,因为,这三段文字跟仓央嘉措一点关系都没有——嗯,话也不必说得这么绝对,有一点点关系,那就是张冠李戴,它实实在在是个现代的汉族人写的,而被大多数人以为是仓央嘉措的作品。
从三段文字的细微不同可以看出,它业已经过修饰,其原本,最早出现的载体不是诗集,更不是什么仓央嘉措情歌集,而是一张叫做《央金玛》的唱片。
所以,它是首歌词,它的名字叫《信徒》。
而在这张由朱哲琴与何训田合作的唱片中,出现了另一首歌,名字叫《六世达赖喇嘛情歌》。
第一次张冠李戴就这样自然地发生了,“信徒”这个名字渐渐不被人知晓,而将其歌词冠以“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题目,之后,题目成了作品属性,就如同《道德经》与《老子》并存一样。
而那首原名是《六世达赖喇嘛情歌》的歌词,却确实有仓央嘉措的身影,这首歌词将其多首意味相近的诗歌整合在一起,并经过了删改和添加,形成了一首与原作基本无关的歌词。
第二次张冠李戴,则完全是在第一次文字误会上的有意行为,这次是一支在青年群体中较有影响的乐队的重新演绎,它将朱哲琴的两首歌——《信徒》与《六世达赖喇嘛情歌》融合在一起,并加入了另一首真正的诗歌,形成了一首新作,叫做《仓央嘉措情歌》。而据说,这种大杂烩的拼盘歌词,也曾经由某位藏传佛教年轻活佛演唱过。
于是,“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成为了仓央嘉措诗歌中的一部分——虽然,仓央嘉措跟它没有任何著作权与署名权的关系。
其实,如果仔细地比照《信徒》与业已被学界认定的“仓央嘉措情歌”,任何人都可以看得出来,它们的文字风格完全不一致,《信徒》的修辞之复杂、意境之优美、文字之洗练,在“仓央嘉措情歌”中完全找不到一丁点儿影子。
真正的“仓央嘉措情歌”,最早出版于1930年,汉文版本的著作权为我国藏学藏语研究的前辈于道泉先生,这本书版本名号为“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单刊甲种之五”,书名《第六代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情歌》。
它开创了仓央嘉措诗歌汉译的先河,此后,有1932年刘家驹本、1939年曾缄本和刘希武本等,而且,这几个版本间,也有互相影响的痕迹,再其后的版本,几乎都是以上版本的“润色本”。
而在这些版本中,从来就没出现过“那一天,那一月,那一年”。
但它的流传确实太广,让人以讹传讹,直至今天,可以预见的是,它还会误传下去。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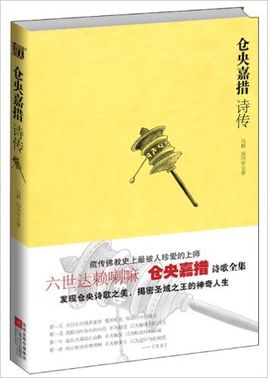 作者:苗欣宇(现代)
作者:苗欣宇(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