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进*
在1980年的某个时候,我的朋友马洛·肯瑞(MuroKenji)在和他的指导教师兼朋友——一位名为鹤见俊介(TsurumiShunsuke)的哲学家谈过话后,顺访了我,他兴致很高(这是他的习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他说,“*在所有地方都是激进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批判性的:在美国,在苏联,在日本,在菲律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所有地方”。这个既老又新、既简单又复杂、既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的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当看到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原则——据福斯特(Forster)讲,这个原则只值得欢呼两下,但绝不值得欢呼三下——如此兴致勃勃,我是感到很好奇的。
大约在相同的时候,有人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说,有一本名为《*》的杂志,并询问我在日本是否有激进*主义者可以举荐为这本杂志撰稿。“激进*”这个观念开始植入我的脑海。这种经验有点像你开始爱上邻家的一位姑娘(或小伙),那种感觉你一直知道但突然变得那样新鲜、那样鲜明、那样……无有前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以及在日本,我一直是某种类型的运动积极分子,但像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主义者这道槛,我未跨过,只是一直借重*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批判力量。在那些年代的运动政治学中,*主义被解释为和*左翼有一定的距离,即是说比*左翼要激进;在另一方面,*主义者被解释为站在*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地位上(并很难和后者区分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左—中—右这样的空间性的隐喻对于安置我们政治学的方式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量。一个人的政治定位如果是被认为在另外的两种政治倾向之间,这种定位很难避免被想象为是一种妥协、杂糅,并且没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原则。我开始感觉到鹤见马洛的定律(“*在所有地方都是批判性的”)能够成为重新安排这个空间性的形象的基础。*既然像激进主义一样被认为是激进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定位和这些政治定位之间的关系将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将导致对政治现实作出更精确的反思,以及以一种方式赋予*理论更强的批判力量。
从我最初为这本书的观点开始构思算起,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在诸如波兰、缅甸、菲律宾等不同的国家中发生了激烈的*运动,同时在*理论领域产生了新的一波作为。在很多年中,任何一本题为《*》的书,基本可以判断为是在单调重复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所谓优点,但是称*为激进的一批理论家也出现了。当乔治·布什宣称在他的任期内*已经“胜利了”的时候,另外有人正建构或重新发现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可以作为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而且可以作为对里根和布什与其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共有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批判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的讨论第一次让人感兴趣。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贡献给这一讨论的。
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菲律宾大学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工作时,我不仅很难向在日本和美国的朋友,也很难向在菲律宾的朋友解释我的研究选择。我到菲律宾不是研究菲律宾本身,而是进行研究*理论的准备工作,这在他们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偏见在作怪。如果一位在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不研究马萨诸塞的政治或文化,人们不觉得奇怪。一位在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东南亚或一位在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非洲,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但反过来就不是如此:一位前往第三世界的访问学者就被认定要去研究第三世界。
我有意地选择菲律宾大学以打破这种固定观念,这符合这种一般原则:如果你打破某个固定的观念,你很可能将学到意想不到的事物。但是我选择菲律宾无论如何也不是偶然的。当时,1986年2月的人民权力革命刚过去一年。“人民权力”是希腊单词demos和kratia的英译。人民权力——激进*做了表面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仅通过人民赢得选举,而且通过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监督这场选举而获得选举胜利,人民将一个*的、有精良武装保护的、卑鄙而富裕的*者赶下台并赶出国。我想去这样一个地方,那里*不只是一个无力的口号而且是一个活的观念,一个真正重要的、人民以热情和投入来谈论的原则。事物并没有完全那样发展。尽管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公众情绪充满兴奋和激进希望,到1987年春天,公众情绪陷入了幻灭。激进希望——这是人*动的核心(我在第五章将更多地谈论这一点),已经制造了一种准确地说是革命的政治情境,但是这一希望的目标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政客——正寻求赢得选举的科拉松·阿基诺。激进*在重建自由主义政治中消耗了自己的能量。土地改革搁浅了,内战在继续,1987年是阴郁的一年。
在1980年的某个时候,我的朋友马洛·肯瑞(MuroKenji)在和他的指导教师兼朋友——一位名为鹤见俊介(TsurumiShunsuke)的哲学家谈过话后,顺访了我,他兴致很高(这是他的习惯)。“我们生活在一个有趣的时代”,他说,“*在所有地方都是激进的。它在任何一个体系、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批判性的:在美国,在苏联,在日本,在菲律宾,在非洲和拉丁美洲——在所有地方”。这个既老又新、既简单又复杂、既显而易见又模糊不清的观念,是有吸引力的。当看到有一个人对这样一个原则——据福斯特(Forster)讲,这个原则只值得欢呼两下,但绝不值得欢呼三下——如此兴致勃勃,我是感到很好奇的。
大约在相同的时候,有人从美国寄来一封信说,有一本名为《*》的杂志,并询问我在日本是否有激进*主义者可以举荐为这本杂志撰稿。“激进*”这个观念开始植入我的脑海。这种经验有点像你开始爱上邻家的一位姑娘(或小伙),那种感觉你一直知道但突然变得那样新鲜、那样鲜明、那样……无有前例。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在美国以及在日本,我一直是某种类型的运动积极分子,但像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主义者这道槛,我未跨过,只是一直借重*主义对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和自由主义的经济学的批判力量。在那些年代的运动政治学中,*主义被解释为和*左翼有一定的距离,即是说比*左翼要激进;在另一方面,*主义者被解释为站在*主义者和左翼自由主义者之间的地位上(并很难和后者区分开)。从法国大革命以来,左—中—右这样的空间性的隐喻对于安置我们政治学的方式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力量。一个人的政治定位如果是被认为在另外的两种政治倾向之间,这种定位很难避免被想象为是一种妥协、杂糅,并且没有自己独立清晰的原则。我开始感觉到鹤见马洛的定律(“*在所有地方都是批判性的”)能够成为重新安排这个空间性的形象的基础。*既然像激进主义一样被认为是激进的,所有其他的政治定位和这些政治定位之间的关系将呈现一种新的面貌。这将导致对政治现实作出更精确的反思,以及以一种方式赋予*理论更强的批判力量。
从我最初为这本书的观点开始构思算起,十多年过去了。在此期间,在诸如波兰、缅甸、菲律宾等不同的国家中发生了激烈的*运动,同时在*理论领域产生了新的一波作为。在很多年中,任何一本题为《*》的书,基本可以判断为是在单调重复北方工业发达国家的所谓优点,但是称*为激进的一批理论家也出现了。当乔治·布什宣称在他的任期内*已经“胜利了”的时候,另外有人正建构或重新发现一种*观念,这种*观念不仅可以作为对罗纳德·里根和乔治·布什,而且可以作为对里根和布什与其自由主义的反对派共有的意识形态框架进行批判的基础。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关于*的讨论第一次让人感兴趣。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贡献给这一讨论的。
很有趣的是,当我在菲律宾大学第三世界研究中心工作时,我不仅很难向在日本和美国的朋友,也很难向在菲律宾的朋友解释我的研究选择。我到菲律宾不是研究菲律宾本身,而是进行研究*理论的准备工作,这在他们看起来是很奇怪的。在这里有一个隐藏的偏见在作怪。如果一位在哈佛大学的访问学者不研究马萨诸塞的政治或文化,人们不觉得奇怪。一位在康奈尔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东南亚或一位在伦敦大学的访问学者去研究非洲,人们也不觉得奇怪。但反过来就不是如此:一位前往第三世界的访问学者就被认定要去研究第三世界。
我有意地选择菲律宾大学以打破这种固定观念,这符合这种一般原则:如果你打破某个固定的观念,你很可能将学到意想不到的事物。但是我选择菲律宾无论如何也不是偶然的。当时,1986年2月的人民权力革命刚过去一年。“人民权力”是希腊单词demos和kratia的英译。人民权力——激进*做了表面看起来不可能的事情:不仅通过人民赢得选举,而且通过人民冒着生命危险监督这场选举而获得选举胜利,人民将一个*的、有精良武装保护的、卑鄙而富裕的*者赶下台并赶出国。我想去这样一个地方,那里*不只是一个无力的口号而且是一个活的观念,一个真正重要的、人民以热情和投入来谈论的原则。事物并没有完全那样发展。尽管在马科斯政权的最后几年,公众情绪充满兴奋和激进希望,到1987年春天,公众情绪陷入了幻灭。激进希望——这是人*动的核心(我在第五章将更多地谈论这一点),已经制造了一种准确地说是革命的政治情境,但是这一希望的目标是一位自由主义的政客——正寻求赢得选举的科拉松·阿基诺。激进*在重建自由主义政治中消耗了自己的能量。土地改革搁浅了,内战在继续,1987年是阴郁的一年。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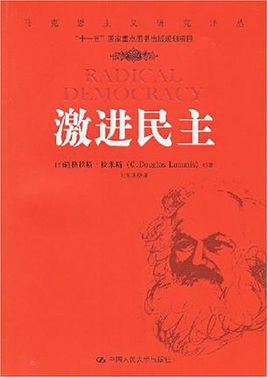 作者:拉米斯(美)
作者:拉米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