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由于人的嫉妒天性,发现新的方式和体制(modi ed ordini nuovi)总是与寻找未知的水源和土地一样危险(因为人们更易于指责而不是赞扬他人的行为);但是,在我心中一直有一种天生的欲望,即毫不犹豫地进行那些我认为会带给每个人共同福祉的事情。受这种欲望的驱使,我下定决心进入一条还没有人走过的道路,虽然这可能给我带来辛劳和困难,但它也可能通过那些善意地看待我付出这些辛劳的目的的人,给我带来奖赏。即使才智贫乏、对当代事物的经验欠缺和对古代事物的肤浅的了解,使我的这种尝试存有缺陷,并没有很大的用处,但它们至少给有些人指明了道路,这些人具有更高的德行,更强的分析、推理和判断力,将能够实现我的意图;这即使不能使我受到赞美,也不应该引起对我的指责。[这段开场白不见于《李维史论》最早的两个版本,但在唯一存世的《李维史论》手稿片段中,保留着经马基雅维利亲笔润色的原稿。对于它是草稿还是定稿,学界存在分歧,参见Carlo Pincin, La prefazione alla prima parte dei Discorsi, Atti dell Accademica Scienze di Torino 94 (1959-1960): II, 506-518; Le prefazione la dedicatoria dei Discorsi di Machiavelli, Giornale storica della letteratura, italiana 143 (1966): 72-83; Harvey C. Mansfield, Jr., Machiavelli s New Modes and Orders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79), 25n。
]
考虑一下世人对古代赋予多么高的荣誉,人们经常 且不谈无数其他例子 不惜重金购买一座古代雕像的残片,是为了将它随身携带,用它为自己的居室增光,使那些喜爱那种艺术的人能够效仿它,而这些人后来尽其所能在其所有的作品中表现它;从另一方面,看看历史向我们显示的,由古代的王国和共和国,由国王、将领、公民、立法者和其他为其祖国而不辞辛劳的人所做的极其有德行的行为,人们宁愿钦佩,也不去仿效它们(相反,每个人在所有最小的事情上都对它们避而远之,以致古代德行在我们身上踪迹全无),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惊诧同时又感到遗憾。就我看到的下列情形而言,更是如此:当公民之间产生市民法的争议,或者当人们患上疾病时,人们总是求助于古人所判定的裁决,或者古人所指示的药方。因为市民法不是别的,只是古代法学家所作出的判决,它们被归纳整理得有序,指引我们今天的法学家做出裁决;医术也只不过是古代医生所经历的经验,在其基础上今天的医生做出自己的诊断。然而,在整饬共和国、维护国家、统治王国、整训部队和作战、审判属民、扩张帝国时,却没有哪个君主,也没有哪个共和国或将领求助于古人的例子。我认为,这种状况不只是源于当今的宗教[有的版本作“当今的教育”。
]使世界陷于虚弱,或者有野心的懒散给许多基督教地域和城市造成的损害,更是源于没有对历史的真正了解,因为在阅读历史时,既没有从它们中获取其意蕴,也没有品味到它们所具有的趣味。由此导致无数人阅读史书,沉湎于其中包含的各种历史掌故,却从来不曾想去效仿,他们断定这种效仿不仅困难,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就仿佛苍穹、太阳、各种元素和人类自身在运动、秩序和力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今时已不同于往日了。
因此,为了使世人摆脱这种错误,我决定,对于未被时光的流逝所毁损的提图斯·李维的所有那些卷册,[李维的《自建城以来》,即习称的《罗马史》,全书共计142卷,目前保留下的只有35卷(第1-10卷,第21-45卷),其余各卷除个别片段以外已散失。此外,尚有后人编写的全书各卷的摘要(Perioohae/ Summaries)存世。
]有必要记下我根据对古代和现代事物的了解,认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所必要的内容;以便那些读我的这些评论的人能够更容易地从中获得助益,而这种助益正是人们必须力求了解历史的目的之所在。虽然这项事业很艰巨,但在那些鼓励我担此重任的人的帮助下,我试图从事这项工作,以便留给他人较短的路程来完成它。
第一章 城邦的起源一般而言是什么样的,罗马的起源是什么样的
那些读过罗马城是如何起源,由哪些立法者、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的人不会感到惊奇,那个城邦数个世纪来维持了如此大的德行,并且后来从那个共和国中发展出那个帝国。我首先想要谈谈它的诞生,我要说,所有城邦要么是由城邦建立地本土出生的人建立的,要么是由外人建立的。前一种情形发生于分散为许多小部分的居民认为生活不安全,由于所处的位置以及人数少,每个部分自身都不能抵抗袭击他们的人的进攻;当敌人到来时,要聚集起来进行防守在时间上来不及,或者,即使来得及聚集起来,也得放弃他们的许多据点,从而立即被其敌人所俘获:如此这般,为了避免这些危险,由他们自己发动,或者在他们中具有较高威信的某个人的发动下,他们聚拢起来共同居住在由他们选定的、更便于生活和更易于防守的地方。
属于这类情形的城邦有许多,其中就有雅典和威尼斯。前者在提修斯的权威下,出于相似的原因,由分散的居民建立。[参见P 6, 26;Plutarch, Thescus, 24-25; Thucydides, II 15。
]后者,由于许多居民已退居到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海岬的一些岛屿上,以躲避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每次新的蛮族人到来就会在意大利爆发的那些战争;[关于威尼斯的起源,见FH II 29, Livy I 1。
]在他们中,没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某个特定君主,这个城邦开始生活在他们认为更适于维持它的那些法律之下。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地理位置使他们得以高枕无忧,因为那个海洋没有出口,并且那些损害意大利的民族也没有船只能够侵扰他们;因此,每个小的开端,都能够使他们变得如现在那样的伟大。
第二种情形,即由外人建立的城邦,它或者产生于自由人,或者产生于依附于他人的人,如同某个共和国或君主派遣的那些移民一样,派遣移民是为了减轻他们的原住地的负担,或者是为了保护新获得的国土,他们想要安全可靠地、而又不付代价地让它自我维持下去(这些城邦罗马人建有许多,遍布整个帝国);或者,这些城邦的建立,是由一个君主不是为了在那里居住,而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而为之,例如由亚历山大建的亚历山大城。由于这些城邦没有自由的起源,它们很少取得巨大成就,也很难进入王国的首要城市之列。佛罗伦萨的建立与此相似,因为(它或者是由苏拉的士兵所建,或者是由菲耶索莱山上的居民偶然建立的,后者相信在屋大维的统治下世间产生的长期太平,故退回到阿诺河畔的平原上居住)它是在罗马的统治下建立的,在它创立之初,除了君主慷慨赐予它的那些扩张之外,它不可能进行别的疆界扩张。[关于佛罗伦萨的起源,见FH II 2。
]
当一些民族,无论他们是受一个君主的统治,还是实行自治,由于疾病、饥荒或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为自己寻找新的住所的时候,城邦的创建者是自由的:这些人,或者定居于他们在其征服的土地上发现的那些城市,摩西就是这样做的;或者重新建立城市,埃涅阿斯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创建者的德行和所创建的城市的运气:这种运气是否令人惊奇,要看最开始的创建者德行的多寡。创建者的德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了解:一种方式是城址的选择,另一种方式是法律的制定。由于人们的行为或者出于必然性,或者出于选择;并且人们看到,选择余地越小,德行越多,因此要考虑是否选择贫瘠之地建城更好些:这样,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不被怠惰所占据,更加团结地生活,由于地方穷,也较少有骚乱的理由,如同在拉古萨和许多其他的在这类地方建立的城市所发生的一样;如果人们满足于过自己的生活,不想力求控制他人,那么这种选择无疑较为明智和有益。
因此,如果人们除了凭实力之外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避开这种贫瘠之地,而安置于肥沃富庶之地,在这些地方,由于土地肥沃而能够扩张自己的领土,故城市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他人攻击,并镇压任何与其强大作对的人。至于这种地方带给城市的那种懒散,应当规定法律,对它强加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所不强迫的那些要求;并应当仿效这样一些人,他们很明智:居住在极其惬意和肥沃富庶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易于产生懒散的人,不能胜任各种英勇的训练,为了避免土地的适意和那种懒散可能造成的那些损失,他们向那些当兵的人提出了操练的要求;这样,通过这种体制,他们在那里成为比在那些自然条件很艰苦和贫瘠的国家更好的士兵。埃及人的王国即属此类,尽管这个国家极其适意,由法律命令的那个要求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最杰出的人;如果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在古代就被遗忘,就可能看到他们应受的赞颂是如何超过亚历山大大帝和许多其他的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人。只要看看在被土耳其大帝塞利姆消灭之前的苏丹王国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Mammalucchi/ Mamelukes),1250-1517年统治埃及的穆斯林军事阶层。
]及其军队的体制,就可以看到其中对士兵的许多训练;并且实际上可以认识到,他们是多么惧怕土地肥沃可能将他们引致的那种懒散,对此只能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来避免。
因此,我说,选择在肥沃之地安置是较为明智的,只要通过法律规定将那种肥沃的可能不利后果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想为自己的荣誉建立一座城市,建筑师狄诺克拉底来到他那儿,向他进言说自己如何能够在阿索斯山上建这座城市:这个地方除了坚固之外,还可以进行改建,以至于可以将这座城市建成人的形状,这将是一个神奇而少见的事物,配得上他的伟大。亚历山大问他居民靠什么生活,他回答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亚历山大置之一笑,没有理会那座山,而是把亚历山大城建在了土地肥沃、有海洋和尼罗河之便,故而居民愿意居住的地方。[这个故事见Vitruvius, Preface, II 1-4;它被托马斯·阿奎那所转述,见Thomas Aquinas, On Kingdom, II 7;参见Plutarch, Alexander, 26。
]
考虑一下世人对古代赋予多么高的荣誉,人们经常 且不谈无数其他例子 不惜重金购买一座古代雕像的残片,是为了将它随身携带,用它为自己的居室增光,使那些喜爱那种艺术的人能够效仿它,而这些人后来尽其所能在其所有的作品中表现它;从另一方面,看看历史向我们显示的,由古代的王国和共和国,由国王、将领、公民、立法者和其他为其祖国而不辞辛劳的人所做的极其有德行的行为,人们宁愿钦佩,也不去仿效它们(相反,每个人在所有最小的事情上都对它们避而远之,以致古代德行在我们身上踪迹全无),对此我不能不感到惊诧同时又感到遗憾。就我看到的下列情形而言,更是如此:当公民之间产生市民法的争议,或者当人们患上疾病时,人们总是求助于古人所判定的裁决,或者古人所指示的药方。因为市民法不是别的,只是古代法学家所作出的判决,它们被归纳整理得有序,指引我们今天的法学家做出裁决;医术也只不过是古代医生所经历的经验,在其基础上今天的医生做出自己的诊断。然而,在整饬共和国、维护国家、统治王国、整训部队和作战、审判属民、扩张帝国时,却没有哪个君主,也没有哪个共和国或将领求助于古人的例子。我认为,这种状况不只是源于当今的宗教[有的版本作“当今的教育”。
]使世界陷于虚弱,或者有野心的懒散给许多基督教地域和城市造成的损害,更是源于没有对历史的真正了解,因为在阅读历史时,既没有从它们中获取其意蕴,也没有品味到它们所具有的趣味。由此导致无数人阅读史书,沉湎于其中包含的各种历史掌故,却从来不曾想去效仿,他们断定这种效仿不仅困难,而且是不可能的;这就仿佛苍穹、太阳、各种元素和人类自身在运动、秩序和力量等方面已经发生了变化,今时已不同于往日了。
因此,为了使世人摆脱这种错误,我决定,对于未被时光的流逝所毁损的提图斯·李维的所有那些卷册,[李维的《自建城以来》,即习称的《罗马史》,全书共计142卷,目前保留下的只有35卷(第1-10卷,第21-45卷),其余各卷除个别片段以外已散失。此外,尚有后人编写的全书各卷的摘要(Perioohae/ Summaries)存世。
]有必要记下我根据对古代和现代事物的了解,认为是为了更好地理解它所必要的内容;以便那些读我的这些评论的人能够更容易地从中获得助益,而这种助益正是人们必须力求了解历史的目的之所在。虽然这项事业很艰巨,但在那些鼓励我担此重任的人的帮助下,我试图从事这项工作,以便留给他人较短的路程来完成它。
第一章 城邦的起源一般而言是什么样的,罗马的起源是什么样的
那些读过罗马城是如何起源,由哪些立法者、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的人不会感到惊奇,那个城邦数个世纪来维持了如此大的德行,并且后来从那个共和国中发展出那个帝国。我首先想要谈谈它的诞生,我要说,所有城邦要么是由城邦建立地本土出生的人建立的,要么是由外人建立的。前一种情形发生于分散为许多小部分的居民认为生活不安全,由于所处的位置以及人数少,每个部分自身都不能抵抗袭击他们的人的进攻;当敌人到来时,要聚集起来进行防守在时间上来不及,或者,即使来得及聚集起来,也得放弃他们的许多据点,从而立即被其敌人所俘获:如此这般,为了避免这些危险,由他们自己发动,或者在他们中具有较高威信的某个人的发动下,他们聚拢起来共同居住在由他们选定的、更便于生活和更易于防守的地方。
属于这类情形的城邦有许多,其中就有雅典和威尼斯。前者在提修斯的权威下,出于相似的原因,由分散的居民建立。[参见P 6, 26;Plutarch, Thescus, 24-25; Thucydides, II 15。
]后者,由于许多居民已退居到位于亚得里亚海的海岬的一些岛屿上,以躲避在罗马帝国衰落后每次新的蛮族人到来就会在意大利爆发的那些战争;[关于威尼斯的起源,见FH II 29, Livy I 1。
]在他们中,没有对他们发号施令的某个特定君主,这个城邦开始生活在他们认为更适于维持它的那些法律之下。他们之所以获得成功,是因为地理位置使他们得以高枕无忧,因为那个海洋没有出口,并且那些损害意大利的民族也没有船只能够侵扰他们;因此,每个小的开端,都能够使他们变得如现在那样的伟大。
第二种情形,即由外人建立的城邦,它或者产生于自由人,或者产生于依附于他人的人,如同某个共和国或君主派遣的那些移民一样,派遣移民是为了减轻他们的原住地的负担,或者是为了保护新获得的国土,他们想要安全可靠地、而又不付代价地让它自我维持下去(这些城邦罗马人建有许多,遍布整个帝国);或者,这些城邦的建立,是由一个君主不是为了在那里居住,而是为了他自己的荣誉而为之,例如由亚历山大建的亚历山大城。由于这些城邦没有自由的起源,它们很少取得巨大成就,也很难进入王国的首要城市之列。佛罗伦萨的建立与此相似,因为(它或者是由苏拉的士兵所建,或者是由菲耶索莱山上的居民偶然建立的,后者相信在屋大维的统治下世间产生的长期太平,故退回到阿诺河畔的平原上居住)它是在罗马的统治下建立的,在它创立之初,除了君主慷慨赐予它的那些扩张之外,它不可能进行别的疆界扩张。[关于佛罗伦萨的起源,见FH II 2。
]
当一些民族,无论他们是受一个君主的统治,还是实行自治,由于疾病、饥荒或战争而被迫背井离乡,为自己寻找新的住所的时候,城邦的创建者是自由的:这些人,或者定居于他们在其征服的土地上发现的那些城市,摩西就是这样做的;或者重新建立城市,埃涅阿斯就是如此。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看出创建者的德行和所创建的城市的运气:这种运气是否令人惊奇,要看最开始的创建者德行的多寡。创建者的德行可以通过两种方式来了解:一种方式是城址的选择,另一种方式是法律的制定。由于人们的行为或者出于必然性,或者出于选择;并且人们看到,选择余地越小,德行越多,因此要考虑是否选择贫瘠之地建城更好些:这样,人们不得不想方设法,不被怠惰所占据,更加团结地生活,由于地方穷,也较少有骚乱的理由,如同在拉古萨和许多其他的在这类地方建立的城市所发生的一样;如果人们满足于过自己的生活,不想力求控制他人,那么这种选择无疑较为明智和有益。
因此,如果人们除了凭实力之外无法保障自身安全,就必须避开这种贫瘠之地,而安置于肥沃富庶之地,在这些地方,由于土地肥沃而能够扩张自己的领土,故城市能够保护自己免受他人攻击,并镇压任何与其强大作对的人。至于这种地方带给城市的那种懒散,应当规定法律,对它强加它所在的地理位置所不强迫的那些要求;并应当仿效这样一些人,他们很明智:居住在极其惬意和肥沃富庶的地方,而这些地方易于产生懒散的人,不能胜任各种英勇的训练,为了避免土地的适意和那种懒散可能造成的那些损失,他们向那些当兵的人提出了操练的要求;这样,通过这种体制,他们在那里成为比在那些自然条件很艰苦和贫瘠的国家更好的士兵。埃及人的王国即属此类,尽管这个国家极其适意,由法律命令的那个要求有如此大的影响,以至于产生了最杰出的人;如果这些人的名字不是在古代就被遗忘,就可能看到他们应受的赞颂是如何超过亚历山大大帝和许多其他的我们仍然记忆犹新的人。只要看看在被土耳其大帝塞利姆消灭之前的苏丹王国和马穆鲁克[马穆鲁克(Mammalucchi/ Mamelukes),1250-1517年统治埃及的穆斯林军事阶层。
]及其军队的体制,就可以看到其中对士兵的许多训练;并且实际上可以认识到,他们是多么惧怕土地肥沃可能将他们引致的那种懒散,对此只能通过强有力的法律来避免。
因此,我说,选择在肥沃之地安置是较为明智的,只要通过法律规定将那种肥沃的可能不利后果限制在可接受的范围内。亚历山大大帝曾经想为自己的荣誉建立一座城市,建筑师狄诺克拉底来到他那儿,向他进言说自己如何能够在阿索斯山上建这座城市:这个地方除了坚固之外,还可以进行改建,以至于可以将这座城市建成人的形状,这将是一个神奇而少见的事物,配得上他的伟大。亚历山大问他居民靠什么生活,他回答说,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亚历山大置之一笑,没有理会那座山,而是把亚历山大城建在了土地肥沃、有海洋和尼罗河之便,故而居民愿意居住的地方。[这个故事见Vitruvius, Preface, II 1-4;它被托马斯·阿奎那所转述,见Thomas Aquinas, On Kingdom, II 7;参见Plutarch, Alexander, 26。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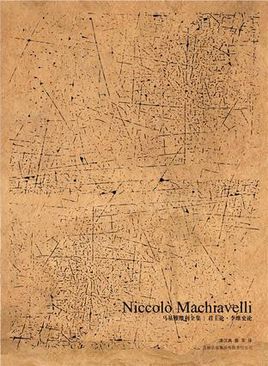 作者:马基雅维利(意)
作者:马基雅维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