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张之洞与他的时代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人又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关系。
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1811—1872)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鸿章(1823—1901)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1785—1850)率先“开眼看世界”,林氏的朋友魏源(1794—1857)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②。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1833—1898)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1810—1882)、俞樾(1821—1907)、黄以周(1828—1899)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1728—1804)、王念孙(1744—1832)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腐败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毛泽东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生平篇——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第一节 世宦之家
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依然传诵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本书传主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迁徙人流中。
张本从洪洞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一带),安下家来。经过两代耕读,张本的孙子张端,官居南直隶繁昌县获港巡检,又举家迁至天津府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张氏家族从此定居于此,声名渐盛,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①。张淮七传至乃曾,即之洞高祖,为清代山西孝义知县,乃曾之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具令,皆以廉惠闻”②。之洞祖父廷琛,字献侯,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题补古田知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闽浙总督伍拉那等贪污、纵盗案,督抚藩臬十余要员下狱,牵连甚广。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多方“调护拯救”,甚获时誉。
之洞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493年),早年丧父,家境窘迫,“食贫力学”③,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中举。张锳将家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举后,张锳屡赴会试不第,以大挑④补贵州安化知县,又调贵筑知县,后迁古州同知,擢兴义知府(所辖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张锳一生三娶。原配刘夫人,布政司经历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四川嘉定知府蒋策之女。再娶朱夫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朱夫人生之洞于兴义知府官舍⑤。之洞以上,有一个哥哥之渊,以下有两个弟弟之澄、之涌,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之清因父早亡,也被张锳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庭。
道光二十年(1840年),朱夫人病逝。三岁的之洞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却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①
生母死后,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母子感情甚笃。光绪十三年(1887年),魏氏卒于南皮。此时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闻报十分悲伤,“白衣冠为位而祭”,“循礼成服”。对魏氏亲属来粤者,亦“以戚谊待之”②。
张锳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侍授“乾嘉老辈诸言”③,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之洞四岁发蒙,从附生何养源受读。拔贡曾搢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赵斗山,进士敖慕韩,先后作过他的业师。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童年的之洞十分勤勉,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④学业因此大进。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兴义府署比邻试院,院内有天香阁,立树石佳胜之间。之洞读书习字、赋诗填词于其中,每得怡乐。他曾集此时诗文为一集,曰《天香阁十二龄草》①。张锳高兴地将其寄给之洞的伯父一阅,伯父复函以“敛才勿露”为最。之洞终身诵之。
十二岁以后,之洞又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孙、重云逵、袁燮堂、洪次庚、吕文节、刘僊石、朱伯韩,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他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1812—1861)问业。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胡编《年谱》卷一。
①集中诗文存于张锳主纂《兴义府志》,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许编《年谱》,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清乾隆以后定制,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由国家挑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挑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
⑤此据许同莘《年谱》和胡钧《年谱》。另据刘显世等修《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道光十七年,张锳尚在贵筑知县任内,按此说,则之洞的出生地应为贵筑知县官舍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人是历史的主体。历史发展固然有其必然规律,但这丝毫也不排斥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当然,人又不是单个人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人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个人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创造历史,他们的活动总要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发生复杂的交互关系。
本书传主张之洞(1837—1909)是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晚清社会的产儿,他又发挥了极大的主观能动性,对这个转型时代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文化、教育等诸多侧面打上鲜明印记;他的心路历程,从一个特定的角度相当典型地反映了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年间中国社会走过的曲折坎坷的路径。
本书传主辞世已久,人们却难以忘怀他的创榛辟莽的业绩和新旧杂糅的思维教训。时至二十世纪中叶,毛泽东(1893—1976)在论及中国近代工业发展史时还特别强调:讲到重工业,不能忘记张之洞①;学界泰斗陈寅恪(1890—1969)在三十年代则自称,“平生为不古不今之学,思想囿于咸丰、同治之世,议论近乎曾湘乡张南皮之间”②,足见今人或者不时感受到张氏的遗泽,或者难以摆脱这位“文襄公”的思想轨范。
将张之洞与曾国藩(1811—1872)并列为咸同以降对人们的思想和议论发生久远影响者,自有一番道理。处于社会转型阶段的中国近世,涌现出竞相寻求“过渡之道”的众多风云人物,就清廷内部言之,探求过渡之道而又兼具政坛要角、学术重镇双重身份的,惟曾、张二位。以张之洞论,他留给后世的遗产包括斑驳陆离的政治实绩和古今交汇、中西并存的学术两大部类。品议政治家的张之洞,应当着重前者,兼顾后者;评析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必须详剖后者,而又不可脱离前者。
古人将“立德、立功、立言”称作人生“三不朽”。张之洞是深识此中三昧的,他除力图建树功业外,还十分重视“立言”,终身亲治文书,不假手幕客,这与李鸿章等其他洋务大吏颇不相同。一部数百万言的《张文襄公全集》,多出自张氏本人手笔,这为研究张之洞的思想言行提供了系统的一手资料。然而,《张文襄公全集》这部书究竟应当怎样阅读?这里用得上孟子的名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①读书须知人,知人须论世,这是评价历史人物的通则;考察张之洞这位既由时势所造,又深刻影响时势的人物,尤其要以“知人论世”为人门之径。
张之洞的人生跨度,迈越咸、同、光、宣诸朝,这不仅是清王朝的衰败之世,而且也是中国数千年农业一宗法社会发生剧变的时期。这种“千古之奇变”的根由,除深植于中国国内诸多社会矛盾之外,还在于世界历史已经运行到一个崭新的阶段,无论中国人愿意与否,都无可避免地要卷入这种亘古未遇的“变局”之中。
自十六世纪开始,世界历史逐步从诸区域性文明各自生灭走向全球性文明一体化发展。推动这种历史性转折的是南欧和西欧竞相生长起来的资本主义所焕发出的巨大生产力,以及与之相伴随的对远方异域的扩张力。以英吉利、法兰西为代表的西欧诸国,历经原始积累、产业革命、政治变革,到十九世纪,资本主义已获得较充分的发育,其海外殖民活动的广度和深度更达到新的水平。继中东、南亚之后,地处远东的广土众民的中华帝国也成为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经济渗透、军事侵略的重要对象,商品、鸦片、坚船利炮一并向其袭来,老大的清王朝几无招架之功,闭关锁国状态被强行打破。李鸿章(1823—1901)陈述中国历史上这种空前严峻的形势说:
历代备边,多在西北,其强弱之势,客主之形,皆适相埒,且犹有中外界限。今则东南海疆万余里,各国通商传教,来往自如,麇集京师及各省腹地,阳托和好之名,阴怀吞噬之计,一国生事。诸国构煽,实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轮船电报之速,瞬息千里,军器机事之精,工力百倍,炮弹所到,无坚不摧,水路关隘,不足限制,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①中国历代诸中原王朝曾多次受到来自西北的游牧人的军事威胁,然而,这些游牧人虽有强劲武功,其整个文明水平却大大低于中原农耕文明,因此,中原人可能被游牧人所征服,最终却通过自己的高势位文化反过来同化征服者。但是,十九世纪中叶以降的格局却大异于以往,中国人固有的文化优势已经丧失,诚如李鸿章满怀惊恐指出的,古老的中国历经着“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亿万中国人面对“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自成一体的中华文化无可回避地纳入全球近代文化的大潮中,经受前所未遇的磨难,自觉不自觉地进行重组和转型。这里所谓的“重组”,是指经过中西文化的碰撞和融合,中华文化的固有格局发生解体,重新进行结构组合;所谓的“转型”,是指从中古时代自然经济的农耕文化转向近代商品经济的工业文化。本书传主正是在这古今中西大交汇的关口,以干练务实的朝廷大员和淹博深厚的学者的双重身份,感受着时代的变迁,并随着变迁的时代改变着自身,又力图左右时代的更化方向,在“求变”与“守常”的矛盾过程中,完成其人生之旅,刻画出复杂多致的思想一实践轨迹。
张之洞生命的节律与中国近代历史大体共始终。他的一生,或耳闻目睹、或亲身参与中国近代史上的许多重大事件。作为“身系朝局疆寄之重者四十年”的政治家,他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戊戌变法、义和团运动中都扮演了举足轻重的角色,更在洋务运动和清末”新政”中成为“朝廷柱石”;而作为涉猎广泛、富于锋芒的思想家,张之洞的所思、所言往往新旧纷呈、中西并列,活现出中国近代文化变迁的曲折与艰难。
无论从历史条件或者个人作为来看,张之洞都是典型的“过渡型”人物。东方中古传统与“欧风美雨”所驱动的近代化潮流,在他头脑里相激相荡。他的基本立足点是中国传统文化,既承袭其“经世”、“变通”、“自强”等积极意识,力图顺应时势,通过有限度的汲纳西学,革故鼎新;同时又深荷纲常名教的重负,以卫道者自居,不免抱残守缺之讥。这一切铸就了他复杂多面的性格,支配其在近代舞台上或顺乎时代潮流,或阻挡历史车轮的诸般表演。
张之洞作为历史过渡人物的典型意义,尤其在于他的思想与言行的发展轨迹与近代中国这一过渡时代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着或丝丝入扣,或有所错位的关系。张氏作为一员有作为的“能吏”,参与清廷同光间“御外”和”靖内”的各项主要活动,同西方列强、朝中各党、民众运动诸流派均发生错综复杂的关系;同时,他又以通权达变者和“圣教”捍卫者的双重身份,投入近代中国的思想战线,既抨击守旧者的“不知通”,又讨伐求新者的”不知本”,然而他本人也未能寻觅到“因”与”革”,“常”与“变”的合理统一。因而一部张之洞传,在相当的意义上,显示出中国近代史。特别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的矛盾性和复杂性。
清道光二十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这一年,张之洞刚满三岁。这一场战争的时代意义,当然不是一个孩童所能理解,但它所造成的历史震动,渐次深入地作用于中华民族器物文化、制度文化和心态文化的各个层面,而这一切,又给予青年、壮年及老年张之洞以深刻影响,并制约了他的一生。
鸦片战争以石头城下一纸屈辱条约的签订而告终。西方资本主义文明通过野蛮的暴力和无耻的鸦片贸易撬开中华帝国封闭的大门。严酷的现实危机感,逼迫着中国人在超越九州之内王朝更迭的广阔的时空坐标系中为国家、民族重新确定位置,寻求出路。林则徐(1785—1850)率先“开眼看世界”,林氏的朋友魏源(1794—1857)则较系统地阐述了这样做的必要性:“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所以,中国人必须”师夷长技以制夷”①。不过,魏源所谓的“师夷长技”,主要局限于坚船利炮等器物文化层面,虽偶有赞扬西方社会制度的言词,却没有明确的仿效意向。总之,魏氏的“师夷”,还只是表达了一种先进士人的认知态度,社会并没有付诸实行,因而既未赢得热烈的响应,也未遇到激烈的反对。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六十年代。
这一阶段,张之洞尚在青少年时朗。此间他生活于闭塞的贵州等地,林、魏辈的思想尚无影响可言,沿着科举之途勤奋跋涉,则是其心力所寄。两次鸦片战争给中国带来的灾祸,也曾给青年张之洞的心头罩上阴影,咸丰十年(1860年),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张之洞感愤时事,诗以纪之①。不过,此时他孜孜以求的,仍然是”明体而达用,化民而成俗”的“帝王之学”②。同治二年(1863年)科考殿试一甲第三(俗称“探花”)的张之洞的精神状况,同当时绝大部分中国士人一样,震怵于民族危机,却又找不到解救出路,仍在传统故道上踯躅徘徊。
六十年代以后,西方器物文化的先进性,得到逐渐增多的中国人的承认,魏源当年的“师夷”说,此时具体化为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奕(1833—1898)等人兴办“洋务”的实践。“师夷”口号一旦落实为行动,立刻招致社会习惯势力的顽强抵制。“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申,邪气因而弥炽”③的责难蜂起。张之洞并不是洋务先进,当李鸿章辈亟亟兴办江南制造总局,勤于“夷务”的六、七十年代,张之洞或为外省学政,或为京师清流。所受教养及个人经历,使他“尚知六经大旨,以维持名教为己任”④。但执著于经世之志的张之洞又有别于“以不谈洋务为高”的一般“清流”同党,对洋务派兴办的近代化事业很少进行实质性的批评,而且认为“塞外番僧,泰西智巧,驾驭有方,皆可供我策遣。”
由于张之洞素有励精图治的意气和长于权变的机智,当他走出京官清流圈子,踏上封疆大吏之途以后,目睹中外大势,参酌诸洋务先进的前例,迅速从清流党向洋务派转化。他八十年代初在山西巡抚任上发布的启示宣称:“盖闻经国以自强为本,自强以储才为先,方今万国盟聘,事变日多,洋务最为当务之急”②。这番话可视作他从京师清流一变而为洋务大员的标志。由晋抚移督两广,经历中法战争的教训,张之洞以更加切实的步骤实施洋务计划。
“效西法—图富强”以便”保中国”进而“保名教”③,成为张之洞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基本思路,这不仅意味着张氏个人随“天下大局一变”而与时俱进,而且报告了一种社会心理变迁的时代消息。
纵观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中国民众的普遍心态,虽然经受了被西方资本主义殖民者一再战败的打击,却只承认“器不如人”、“技不如人”,而并未意识到固有的精神文明尚有改进的必要。从学术文化而论,此时中国士子的学问方向仍在传统故道中运行,其论著极少得见西学影响的痕迹。咸丰、同治、光绪间大儒陈澧(1810—1882)、俞樾(1821—1907)、黄以周(1828—1899)等人著作的思想及其表述方式与钱大昕(1728—1804)、王念孙(1744—1832)等乾嘉老辈并无二致;张之洞七十年代在四川学政任上所撰《輶轩语》和《书目答问》,除涉及个别西书外,其内容与言词均未越出传统学问的范围。这与其说表现了士子们对西学有意识的抵制,不如说是对西学的无视和淡漠。可见,截至中法战争前,中华文化的观念层面“古井无波”的状态并未发生根本变化。
然而,伴随着西方物质文明的输入,以坚船利炮和廉价工业品开路,西方资本主义的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也无可阻遏地涌进中国,如科学理论(生物进化论、血液循环学说)、民主思想(天赋人权论、社会契约论)、政治制度(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社会风俗(有父子之平权、无男女之大防)、宗教信仰(原罪救赎、末日审判)等等纷纷传人,其强度则与日俱增。从中法战争到中日战争十年间(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至九十年代中期),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发生着明显变化,张之洞也在此间成为直追李鸿章的洋务巨擘,并因“湖北新政”的实绩和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竭力主战而赢得“天下之望”。这十年应视作张之洞一生的黄金时段。
甲午战争中国惨败,而且是败于素为中国人所蔑视的东瀛岛国,这给中华帝国这头“睡狮”以剧烈震撼,康有为泣血以诉:“瓜分豆剖,渐露机芽”;谭嗣同长歌当哭:“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以政治变法与思想启蒙为双重目的的维新运动勃然而兴。从甲午到戊戌,中国思想界出现了自两千多年前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以后所罕见的热烈气象。曾经因力倡“师夷智”以”救时”而一领风骚的洋务派,在“变政”任务提出后则显出落伍于时代的窘态。
这一时期,张之洞思想的内在矛盾渐趋激烈和外显。一方面,他进一步感受到国势衰败的危机,继续将洋务事业推向前进,两湖、两江地区的实业建设、学堂创办、新军操练均有发展;另一方面,作为受儒教熏陶而且又执掌权柄的高级官员,他又忧心忡忡于日益昭彰的“新学”对名教纲常的冲击。如果说,十九世纪中叶李鸿章深怀忧虑地指出中国面临“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是指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给中国造成的威胁,那么,十九世纪末叶张之洞更进而担心中国人自身对中古传统的叛逆将导致固有国家政体和社会结构、伦常规范的崩解,他惊呼:“学者摇摇,中无所主,邪说暴行,横流天下。”“吾恐中国之祸,不在四海之外,而在九州之内矣”①,为此,他修撰出平生最重要的著作《劝学篇》。《劝学篇》的宗旨是“激发忠爱,讲求富强,尊朝廷,卫社稷”②,张之洞以此表明自己既与康有为等“激进”的“乱党”划清了界限,但又绝非抱残守缺的顽固“冬烘”,从而确立了自己在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上的特定地位。
西太后以血腥手段扑灭戊戌维新,但清王朝也从此陷入更严重的统治危机。义和团风暴席卷北中国,八国联军的铁蹄蹂躏京畿。在从戊戌到庚子一片混沌的政治风云变幻之中,张之洞纵横捭阖,翻云覆雨,作出淋漓尽致的权术表演。他主谋策划“东南互保”,以免“全局瓦解,不可收拾”。此间他与朝廷、列强及保皇派、革命党诸方面周旋折冲,干练老辣、机敏莫测。
进入二十世纪,“山雨欲来风满楼”。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及清王朝一并走向生命的尽头。老迈年高的张之洞,也由“久任疆寄”的地方大吏迈入朝廷中枢,成为“第二次洋务运动”——清末“新政”的主角。此时张之洞“开新”与“卫道”的二重变奏仍在继续,不过,由于腐败朝政病入膏盲,“开新”已绝无起死回生之可能,“卫道”的种种努力在不可阻挡的革命风潮面前,也越发显现出逆历史潮流而动的愚顽。宣统元年(1909年)八月,垂垂老矣的张之洞心力交瘁,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①的悲凉感叹中撤手人寰,此时距离武昌城头那划时代的首义枪声打响,已不足八百个昼夜。
作为一个敏锐而言于历史感的思想家,张之洞对于自己所处的时代,有其独特的观照角度和结论,这正是他作为政治家谋身行事的依据。在《劝学篇》中,他论及中外大势时说:今日世变,岂特春秋所未有,抑秦汉以至元明所未有也。②这与此前李鸿章“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之说,以及薛福成(1838—1894)在《变法》一文中所言“华夷隔绝之天下,一变而为中外联属之天下”③,是近似认识。张之洞还从比较历史学的角度,分析“今日之世变”发生的因由:欧洲各国开辟也晚,郁积勃发,斗力竞巧,各自摩厉,求免灭亡,积惧成奋,积奋成强。独我中国士夫庶民,情然罔觉,五十年来,屡鉴不悛,守其傲情,安其偷苟,情见势继,而外侮亟矣。
张之洞明确反对以种族优劣来说明西方进步而中国停滞的严酷现实,他设问道:“岂西人智而华人愚哉?”并进而分析西方“开辟也晚”,”进境尤速”的原因:欧洲之为国也多,群虎相伺,各思吞噬,非势均力敌,不能自存。故教养富强之政,步天测地、格物利民之技能,日出新法,互相仿效,争胜争长。且其壤地相接,自轮船、铁路畅通以后,来往尤数,见闻尤广,故百年以来,焕然大变,三十年内,进境尤速②。
这种议论显然是从当时盛行的进化论中导出:欧洲的进步是竞争的产物。张之洞继而指出,与西方世界“争胜争长”的情形相比,老大的中国则是另一番景象:傫然独处于东方,所与邻者,类皆陬噬蛮夷,沙漠蕃部,其治术学术,无有胜于中国者,惟是循其旧法,随时修饬,守其旧学,不逾范围,已足以治安而无患,迨去古益远,旧弊日滋,而旧法、旧学之精意渐失,今日五洲大通,于是相形而见继矣。张氏不无婉惜地议论:”西国强盛开通,适当我圣祖高宗之朝”,假使“其时朝廷恢豁大度,不欺远人,远识雄略,不囿迂论,而人才众多,物力殷阜,吾知必已遣使通问,远游就学,不惟采其法,师其长,且可引为外惧,藉以做我中国之泄沓,戢我中国之盈侈,则庶政百能,未必不驾而上之”②。在这里,张之洞颇抱怨清廷“开放”太晚,不能不说是一种觉悟者的反思。
张之洞对于时代面临剧变的估量,对于中国落后于西方的原因探讨,已越出传统陈说,显示出接纳新知的愿望,其直追异域先进,亟欲祖国富强的意向更溢于言表。他关于康熙年间若能开国师法远西,今必大盛的设想,也不失为智者之遐思。
历史毕竟不能假设,但历史却可以创造。张之洞不是幻想家,而是力行者,他“矢抱冰握火之志,持危扶颠之心,冀挽虞渊之落日”③,兴灭继绝,使中华“庶政百能”,对西洋“驾而上之”,他为此奔走呼号,辛勤劳作,其成败得失,留待后人评说。我们今天有充足的理由和证据来分析张之洞思想言行的新旧杂糅、自相矛盾,却无法否认张之洞在中国近代历史进程中的巨大份量——
作为政治家的张之洞,在“国步维艰,外患日棘,民穷财尽”的历史条件下,宵衣旰食,励精图治,确实有所作为,其实绩颇耸动中外,日本名臣伊藤博文(1841—1909)称其为中国第一能办事之人,实非过誉;然而,对于政治制度层面的变革和激烈的社会革命,张之洞又持不共戴天态度,故尔清末革命党人斥其为附鳞攀翼的汉奸,恨不能将其“头置于胯下”①,也是自有缘故的。作为思想家的张之洞,则在古今中西大交汇的浪潮中殚精竭虑,因革损益,留给后世一份丰富而驳杂的遗产。方面,张之洞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技术一艺能层面给予充分的接纳,表现出颇为大度的宽容和开明,这在其《劝学篇》的外篇中表述得酣畅淋漓;另一方面,他对新文化、新思想的政治—伦理层面又加以排拒、否定,口诛笔伐,展开殊死较量,《劝学篇》的内篇正显示了他卫道的执著和激昂。从结构上分析,一种文化包括外缘和内核,技术—艺能层面属于外缘,政治—伦理层面属于内核。张之洞作为以”保教”为职志的思想家,最大特点在于,当他感受到“圣教”受到根本性威胁时,企图通过变通其外缘来达到捍卫其内核的目的。他的这种努力的理论表现就是对”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时代“流行语”作出系统的阐发。他所钟情的这一文化范式具有相当大的涵盖性,虽有严复(1854—1921)、何启(1859—1914)、胡礼垣(1847—1916)等启蒙思想家对这一文化范式及时驳诘,但仍为众多的人们所认同,直至二十世纪初叶仍然如此。以“五四”为开端的新文化运动,以及此后数十年间,经过全民族吞吐融会古今中西文明成就的实践,方逐步突破“中体西用”樊篱,告别张之洞时代,但仍不能说张氏的思维模式己全然成为明日黄花,兼通中两的陈寅恪直至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还宣称自己的思想言论未能脱出其轨道,就是一个例证。
①见1907年《民报》特刊《天讨》所载”现代汉奸之真相”图片。
①毛泽东同时说,讲到轻工业,不能忘记张謇;讲到化学工业,不能忘记范旭东;讲到交通运输业,不能忘记卢作孚。转引自丁守和:《关于近代史人物研究和评价问题》,《近代史研究》1983年第4期。
②陈寅恪:《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下册审查报告》,《金明馆丛稿二编》,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1927年王国维自沉昆明湖,陈寅恪作挽词曰:“依稀廿载忆光宣,犹是开元全盛年。海宇承平娱旦暮,京年冠盖萃英贤。当日英贤谁北斗,南皮太保方遇叟。忠顺勤劳失素衷,中西体用资循诱。”可见陈氏对张之洞的景仰和对“中体西用”思想的服膺。
①《孟子·万章下》。
①《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②《劝学篇·内篇·同心第一》,《全集》卷二百零二。
①《全集》卷七十,奏议七十,《遗折》。
②《劝学篇·序》,《全集》卷二百零二。
③郑振铎编:《晚清文选》,上海书店1987年版,第218页。
①《劝学篇·内篇·知类第四》,《全集》卷二百零二。以下引《劝学篇》不标《全集》卷数。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①
②《劝学篇·外篇·益智第一》。
③胡钧:《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胡编《年谱》,北京天华印书馆民国二十八年版,甘朋云序。
①[清]宝鋆等辑:《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九六,第17页。重点号为本书作者所加。
①《海国图志叙》,《魏源集》,中华书局1976年版。
①见《张文襄公全集》,以下简称《全集),北京文华斋刻本,1928年版,卷二百二十四,诗集一,《海水》。
②《全集》,卷二百一十二,古文一,《殿试对策》。
③《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卷四十七,第24页。
④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岳麓书社1985年版。
①《全集》卷二,奏议二,《边防实效全在得人折》。
②《全集》卷八十九,公牍四,《延访洋务人才启》。
③见辜鸿铭:《张文襄幕府纪闻·清流党》。
●生平篇——从清流健将到洋务殿军 第一章 早岁经历 第一节 世宦之家
明永乐年间,朝廷迁徙山西人口充实畿辅及川、陕、湖广一带。这是中国历史上一次著名的大移民。直到今天,民间依然传诵着“要问祖先来何处,洪洞城北大槐树”的寻根谣。本书传主张之洞的先祖张本,也跋涉在茫茫的迁徙人流中。
张本从洪洞来到京畿漷县(今北京通县一带),安下家来。经过两代耕读,张本的孙子张端,官居南直隶繁昌县获港巡检,又举家迁至天津府南皮县(今属河北省),于东门印子头置产立业。张氏家族从此定居于此,声名渐盛,号”东门张氏”。张端之子张淮于明正德年间进士及第,官至河南按察使,“以文章忠义有声于时”①。张淮七传至乃曾,即之洞高祖,为清代山西孝义知县,乃曾之子怡熊,官浙江山阴知县,“两世为具令,皆以廉惠闻”②。之洞祖父廷琛,字献侯,以贡生资格任四库馆誊录,后议叙福建漳浦东场盐大使,又题补古田知县。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因闽浙总督伍拉那等贪污、纵盗案,督抚藩臬十余要员下狱,牵连甚广。廷琛不仅洁身免祸,还多方“调护拯救”,甚获时誉。
之洞的父亲张锳,字又甫,号春潭,生于乾隆五十八年(1493年),早年丧父,家境窘迫,“食贫力学”③,于嘉庆十八年(1813年)乡试中举。张锳将家徙居南皮城南三里双妙村,这里便成为张之洞的故里。中举后,张锳屡赴会试不第,以大挑④补贵州安化知县,又调贵筑知县,后迁古州同知,擢兴义知府(所辖在今贵州安龙布依族苗族自治县一带)。张锳一生三娶。原配刘夫人,布政司经历刘廷武之女。继娶蒋夫人,四川嘉定知府蒋策之女。再娶朱夫人,四川邛州直隶州知州朱绍恩之女。道光十七年八月初三日(1837年9月2日),朱夫人生之洞于兴义知府官舍⑤。之洞以上,有一个哥哥之渊,以下有两个弟弟之澄、之涌,还有八个姐妹。堂兄之、之清因父早亡,也被张锳收养,如同亲生一般。这是一个颇为热闹、殷实的大家庭。
道光二十年(1840年),朱夫人病逝。三岁的之洞当然记不得母亲的音容笑貌,但母亲生前喜爱抚弄的两尊古琴,却常常勾起他的思念之情:
梦断怀棬泪暗倾,双琴空用锦囊盛。
儿嬉仿佛前生事,那记抛廉理柱声。①
生母死后,之洞由父亲的侧室魏氏抚养。魏氏无子,待之洞如己出。母子感情甚笃。光绪十三年(1887年),魏氏卒于南皮。此时之洞在两广总督任内,闻报十分悲伤,“白衣冠为位而祭”,“循礼成服”。对魏氏亲属来粤者,亦“以戚谊待之”②。
张锳对子侄管教甚严。他礼聘远近名儒为子侄侍授“乾嘉老辈诸言”③,又购书数十橱,“令于日课外,听以己意观之”。之洞四岁发蒙,从附生何养源受读。拔贡曾搢之,附贡张蔚斋,举人黄升三、王可贞、张肖、赵斗山,进士敖慕韩,先后作过他的业师。有严父督促,名师指教,童年的之洞十分勤勉,读书“非获解不辍,篝灯思索,每至夜分,倦则伏案而睡,既醒复思,必得解乃已。”④学业因此大进。八岁读完四书五经,十岁开始习作诗文。兴义府署比邻试院,院内有天香阁,立树石佳胜之间。之洞读书习字、赋诗填词于其中,每得怡乐。他曾集此时诗文为一集,曰《天香阁十二龄草》①。张锳高兴地将其寄给之洞的伯父一阅,伯父复函以“敛才勿露”为最。之洞终身诵之。
十二岁以后,之洞又先后师从韩超、丁诵孙、重云逵、袁燮堂、洪次庚、吕文节、刘僊石、朱伯韩,研习经学、小学、古文学、史学、经济之学。他还尝从父亲的挚友胡林翼(1812—1861)问业。胡林翼、韩超十分器重少年之洞的才气,而之洞一生奉行经世实学,亦受胡、韩二人影响为最。
②许编《年谱》卷三。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胡编《年谱》卷一。
①集中诗文存于张锳主纂《兴义府志》,清宣统元年铅印本。
①许同莘:《张文襄公年谱》,以下简称许编《年谱》,商务印书馆民国三十五年版,卷一。
②许编《年谱》卷一。
③许编《年谱》卷一。
④清乾隆以后定制,对三科以上会试不中的举人,由国家挑选其中一等的以知县用,二等的以教职用,挑选标准重在形貌与应对。
⑤此据许同莘《年谱》和胡钧《年谱》。另据刘显世等修《贵州通志》(民国三十七年铅印本),道光十七年,张锳尚在贵筑知县任内,按此说,则之洞的出生地应为贵筑知县官舍六洞桥(今贵阳市博爱路)。
①《全集》,卷二百二十五,诗集二。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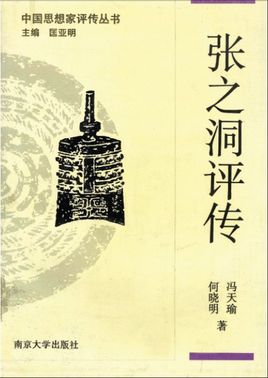 作者:冯天瑜(清)
作者:冯天瑜(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