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库兹涅佐夫睡不着。车厢顶上的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狂风暴雪袭击着车厢,铺位上方隐约可见的小窗给越来越厚的积雪遮没了。
机车发出凶猛的、撕碎风雷的怒吼,拖着军用列车在夜色沉沉的原野上、在白茫茫的漫天飞雪中疾驰。在轰隆作响的车厢的昏暗中,在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里,在士兵们从梦中发出的惊恐的呜咽声和喃喃呓语中,可以听到这仿佛在不断给谁发着警告的机车的怒吼声。库兹涅佐夫透过暴风雪,似乎看到前方有一座燃烧着的城市在冒着朦胧的火光。
在萨拉托夫停车之后,大家算是弄清楚了:现在要把他们的师紧急调往斯大林格勒附近,而不是象他们最初推测的那样调往西线。此刻库兹涅佐夫也知道,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了。于是他把粗梗刺人的、被呼吸弄潮了的军大衣领子拉到面颊上,但怎么也暖和不了,仍然睡不看,因为寒风从积雪掩盖的小窗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尖厉的过堂风在铺位之间穿来穿去。
过去的一切——那炎热多灰的阿克丘宾斯克城,炮兵学校里的夏天,草原上吹来的一阵阵灼人的热风,黄昏的寂静中郊区的骡马喘吁吁的嘶叫声(这叫声每晚都那么准时,以致正在进行战术作业的排长们,尽管渴得非常难受,却也不无轻松之感地对起表来),那热得叫人发昏的酷暑中进行的行军训练,给汗湿透了的、被太阳晒得泛白的军便服,牙齿里格格作响的灰沙,那星期日在城内和公园里的巡逻(军乐队每晚都在公园舞场上和谐地演奏乐曲)……后来从学校毕业了,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在警报声中上车,接着是大雪封盖的森林,雪堆,坦波夫郊外新兵营的土屋;随后在十二月寒冷而绯红的晨阂中,又在警报声里匆匆登上了军用列车;最后是出发——这全部动荡不安的、被什么人掌握着的现实生活,现在已经黯然失色,成为遥远的过去。没有希望看到母亲了,而他在不久之前还几乎毫不怀疑,他们是要经过莫期科被送到西线去的。
库兹涅佐夫怀着突然变得强烈的孤独感,对着沉沉夜色沉思着;“要写封信给她,把这一切都讲清楚。我们已经九个月没有见面啦……”
整个车厢在磨牙声、尖叫声和车轮滚动的轰隆声中沉睡着。一切都在紧张地颠簸着,上层铺位由于列车疾驰而摇摇晃晃。库兹涅佐夫的铺位靠近小窗边,刺骨的过堂风把他吹得全身直打哆咳。他把领子翻直,羡慕地看了看身边熟睡的二排排长达夫拉强中尉——由于铺位间很阴暗,看不见达夫拉强的面部。
“不行,这儿靠窗太冷,我睡不着。这么下去还没到前线就会冻死的,”库兹涅佐夫这样埋怨自己,开始稍微活动一下,就听到车厢板壁上的一层霜在喳喳作响。
他把手往板壁上一撑,离开了那又冷又窄,又有点扎人的铺位,从铺上跳了下来。他感到有必要在火炉边吸暖身子:背脊完全冻僵了。
在关着的车门上有一层厚霜闪闪发光,门边有一只铁火炉,火早就熄了,只有炉底的余烬象一动不动的眼珠,在发着红光。不过这儿比上边毕竟要暖和些。在昏暗的车厢里,这一点暗红的炭火朦胧地照出了横七坚八地放在过道里的新毡靴、饭盒和枕在头底下的背囊。值日兵戚比索夫很别扭地躺在下铺,简直是睡在其他土兵的腿上了。他的整个脸都藏在大衣领子里,只有帽顶露在外面,两手笼在袖管里。
“戚比索夫!”库兹涅佐夫叫了他一声,打开炉门,一丝勉强能感到的热气迎面而来。“火全熄了,戚比索夫!”
没有回答。
“值日兵!听见吗?”
戚比索夫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他疲惫无力,睡眼惺松,护耳皮帽拉得低低的,下巴上的带子系得很紧。他还没有睡醒,想解开带子,把帽子从额上往后推,一面假装糊涂,怯生生地嚷道:“我怎么啦?怎么会睡着了呢?一迷糊就睡过去了。很抱歉,中尉同志。哟,打个盹儿把人都冻僵了!……”
“您倒睡大觉,可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挨冻了。”库兹涅佐夫责备地说。
“中尉同志,那我可没有想到,不是有意的,”戚比索夫喃喃地说。“我太困了……”
接着,他不待库兹涅佐夫命令,就劲头十足地,仿佛根本没睡过一样,从地上拾起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一折两段,忙忙碌碌地开始柱炉里加柴。这时他不住地扭动着胳膊和肩膀,好象两胁发痒似的。他一直弯着腰,一本正经地不时向炉腔里瞅瞅,炉火终于懒洋洋地燃了起来。戚比索夫被烟燎黑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就象想出鬼点子、向人家讨好那样。
“中尉同志,这下我要把暖气补回来,烧得象在澡堂里一样!打仗到现在我可冻坏了!啊哟,冻得真够戗,每根骨头都在酸哩——简直没说的!……”
库兹涅佐夫在打开着的炉门边坐下来。他对值日兵过于做作的张罗仍然感到不快,这使他想起了这个人的过去。戚比索夫是他排里的士兵。这个凡事有求必应、卖力得过分的人,曾在德军俘虏营里待过好几个月。从他在排里出现的第一天起,他似乎随时随刻准备为每个人效劳。这种状况使大伙儿对他既怜悯又警惕。
戚比索夫轻手轻脚地象娘们那样坐到铺上去,眨巴着没有睡醒的眼睛说:“这么说,我们是开到斯大林格勒去罗,中尉同志?照战报上看来,那里简直是一架大绞肉机?您不害怕吗,中尉同志?一点也不怕?”
“到那儿就会看到是架怎样的绞肉机,”库兹涅佐夫盯着炉火,漫不经心地应答着。他看到戚比索夫脸上那种阿 的关切,心里很不舒服。“您怎么啦,害怕了?问这些干什么?”
“是的,可以说有一点,不过不象从前那样怕了。”戚比索夫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回答,然后叹了口气,把一双小手放在膝盖上,似乎为了想使库兹涅佐夫相信他而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后来我们的人把我从俘虏营里救了出来,他们都相信我,中尉同志。要知道我在德国人那儿象狗崽子一样整整给关了三个月啊。我们的人相信我……这是一场大战呀,参加打仗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怎能马上叫人相信呢?”戚比索夫小心地瞟了库兹涅佐夫一眼,库兹涅佐夫没作声,装着弄炉子取暖。他聚精会神地在开着的炉门上面烘手:一会儿把手指攥紧,一会儿又伸开。
“您知道我怎么被俘的吗,中尉同志?我没有对您讲过,但是很想告诉您。德国人把我们赶进一条山沟,在维亚兹马附近。当他们的坦克一直开到跟前。将我们包围起来时,我们连手榴弹都打光了,团政委拿着手枪跳到他的‘爱姆卡’车顶上喊:‘宁死不当法西斯恶棍的俘虏!’说完就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甚至从头上喷了出来。德国人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冲来,他们的坦克把人活活轧死。就在那时候……团长,还有……”
“后来怎么样?”库兹涅佐夫问。
“我没有能开枪自尽。敌人把我们赶到一块儿,叫着‘汗得霍黑’,就把我们带走了……”
“我明白了,”库兹涅佐夫用一种严肃的语调说,这种语调显然意味着,要是他处在戚比索夫的地位,他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戚比索夫,他们一喊‘汗得霍黑’,您就马上缴枪是吗?枪您总有的罗?”
戚比索夫强作笑脸,辩解似地回答说,“您还年轻,中尉同志。没有孩子、没有老婆,可以这样说。大概只有父母吧……”
“这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库兹涅佐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注意到戚比索夫脸上隐约地流露出一种负罪的神色,又补充说:“这是毫不相干的。”
“怎么不相干呢,中尉同志?”
“晤,我大概没把话说情楚……当然,我是没有孩子的。”
戚比索夫比他年长二十来岁,在排里年纪最大,可算是“老爹”、“老大爷”了。论职位,他应绝对服从库兹涅佐夫,但是库兹涅佐夫现在还经常考虑到自己领章上不过刚加上两个小方块,从学校一毕业就担任新职务,所以跟富有生活经验的戚比索夫谈起话来,每一次总感到有点儿信心不足。
“怎么着,中尉,是你在那儿还是我看错了?炉子有火吗?”头顶上有个人,带着睡意未消的声音说。接着,上铺发出一阵忙乱的响声,乌汉诺夫上士象熊一样笨重地跳到火炉跟前。他是库兹涅佐夫排的一炮炮长。
“冻得象龟孙子一样?你们在烤火吗,斯拉夫人?还是在讲故事?”乌汉诺夫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大声说。他抖动着疲乏的肩膀,撩开军大衣的下摆,踏着摇晃的地板走到车门口,用力推开那结着浓霜、隆隆作响的又重又大的车厢门,对着门缝看外面的暴风雪。顿时,车厢里雪花飞旋,冷气逼人,一股蒸汽冲着他的两腿直往里钻,机车发出的威胁般的咆哮声,夹着隆隆的车轮声和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一齐冲了进来。
“呵,真是可怕的黑夜!既看不见灯火,也看不出斯大林格勒。”乌汉诺夫耸着肩说,随即喀嚓一声把四角包有铁皮的车厢门推上了。然后他把毡靴在地板上磕了几下,冷得嘴里发出奇怪的咯咯声,走到已经烧旺的火炉边。他那带着嘲弄神情的浅色眼睛还充满睡意,眉毛上有几片雪花。他在库兹涅佐夫旁边蹲了下来,在火炉上搓搓手,然后掏出烟荷包,忽然又想起什么事,笑了起来,那颗不锈钢的假门牙在火光里闪了一下。
“我又梦见好吃的东西了。我象是睡着,又象是没睡着,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座空城,我一个人……走进一家被炸过的商店——柜台上有面包、罐头、洒、香肠……好,我想,马上来大吃一顿吧!可是天真冷啊。我象个藏身在渔网下的流浪汉,简直冻僵了。后来就醒啦。真扫兴……整个一家大商店哩!你能想象吗,戚比索夫?”
他不是对库兹涅佐夫而是对戚比索夫讲话,显然暗示中尉同别人不一样。
“您做的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上土同志,”戚比索夫皱起鼻子,嗅了一下热空气,仿佛火炉在散发出面包的香味,然
后和颜悦色地膘膘乌汉诺夫的烟荷包说:“如果一整夜不抽烟,倒也省钱,能省十支烟卷哩。”
“你真是个大大的外交家,老大爷!”乌汉诺夫说着,就把烟荷包塞在他手里。“哪怕你卷得象拳头那么粗都行。还省什么鬼钱?有什么意思?”乌汉诺夫就着一块燃着微火的木片吸着了烟卷,然后吐出一口烟,又用木片在火里掏了一阵。“弟兄们,在前线吃的东西到底要好些。还有战利品发下来!哪儿有德国鬼子,那儿就有战利品。到那时,戚比索夫,我们就用不着大伙儿揩中尉补助给养的油了。”乌汉诺夫吹吹烟灰,
眯起眼睛说:“怎么样,库兹涅佐夫,当指挥官就象做亲老子一样,责任挺重吧?当兵要轻松些,管好自己就行了。现在这么
多头脑简单的家伙成为你的累整,你不感到懊恼么?”
“我不懂,马汉诺夫,到底为什么还没有授给你军衔呢?你解释解释,行吗?”库兹涅佐夫说,他被乌汉诺夫的取笑口吻有
点儿触痛了。他和乌汉诺夫上士一起读完了炮兵学校。但是由于某种谁也不知道的原因,没有让乌汉诺夫参加考试。他来到团里时是个上士,被编在第一排任炮长,这使库兹涅佐夫实在感到不好意思。
“我幻想太多,”乌汉诺夫温厚地笑了笑。“你没有从这方面理解我,中尉……算了,再睡它六百分钟吧。也许还能梦见那家商店,能吗?喂,弟兄们,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当我去冲锋没回来吧……”
乌汉诺夫把烟头扔进炉子,伸了下懒腰,站起身来,笨拙地走向铺位,沉重地跳到沙沙作响的干草上,推着熟睡的人说:“喂,弟兄们,让出点生存空间吧。”不多会,那儿就安静下来了。
“你也去躺躺吧,中尉同志,”戚比索夫叹了口气,建议说。“看来夜反正不长了,放心吧,上帝保佑。”
库兹涅佐夫被炉火烤得红光满面,也站了起来,用训练有素的动作整了整新的手枪皮套,以命令的口吻对戚比索夫说,
“好好地执行值日兵的任务。”
库兹涅佐夫说完后,发现戚比索夫的目光顿时变得沮丧起来,就感到自己的语调太生硬了(六个月的炮校生活使他习惯了这种命令语气),于是突然改变口气,低声说:“只是请你别让炉子熄掉,听到吗?”
“明白了,中尉同志。可以说,不用担心了。愿您安安稳稳睡一觉……”
库兹涅佐夫爬上自己的铺位。这里很阴暗,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儿暖气,并且由于列车的狂奔而轧轧乱响、震动不已。他立即感到又要在穿堂风里冻僵了。从车厢的各个角落传来土兵们的鼾声和喘息声。他稍微挤了挤睡在旁边的达夫拉强中尉,后者在梦中哽咽了一声,象小孩那样咂咂嘴唇。库兹涅佐夫朝翻起的大衣领子里呵气,把脸紧贴在潮湿刺人的绒毛上,全身缩成一团,两个膝盖刚好触到板壁上一大片盐花般的浓霜——单是这一点就便他感到够冷的了。
压实了的发潮的干草在他身底下沙沙地滑动:冻透了的板壁发出铁味儿;头顶上的小窗已被大雪塞满.变得黯然无光;一股微小的、刺骨的冷风从窗缝里不断地向他脸上吹来。
机车发出倔强而威严的咆哮声,撕破夜空,拖着列车在苍茫的旷野里不停地飞驰——离前线越来越近了。
第二章
由于寂静,由于一种突如其来而叫人感到不习惯的安谧状态,库兹涅佐夫醒了。他睡意未消的脑子里马上意识到:“是卸车!我们停车了!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他从铺位上跳了下来。这是一个安静而寒冷的早晨。冷风朝敞开的车厢门吹进来;在黎明时已经停止了的这场暴风雪之后,一动不动地隆起着绵延不尽的雪堆,好似晶莹的浪涛直伸到远方地平线上。黯淡的太阳象一只沉重的紫红色圆球,低悬在雪堆上空。所有的一切——包括车门铁皮上的浓霜和空气中碎云母似的灭尘——都亮闪闪地刺人眼目。
冰冷的车厢里已经空无一人。铺位上堆着乱糟糟的干草,枪架上的卡宾枪闪着暗红的微光,打开了的背包乱扔在搁板上。车厢旁边有人啪啪地拍着手套,在这严寒而静悄悄的早上,听得见毡靴踏着甭地的清脆有力的声音。
有人在讲话:“斯拉夫弟兄们!斯大林格勒到底在哪儿呀?”
“好象不是下车吧?什么命令也没有,还来得及吃顿早饭。大概还没有到。我们的人已经带着饭盒走出去了。”
还有个人用嘶哑的声音快活地说:“啊呀,天空晴朗,他们会来空袭吧!……现在可正是时候!”
库兹涅佐夫蓦地摆脱了睡意,来到车厢门口。旷野的白雪要映着强烈的阳光,使他只能眯缝着眼睛,刺骨的寒风呛得他喘不过气来。
列车停在草原上。车厢附近,冻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聚集着成群的士兵。他们兴奋地互相撞着肩头取暖,用手套拍打腰部,大家不时地朝同—方向转过身去。
那边,在靠列车中部的月台上,炊车的烟火正迎着绯红的朝霞枭枭升起。对面是一幢孤零零的会让站的小屋,屋顶探出在雪堆上面,柔和地映着灶火的红光。士兵们带着饭盒从车厢向炊车和小屋跑来.炊车周围和安着吊杆的水井四周雪地上,象蚂蚁一样蠕动着无数穿军大衣和短棉袄的人——看样子全列车的人都在忙着取水,准备开早饭了。
车厢附近有人在聊天:“真是从头到脚冻个透啊,弟兄们!大概有零下三十度吧?这会儿呀,弄个暖和的草棚儿,再来个泼辣的小娘们儿,那么——察伊尔公园的玫瑰花就开放了。”
“涅恰耶夫老是这个调调。不管人家说什么,他一开口就是娘们!大概你在舰队里吃惯了巧克力糖吧?怪不得你成了一条公狗,拿棍子也赶不开啦!”
“老兄,不要讲粗话!这些事情你懂得什么?察伊尔公园里春天来……你呀,老兄,是个乡巴佬!”
“呸,公马!又是那一套!”
“早就停车了吗?”库兹涅佐夫随口问道,随即跳到了嚓嚓响的雪地上。
士兵们看到中尉时并没有停止撞肩、顿脚,也没有按规定的礼节立正站好(“都搞惯了,这些鬼东西!”库兹涅佐夫想),只是有那么一会儿停止了讲话;每个人的眉毛上、帽绒上和拉起的大衣领上都结着白晃晃的刺人的霜花。
一炮瞄准手涅恰耶夫中士,高高的个子,长着一身结实的肌肉,曾在远东当过水兵。他脸上那几颗生着茸毛的胎痣、面颊上的鬓毛以及黑黑的小胡子都很引人注目。
涅恰耶夫说:“中尉同志,关照过不要叫醒您。乌汉诺夫说您夜里值班。暂时没有全体集合的紧急情况。”
“德罗兹多夫斯基在哪儿?”库兹涅佐夫仍然被雪堆上的太阳反光照得眯缝着眼睛。
“在打扮哩,中尉同志。”涅恰耶夫挤了挤眼睛。
在离车厢约二十米的地方,库兹涅佐夫看到了炮兵连长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德罗兹多夫斯基还在学校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具有几乎是天生的军人风度,清瘦、苍白的脸上总是带着威严的表情。他是炮校的优秀学员,是各级指挥员的宠儿。此刻,他赤着膊,正在擦弄着体操家一样结实的肌肉。他站在雪堆旁士兵们看得到的地方,弯着腰,一声不响地用冰雪使劲地在身上摩擦。他那年轻人灵活的身躯、肩膀和光洁无毛的胸膛,都在微微冒着热气。在他用一捧捧冰雪洗擦身体的动作中显示出他的顽强精神。
“好,他做得对。”库兹涅佐夫认真地说。
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就脱下帽子,塞进大衣口袋,解开领扣,走到离车厢稍远的地方,从雪堆上捧起一把又粗又埂的雪,在面颊和下巴上擦起来。直到把皮肤擦得发痛。
“真是稀客呀!您上我们这儿来了?”他听到涅恰耶夫用过分夸张的喜悦声音说。“看到您我们多高兴呀!全连都欢迎您,卓叶奇卡!”
库兹涅佐夫洗着脸,被又冷又稍带苦昧的冰雪弄得气喘吁吁。他挺直身子,换了口气,掏出一块手帕来代替毛巾(他懒得回车厢去拿),这时又听见后面的士兵在笑着大声讲话。接着,背后响起了一个女人的清脆的嗓音:“我不懂,你们一连发生了什么事?”
库兹涅佐夫转过身去。在车厢旁边一群笑嘻嘻的士兵中间,站着炮兵连的卫生指导员卓娅·叶拉金娜。她穿着漂亮的白色短皮袄、整洁的白毡靴,戴着绣花白手套,完全不象个军人。她这身节日般干干净净的冬季装束,倒象是来自另一个遇远的太平世界。卓娅忍住笑,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德罗兹多夫斯基,而他却没有发现卓娅,依旧象在做操般的弯腰伸腿,拿雪块迅速擦着已经发红的健壮身体,然后又用巴掌拍着肩膀、肚皮,做深呼吸,并在吸气时卖弄地挺起胸膛。这时大家都象卓娅那样看着他了。
“中尉!”卓娅大声喊道:“您的体操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我找您有事。”
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抹掉胸前的雪碴,脸上露出被人打扰之后那种不满意的神气,顺手解下围在腰间的毛巾,不大乐意地说:“谈吧!”
“早上好,连长同志!”她说。正在用手帕揩脸的库兹涅佐夫看到卓娅那被霜花弄得毛蓬蓬、刚硬如刺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我要找您一下。您的连能抽点时间管管我的事吗?”
德罗兹多夫斯基不慌不忙地把手巾搭在脖子上,向车厢走去。用雪擦过的肩膀油光光地发亮,就象刚洗过澡一样;草黄色的短发也是潮湿的;他一边走,一边用那对蓝眼睛——此刻显得更蓝,蓝得几乎透明的眼睛——威严地看着聚集在车厢近旁的士兵。路上他随口问了一句:“我猜到,卫生指导员,您是根据章程第八条下连来查卫生的吧?这儿没有虱子。”
“亲爱的卓叶奇卡,”涅恰耶夫中士连忙接着说,轻佻的目光瞟过卓娅整洁的短皮袄和她腰间的救护包。“我们连严格执行规定。大白天点着灯也找不到寄生虫子,您找错地方啦……夜里睡得好吗?没有谁打扰您吧?”
“废话那么多,涅恰耶夫!”德罗兹多夫斯基打断了他,从卓娅身边走过,顺着小铁梯走进车厢。车厢里挤满了刚从炊车那边领早饭回来的士兵们。他们的饭盒里盛着热气腾腾的汤,三个背囊塞满着烤面包和面包干。士兵们象通常开饭时那么熙熙攘攘,把不知哪一个的军大衣摊开在下层铺位上,打算在那儿切面包;冻得发红的脸上显出忙于张罗日常生活的神色。
德罗兹多夫期基穿上军便服,把它拉平整,然后发出命令:“静下来!不要嚷嚷行吗?各炮炮长维持秩序!瞄准手涅恰耶夫!您站在那里干什么7过来分配食物,我看你是个分食老手!卫生指导员那里有人照顾,不用您管了。”
涅价耶夫抱歉地向卓娅点点头,登上车厢,在里里喊了起来:“弟兄们,为什么大家都不动手了呢?那么吵吵嚷嚷干啥?真象坦克一样轰隆轰隆没个完。”
库兹涅佐夫听到这几声喊,特别是由于这些不再管卓娅的士兵们当着她的面就乱哄哄地分早饭,感到很不舒服。他真想用一种连自己也要吓一跳的大胆腔调对卓娅说:“其实用不着到我们几个排来查什么卫生。只要您到我们这里来了,那就好啦。”
他到头来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只要卓娅一到这里,大伙就情不自禁地用这种庸俗可鄙的腔调跟她说话,现在就连他自己也巴不得这么干了。这种放肆的调情口吻似乎在向卓娅暗示:她每一次来都弄得大家有点酸溜溜的,似乎大家能从她那微带睡容的脸蛋上、从她眼睛底下的黑晕里和两片嘴唇之间,觉察出她答应人家干的不体面事情的迹象;而这码事在她和那些医疗营的年轻医生之间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途中大部分时间卓娅都坐在救护车厢里,跟他们在一起。库兹涅佐夫猜想,卓娅每次停车都跑到连里来,并不仅仅为了检查卫生,她在寻找机会跟德罗兹多夫斯基接触。
“连里一切正常,卓娅,”库兹涅佐夫说,“不必作任何检查。而且正在开早饭。”
卓娅耸耸肩膀说:“这个车厢真特别,没有一个要看病的!别装出那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你们这样不行!”她睫毛—扬,打量了库兹涅佐夫一眼,莫名其妙地笑着。“您那敬爱的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在这样大成问题的雪浴之后,我想,他不会出现在前线,而将出现在医院里!”
“第一,他不是我敬爱的。”库兹涅佐夫问答:“第二……”
“谢谢您对我说实话,库兹涅佐夫。第二呢?第二您对我是怎么想的?”
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已经穿好衣服,正用皮带把军大衣束紧,新手枪套在皮带上晃荡着。他轻巧地跳到雪地上,瞧瞧库兹涅佐夫,又瞧瞧卓娅,慢吞吞地说:“卫生指导员,您说说,我象个想做逃兵的人吗?”
卓娅挑衅地把头一扬说:“可能正是这样……至少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告诉您,”德罗兹多夫斯基断然地说,“您不是班主任,我也不是小学生。请您回到救护车厢去吧,明白吗?……库兹涅佐夫,您留下来代我负责一下,我到营长那里去。”
德罗兹多夫斯基带着叫人揣摩不透的表情,举手行了个军礼。他腰间紧束着皮带和新武装带,迈着优美的队列军人的灵活矫健的步伐,从车厢附近来来去去的士兵身边走过去。士兵们一见到他就不吭声了,纷纷给他让路,仿佛他的目光能把大家推开似的。他一边走,一边随便举举手向土兵们还礼。太阳被一道道彩虹环绕着,挂在白晃晃的草原上空。水井周围,人群依然时聚时散。人们在那儿打好水,接着脱下军帽,缩着身子,呼哧呼哧地洗脸,然后他们向列车中段冒着诱人炊烟的炊车那儿跑去,路上谨慎地绕过几个营部军官——他们都站在一节蒙着厚霜的客车车厢旁边。
德罗兹多夫斯基向这几个军官走去。
这时库兹涅佐夫看到,卓娅圆睁微斜的眼睛,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目送连长远去。他问道:“您在我们这里吃早饭吧?”
“什么?”她心不在焉地问。
“跟我们一块儿吃早饭。您大概还没吃过吧。”
“中尉同志,都要冷掉了!我们在等您呐,”涅恰涅夫在车门口叫了一声。“豌豆羹,”他从饭盒掇舀起—‘匙羹来,舔小胡子说,“只要不噎死,终归能活着!”
在他背后,士兵们正挤挤嚷嚷地从摊开的大衣上领取自己的一份早餐,有的在满意地说笑,有的则嘟哝着坐到铺上,把匙子放进饭盒里,咬起冻硬了的黑面包来。现在谁也顾不上卓娅了。
“戚比索夫!”库兹涅佐夫唤道。“快把我的饭盒拿给卫生指导员!”
“小护士!您怎么啦?”戚比索夫在车厢里用悦耳的声音答应着,“我们这儿,可以说,是一帮快活人。’
“是的……很好,”卓娅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当然,库兹涅佐夫中尉。我没吃过早饭。不过……为什么要用您的饭盒?您自己呢?”
“我等一会。不会挨饿的,”库兹涅佐夫回答。
戚比索夫急急忙忙地咀嚼着,走列车门口,不知怎么一来,就从翻起的领子里过分殷勤地伸出了胡子拉碴的小脸,他象孩子做游戏那样,愉快地朝卓娅点点头。他长得很瘦小,身上穿着一件短得难看又宽得不象样子的军大衣。
“上来吧,小护士!这有什么关系!……”
“我在您的饭盒里吃一点好了,”卓娅对库兹涅佐夫说。“一定得跟您一道吃,否则我就不吃……”
士兵们呼哧呼哧地吃着早饭。但在喝了几勺子热羹和几口糖开水之后,他们又开始用探索的目光打量起卓娅来了。她解开了短皮袄的领口,展出洁白的脖子,小心翼翼地从库兹涅佐夫的饭盒里舀羹吃,她把饭盒放在膝盖上,在许多人目光的注视下低垂着眼睛。
库兹涅佐夫同卓娅一道吃着,尽量不去看她怎样斯文地把汤匙送到唇边,在吞咽食物时喉头怎样活动。她那低垂的睫毛已被溶化了的霜花沾湿,粘在一起,乌油油地恰好遮住她那心神不定的眼睛。卓娅在烧得通红的火炉边感到热,便脱下帽子,让栗色的头发披散在皮袄的白毛领子上。帽子一脱顿时使她换了一副无可掩饰的可怜巴巴的模样。她颧骨挺高,嘴巴很大,一张绷紧的、甚至怯生生的孩子气的脸,在炮兵们由于吃饭而热得出汗的红脸膛中间,显得异常突出。库兹涅佐夫第一次发现;她长得并不漂亮。他过去从未见过卓娅不戴帽子。
“察伊尔公园里玫瑰开,察伊尔公园里春天来……”
涅恰耶夫中士叉开两腿站在铺边,他喝过茶了,正在那儿卷烟卷,一面轻声哼着歌儿,带着温存的浅笑打量着卓娅。
戚比索夫则特别殷勤地倒来满满一杯茶递给卓娅。
她用手指接过很烫的茶杯,不好意思地说:“谢谢,戚比索夫。”
她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涅恰耶夫说:“您说说,中士,这是怎么样的公园和玫瑰呀?我不懂,为什么您老是唱这个?”
士兵们活跃起来了,怂恿涅恰耶夫说:“讲吧,讲吧,中士。问你这支歌是打哪儿来的?”
库兹涅佐夫睡不着。车厢顶上的呼啸声一阵紧似一阵,狂风暴雪袭击着车厢,铺位上方隐约可见的小窗给越来越厚的积雪遮没了。
机车发出凶猛的、撕碎风雷的怒吼,拖着军用列车在夜色沉沉的原野上、在白茫茫的漫天飞雪中疾驰。在轰隆作响的车厢的昏暗中,在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里,在士兵们从梦中发出的惊恐的呜咽声和喃喃呓语中,可以听到这仿佛在不断给谁发着警告的机车的怒吼声。库兹涅佐夫透过暴风雪,似乎看到前方有一座燃烧着的城市在冒着朦胧的火光。
在萨拉托夫停车之后,大家算是弄清楚了:现在要把他们的师紧急调往斯大林格勒附近,而不是象他们最初推测的那样调往西线。此刻库兹涅佐夫也知道,只有几小时的路程了。于是他把粗梗刺人的、被呼吸弄潮了的军大衣领子拉到面颊上,但怎么也暖和不了,仍然睡不看,因为寒风从积雪掩盖的小窗上的那些看不见的缝隙里钻进来,尖厉的过堂风在铺位之间穿来穿去。
过去的一切——那炎热多灰的阿克丘宾斯克城,炮兵学校里的夏天,草原上吹来的一阵阵灼人的热风,黄昏的寂静中郊区的骡马喘吁吁的嘶叫声(这叫声每晚都那么准时,以致正在进行战术作业的排长们,尽管渴得非常难受,却也不无轻松之感地对起表来),那热得叫人发昏的酷暑中进行的行军训练,给汗湿透了的、被太阳晒得泛白的军便服,牙齿里格格作响的灰沙,那星期日在城内和公园里的巡逻(军乐队每晚都在公园舞场上和谐地演奏乐曲)……后来从学校毕业了,在一个秋天的夜晚,在警报声中上车,接着是大雪封盖的森林,雪堆,坦波夫郊外新兵营的土屋;随后在十二月寒冷而绯红的晨阂中,又在警报声里匆匆登上了军用列车;最后是出发——这全部动荡不安的、被什么人掌握着的现实生活,现在已经黯然失色,成为遥远的过去。没有希望看到母亲了,而他在不久之前还几乎毫不怀疑,他们是要经过莫期科被送到西线去的。
库兹涅佐夫怀着突然变得强烈的孤独感,对着沉沉夜色沉思着;“要写封信给她,把这一切都讲清楚。我们已经九个月没有见面啦……”
整个车厢在磨牙声、尖叫声和车轮滚动的轰隆声中沉睡着。一切都在紧张地颠簸着,上层铺位由于列车疾驰而摇摇晃晃。库兹涅佐夫的铺位靠近小窗边,刺骨的过堂风把他吹得全身直打哆咳。他把领子翻直,羡慕地看了看身边熟睡的二排排长达夫拉强中尉——由于铺位间很阴暗,看不见达夫拉强的面部。
“不行,这儿靠窗太冷,我睡不着。这么下去还没到前线就会冻死的,”库兹涅佐夫这样埋怨自己,开始稍微活动一下,就听到车厢板壁上的一层霜在喳喳作响。
他把手往板壁上一撑,离开了那又冷又窄,又有点扎人的铺位,从铺上跳了下来。他感到有必要在火炉边吸暖身子:背脊完全冻僵了。
在关着的车门上有一层厚霜闪闪发光,门边有一只铁火炉,火早就熄了,只有炉底的余烬象一动不动的眼珠,在发着红光。不过这儿比上边毕竟要暖和些。在昏暗的车厢里,这一点暗红的炭火朦胧地照出了横七坚八地放在过道里的新毡靴、饭盒和枕在头底下的背囊。值日兵戚比索夫很别扭地躺在下铺,简直是睡在其他土兵的腿上了。他的整个脸都藏在大衣领子里,只有帽顶露在外面,两手笼在袖管里。
“戚比索夫!”库兹涅佐夫叫了他一声,打开炉门,一丝勉强能感到的热气迎面而来。“火全熄了,戚比索夫!”
没有回答。
“值日兵!听见吗?”
戚比索夫惊慌失措地跳了起来。他疲惫无力,睡眼惺松,护耳皮帽拉得低低的,下巴上的带子系得很紧。他还没有睡醒,想解开带子,把帽子从额上往后推,一面假装糊涂,怯生生地嚷道:“我怎么啦?怎么会睡着了呢?一迷糊就睡过去了。很抱歉,中尉同志。哟,打个盹儿把人都冻僵了!……”
“您倒睡大觉,可整个车厢里的人都挨冻了。”库兹涅佐夫责备地说。
“中尉同志,那我可没有想到,不是有意的,”戚比索夫喃喃地说。“我太困了……”
接着,他不待库兹涅佐夫命令,就劲头十足地,仿佛根本没睡过一样,从地上拾起一块木板,放在膝盖上一折两段,忙忙碌碌地开始柱炉里加柴。这时他不住地扭动着胳膊和肩膀,好象两胁发痒似的。他一直弯着腰,一本正经地不时向炉腔里瞅瞅,炉火终于懒洋洋地燃了起来。戚比索夫被烟燎黑的脸上露出得意的表情,就象想出鬼点子、向人家讨好那样。
“中尉同志,这下我要把暖气补回来,烧得象在澡堂里一样!打仗到现在我可冻坏了!啊哟,冻得真够戗,每根骨头都在酸哩——简直没说的!……”
库兹涅佐夫在打开着的炉门边坐下来。他对值日兵过于做作的张罗仍然感到不快,这使他想起了这个人的过去。戚比索夫是他排里的士兵。这个凡事有求必应、卖力得过分的人,曾在德军俘虏营里待过好几个月。从他在排里出现的第一天起,他似乎随时随刻准备为每个人效劳。这种状况使大伙儿对他既怜悯又警惕。
戚比索夫轻手轻脚地象娘们那样坐到铺上去,眨巴着没有睡醒的眼睛说:“这么说,我们是开到斯大林格勒去罗,中尉同志?照战报上看来,那里简直是一架大绞肉机?您不害怕吗,中尉同志?一点也不怕?”
“到那儿就会看到是架怎样的绞肉机,”库兹涅佐夫盯着炉火,漫不经心地应答着。他看到戚比索夫脸上那种阿 的关切,心里很不舒服。“您怎么啦,害怕了?问这些干什么?”
“是的,可以说有一点,不过不象从前那样怕了。”戚比索夫装着很高兴的样子回答,然后叹了口气,把一双小手放在膝盖上,似乎为了想使库兹涅佐夫相信他而用推心置腹的口气说:“后来我们的人把我从俘虏营里救了出来,他们都相信我,中尉同志。要知道我在德国人那儿象狗崽子一样整整给关了三个月啊。我们的人相信我……这是一场大战呀,参加打仗的人是各式各样的,怎能马上叫人相信呢?”戚比索夫小心地瞟了库兹涅佐夫一眼,库兹涅佐夫没作声,装着弄炉子取暖。他聚精会神地在开着的炉门上面烘手:一会儿把手指攥紧,一会儿又伸开。
“您知道我怎么被俘的吗,中尉同志?我没有对您讲过,但是很想告诉您。德国人把我们赶进一条山沟,在维亚兹马附近。当他们的坦克一直开到跟前。将我们包围起来时,我们连手榴弹都打光了,团政委拿着手枪跳到他的‘爱姆卡’车顶上喊:‘宁死不当法西斯恶棍的俘虏!’说完就向自己的太阳穴开了一枪,鲜血甚至从头上喷了出来。德国人从四面八方朝我们冲来,他们的坦克把人活活轧死。就在那时候……团长,还有……”
“后来怎么样?”库兹涅佐夫问。
“我没有能开枪自尽。敌人把我们赶到一块儿,叫着‘汗得霍黑’,就把我们带走了……”
“我明白了,”库兹涅佐夫用一种严肃的语调说,这种语调显然意味着,要是他处在戚比索夫的地位,他的做法就会完全不同。“那么,戚比索夫,他们一喊‘汗得霍黑’,您就马上缴枪是吗?枪您总有的罗?”
戚比索夫强作笑脸,辩解似地回答说,“您还年轻,中尉同志。没有孩子、没有老婆,可以这样说。大概只有父母吧……”
“这跟孩子有什么关系?”库兹涅佐夫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他注意到戚比索夫脸上隐约地流露出一种负罪的神色,又补充说:“这是毫不相干的。”
“怎么不相干呢,中尉同志?”
“晤,我大概没把话说情楚……当然,我是没有孩子的。”
戚比索夫比他年长二十来岁,在排里年纪最大,可算是“老爹”、“老大爷”了。论职位,他应绝对服从库兹涅佐夫,但是库兹涅佐夫现在还经常考虑到自己领章上不过刚加上两个小方块,从学校一毕业就担任新职务,所以跟富有生活经验的戚比索夫谈起话来,每一次总感到有点儿信心不足。
“怎么着,中尉,是你在那儿还是我看错了?炉子有火吗?”头顶上有个人,带着睡意未消的声音说。接着,上铺发出一阵忙乱的响声,乌汉诺夫上士象熊一样笨重地跳到火炉跟前。他是库兹涅佐夫排的一炮炮长。
“冻得象龟孙子一样?你们在烤火吗,斯拉夫人?还是在讲故事?”乌汉诺夫打了个长长的呵欠,大声说。他抖动着疲乏的肩膀,撩开军大衣的下摆,踏着摇晃的地板走到车门口,用力推开那结着浓霜、隆隆作响的又重又大的车厢门,对着门缝看外面的暴风雪。顿时,车厢里雪花飞旋,冷气逼人,一股蒸汽冲着他的两腿直往里钻,机车发出的威胁般的咆哮声,夹着隆隆的车轮声和车轮磨擦冰雪的尖叫声一齐冲了进来。
“呵,真是可怕的黑夜!既看不见灯火,也看不出斯大林格勒。”乌汉诺夫耸着肩说,随即喀嚓一声把四角包有铁皮的车厢门推上了。然后他把毡靴在地板上磕了几下,冷得嘴里发出奇怪的咯咯声,走到已经烧旺的火炉边。他那带着嘲弄神情的浅色眼睛还充满睡意,眉毛上有几片雪花。他在库兹涅佐夫旁边蹲了下来,在火炉上搓搓手,然后掏出烟荷包,忽然又想起什么事,笑了起来,那颗不锈钢的假门牙在火光里闪了一下。
“我又梦见好吃的东西了。我象是睡着,又象是没睡着,模模糊糊地看到一座空城,我一个人……走进一家被炸过的商店——柜台上有面包、罐头、洒、香肠……好,我想,马上来大吃一顿吧!可是天真冷啊。我象个藏身在渔网下的流浪汉,简直冻僵了。后来就醒啦。真扫兴……整个一家大商店哩!你能想象吗,戚比索夫?”
他不是对库兹涅佐夫而是对戚比索夫讲话,显然暗示中尉同别人不一样。
“您做的梦,我没有什么好说的,上土同志,”戚比索夫皱起鼻子,嗅了一下热空气,仿佛火炉在散发出面包的香味,然
后和颜悦色地膘膘乌汉诺夫的烟荷包说:“如果一整夜不抽烟,倒也省钱,能省十支烟卷哩。”
“你真是个大大的外交家,老大爷!”乌汉诺夫说着,就把烟荷包塞在他手里。“哪怕你卷得象拳头那么粗都行。还省什么鬼钱?有什么意思?”乌汉诺夫就着一块燃着微火的木片吸着了烟卷,然后吐出一口烟,又用木片在火里掏了一阵。“弟兄们,在前线吃的东西到底要好些。还有战利品发下来!哪儿有德国鬼子,那儿就有战利品。到那时,戚比索夫,我们就用不着大伙儿揩中尉补助给养的油了。”乌汉诺夫吹吹烟灰,
眯起眼睛说:“怎么样,库兹涅佐夫,当指挥官就象做亲老子一样,责任挺重吧?当兵要轻松些,管好自己就行了。现在这么
多头脑简单的家伙成为你的累整,你不感到懊恼么?”
“我不懂,马汉诺夫,到底为什么还没有授给你军衔呢?你解释解释,行吗?”库兹涅佐夫说,他被乌汉诺夫的取笑口吻有
点儿触痛了。他和乌汉诺夫上士一起读完了炮兵学校。但是由于某种谁也不知道的原因,没有让乌汉诺夫参加考试。他来到团里时是个上士,被编在第一排任炮长,这使库兹涅佐夫实在感到不好意思。
“我幻想太多,”乌汉诺夫温厚地笑了笑。“你没有从这方面理解我,中尉……算了,再睡它六百分钟吧。也许还能梦见那家商店,能吗?喂,弟兄们,如果有什么事,你们就当我去冲锋没回来吧……”
乌汉诺夫把烟头扔进炉子,伸了下懒腰,站起身来,笨拙地走向铺位,沉重地跳到沙沙作响的干草上,推着熟睡的人说:“喂,弟兄们,让出点生存空间吧。”不多会,那儿就安静下来了。
“你也去躺躺吧,中尉同志,”戚比索夫叹了口气,建议说。“看来夜反正不长了,放心吧,上帝保佑。”
库兹涅佐夫被炉火烤得红光满面,也站了起来,用训练有素的动作整了整新的手枪皮套,以命令的口吻对戚比索夫说,
“好好地执行值日兵的任务。”
库兹涅佐夫说完后,发现戚比索夫的目光顿时变得沮丧起来,就感到自己的语调太生硬了(六个月的炮校生活使他习惯了这种命令语气),于是突然改变口气,低声说:“只是请你别让炉子熄掉,听到吗?”
“明白了,中尉同志。可以说,不用担心了。愿您安安稳稳睡一觉……”
库兹涅佐夫爬上自己的铺位。这里很阴暗,冷冰冰的,没有一点儿暖气,并且由于列车的狂奔而轧轧乱响、震动不已。他立即感到又要在穿堂风里冻僵了。从车厢的各个角落传来土兵们的鼾声和喘息声。他稍微挤了挤睡在旁边的达夫拉强中尉,后者在梦中哽咽了一声,象小孩那样咂咂嘴唇。库兹涅佐夫朝翻起的大衣领子里呵气,把脸紧贴在潮湿刺人的绒毛上,全身缩成一团,两个膝盖刚好触到板壁上一大片盐花般的浓霜——单是这一点就便他感到够冷的了。
压实了的发潮的干草在他身底下沙沙地滑动:冻透了的板壁发出铁味儿;头顶上的小窗已被大雪塞满.变得黯然无光;一股微小的、刺骨的冷风从窗缝里不断地向他脸上吹来。
机车发出倔强而威严的咆哮声,撕破夜空,拖着列车在苍茫的旷野里不停地飞驰——离前线越来越近了。
第二章
由于寂静,由于一种突如其来而叫人感到不习惯的安谧状态,库兹涅佐夫醒了。他睡意未消的脑子里马上意识到:“是卸车!我们停车了!为什么不叫醒我呢?……”
他从铺位上跳了下来。这是一个安静而寒冷的早晨。冷风朝敞开的车厢门吹进来;在黎明时已经停止了的这场暴风雪之后,一动不动地隆起着绵延不尽的雪堆,好似晶莹的浪涛直伸到远方地平线上。黯淡的太阳象一只沉重的紫红色圆球,低悬在雪堆上空。所有的一切——包括车门铁皮上的浓霜和空气中碎云母似的灭尘——都亮闪闪地刺人眼目。
冰冷的车厢里已经空无一人。铺位上堆着乱糟糟的干草,枪架上的卡宾枪闪着暗红的微光,打开了的背包乱扔在搁板上。车厢旁边有人啪啪地拍着手套,在这严寒而静悄悄的早上,听得见毡靴踏着甭地的清脆有力的声音。
有人在讲话:“斯拉夫弟兄们!斯大林格勒到底在哪儿呀?”
“好象不是下车吧?什么命令也没有,还来得及吃顿早饭。大概还没有到。我们的人已经带着饭盒走出去了。”
还有个人用嘶哑的声音快活地说:“啊呀,天空晴朗,他们会来空袭吧!……现在可正是时候!”
库兹涅佐夫蓦地摆脱了睡意,来到车厢门口。旷野的白雪要映着强烈的阳光,使他只能眯缝着眼睛,刺骨的寒风呛得他喘不过气来。
列车停在草原上。车厢附近,冻得结结实实的雪地上聚集着成群的士兵。他们兴奋地互相撞着肩头取暖,用手套拍打腰部,大家不时地朝同—方向转过身去。
那边,在靠列车中部的月台上,炊车的烟火正迎着绯红的朝霞枭枭升起。对面是一幢孤零零的会让站的小屋,屋顶探出在雪堆上面,柔和地映着灶火的红光。士兵们带着饭盒从车厢向炊车和小屋跑来.炊车周围和安着吊杆的水井四周雪地上,象蚂蚁一样蠕动着无数穿军大衣和短棉袄的人——看样子全列车的人都在忙着取水,准备开早饭了。
车厢附近有人在聊天:“真是从头到脚冻个透啊,弟兄们!大概有零下三十度吧?这会儿呀,弄个暖和的草棚儿,再来个泼辣的小娘们儿,那么——察伊尔公园的玫瑰花就开放了。”
“涅恰耶夫老是这个调调。不管人家说什么,他一开口就是娘们!大概你在舰队里吃惯了巧克力糖吧?怪不得你成了一条公狗,拿棍子也赶不开啦!”
“老兄,不要讲粗话!这些事情你懂得什么?察伊尔公园里春天来……你呀,老兄,是个乡巴佬!”
“呸,公马!又是那一套!”
“早就停车了吗?”库兹涅佐夫随口问道,随即跳到了嚓嚓响的雪地上。
士兵们看到中尉时并没有停止撞肩、顿脚,也没有按规定的礼节立正站好(“都搞惯了,这些鬼东西!”库兹涅佐夫想),只是有那么一会儿停止了讲话;每个人的眉毛上、帽绒上和拉起的大衣领上都结着白晃晃的刺人的霜花。
一炮瞄准手涅恰耶夫中士,高高的个子,长着一身结实的肌肉,曾在远东当过水兵。他脸上那几颗生着茸毛的胎痣、面颊上的鬓毛以及黑黑的小胡子都很引人注目。
涅恰耶夫说:“中尉同志,关照过不要叫醒您。乌汉诺夫说您夜里值班。暂时没有全体集合的紧急情况。”
“德罗兹多夫斯基在哪儿?”库兹涅佐夫仍然被雪堆上的太阳反光照得眯缝着眼睛。
“在打扮哩,中尉同志。”涅恰耶夫挤了挤眼睛。
在离车厢约二十米的地方,库兹涅佐夫看到了炮兵连长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德罗兹多夫斯基还在学校时就显得与众不同;他具有几乎是天生的军人风度,清瘦、苍白的脸上总是带着威严的表情。他是炮校的优秀学员,是各级指挥员的宠儿。此刻,他赤着膊,正在擦弄着体操家一样结实的肌肉。他站在雪堆旁士兵们看得到的地方,弯着腰,一声不响地用冰雪使劲地在身上摩擦。他那年轻人灵活的身躯、肩膀和光洁无毛的胸膛,都在微微冒着热气。在他用一捧捧冰雪洗擦身体的动作中显示出他的顽强精神。
“好,他做得对。”库兹涅佐夫认真地说。
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这样做,就脱下帽子,塞进大衣口袋,解开领扣,走到离车厢稍远的地方,从雪堆上捧起一把又粗又埂的雪,在面颊和下巴上擦起来。直到把皮肤擦得发痛。
“真是稀客呀!您上我们这儿来了?”他听到涅恰耶夫用过分夸张的喜悦声音说。“看到您我们多高兴呀!全连都欢迎您,卓叶奇卡!”
库兹涅佐夫洗着脸,被又冷又稍带苦昧的冰雪弄得气喘吁吁。他挺直身子,换了口气,掏出一块手帕来代替毛巾(他懒得回车厢去拿),这时又听见后面的士兵在笑着大声讲话。接着,背后响起了一个女人的清脆的嗓音:“我不懂,你们一连发生了什么事?”
库兹涅佐夫转过身去。在车厢旁边一群笑嘻嘻的士兵中间,站着炮兵连的卫生指导员卓娅·叶拉金娜。她穿着漂亮的白色短皮袄、整洁的白毡靴,戴着绣花白手套,完全不象个军人。她这身节日般干干净净的冬季装束,倒象是来自另一个遇远的太平世界。卓娅忍住笑,用严厉的目光看着德罗兹多夫斯基,而他却没有发现卓娅,依旧象在做操般的弯腰伸腿,拿雪块迅速擦着已经发红的健壮身体,然后又用巴掌拍着肩膀、肚皮,做深呼吸,并在吸气时卖弄地挺起胸膛。这时大家都象卓娅那样看着他了。
“中尉!”卓娅大声喊道:“您的体操什么时候才能做完?我找您有事。”
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抹掉胸前的雪碴,脸上露出被人打扰之后那种不满意的神气,顺手解下围在腰间的毛巾,不大乐意地说:“谈吧!”
“早上好,连长同志!”她说。正在用手帕揩脸的库兹涅佐夫看到卓娅那被霜花弄得毛蓬蓬、刚硬如刺的眉梢微微颤动了一下:“我要找您一下。您的连能抽点时间管管我的事吗?”
德罗兹多夫斯基不慌不忙地把手巾搭在脖子上,向车厢走去。用雪擦过的肩膀油光光地发亮,就象刚洗过澡一样;草黄色的短发也是潮湿的;他一边走,一边用那对蓝眼睛——此刻显得更蓝,蓝得几乎透明的眼睛——威严地看着聚集在车厢近旁的士兵。路上他随口问了一句:“我猜到,卫生指导员,您是根据章程第八条下连来查卫生的吧?这儿没有虱子。”
“亲爱的卓叶奇卡,”涅恰耶夫中士连忙接着说,轻佻的目光瞟过卓娅整洁的短皮袄和她腰间的救护包。“我们连严格执行规定。大白天点着灯也找不到寄生虫子,您找错地方啦……夜里睡得好吗?没有谁打扰您吧?”
“废话那么多,涅恰耶夫!”德罗兹多夫斯基打断了他,从卓娅身边走过,顺着小铁梯走进车厢。车厢里挤满了刚从炊车那边领早饭回来的士兵们。他们的饭盒里盛着热气腾腾的汤,三个背囊塞满着烤面包和面包干。士兵们象通常开饭时那么熙熙攘攘,把不知哪一个的军大衣摊开在下层铺位上,打算在那儿切面包;冻得发红的脸上显出忙于张罗日常生活的神色。
德罗兹多夫期基穿上军便服,把它拉平整,然后发出命令:“静下来!不要嚷嚷行吗?各炮炮长维持秩序!瞄准手涅恰耶夫!您站在那里干什么7过来分配食物,我看你是个分食老手!卫生指导员那里有人照顾,不用您管了。”
涅价耶夫抱歉地向卓娅点点头,登上车厢,在里里喊了起来:“弟兄们,为什么大家都不动手了呢?那么吵吵嚷嚷干啥?真象坦克一样轰隆轰隆没个完。”
库兹涅佐夫听到这几声喊,特别是由于这些不再管卓娅的士兵们当着她的面就乱哄哄地分早饭,感到很不舒服。他真想用一种连自己也要吓一跳的大胆腔调对卓娅说:“其实用不着到我们几个排来查什么卫生。只要您到我们这里来了,那就好啦。”
他到头来对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什么只要卓娅一到这里,大伙就情不自禁地用这种庸俗可鄙的腔调跟她说话,现在就连他自己也巴不得这么干了。这种放肆的调情口吻似乎在向卓娅暗示:她每一次来都弄得大家有点酸溜溜的,似乎大家能从她那微带睡容的脸蛋上、从她眼睛底下的黑晕里和两片嘴唇之间,觉察出她答应人家干的不体面事情的迹象;而这码事在她和那些医疗营的年轻医生之间是有可能发生的,因为途中大部分时间卓娅都坐在救护车厢里,跟他们在一起。库兹涅佐夫猜想,卓娅每次停车都跑到连里来,并不仅仅为了检查卫生,她在寻找机会跟德罗兹多夫斯基接触。
“连里一切正常,卓娅,”库兹涅佐夫说,“不必作任何检查。而且正在开早饭。”
卓娅耸耸肩膀说:“这个车厢真特别,没有一个要看病的!别装出那副什么都不懂的样子,你们这样不行!”她睫毛—扬,打量了库兹涅佐夫一眼,莫名其妙地笑着。“您那敬爱的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在这样大成问题的雪浴之后,我想,他不会出现在前线,而将出现在医院里!”
“第一,他不是我敬爱的。”库兹涅佐夫问答:“第二……”
“谢谢您对我说实话,库兹涅佐夫。第二呢?第二您对我是怎么想的?”
德罗兹多夫斯基中尉已经穿好衣服,正用皮带把军大衣束紧,新手枪套在皮带上晃荡着。他轻巧地跳到雪地上,瞧瞧库兹涅佐夫,又瞧瞧卓娅,慢吞吞地说:“卫生指导员,您说说,我象个想做逃兵的人吗?”
卓娅挑衅地把头一扬说:“可能正是这样……至少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
“我告诉您,”德罗兹多夫斯基断然地说,“您不是班主任,我也不是小学生。请您回到救护车厢去吧,明白吗?……库兹涅佐夫,您留下来代我负责一下,我到营长那里去。”
德罗兹多夫斯基带着叫人揣摩不透的表情,举手行了个军礼。他腰间紧束着皮带和新武装带,迈着优美的队列军人的灵活矫健的步伐,从车厢附近来来去去的士兵身边走过去。士兵们一见到他就不吭声了,纷纷给他让路,仿佛他的目光能把大家推开似的。他一边走,一边随便举举手向土兵们还礼。太阳被一道道彩虹环绕着,挂在白晃晃的草原上空。水井周围,人群依然时聚时散。人们在那儿打好水,接着脱下军帽,缩着身子,呼哧呼哧地洗脸,然后他们向列车中段冒着诱人炊烟的炊车那儿跑去,路上谨慎地绕过几个营部军官——他们都站在一节蒙着厚霜的客车车厢旁边。
德罗兹多夫斯基向这几个军官走去。
这时库兹涅佐夫看到,卓娅圆睁微斜的眼睛,带着无可奈何的表情目送连长远去。他问道:“您在我们这里吃早饭吧?”
“什么?”她心不在焉地问。
“跟我们一块儿吃早饭。您大概还没吃过吧。”
“中尉同志,都要冷掉了!我们在等您呐,”涅恰涅夫在车门口叫了一声。“豌豆羹,”他从饭盒掇舀起—‘匙羹来,舔小胡子说,“只要不噎死,终归能活着!”
在他背后,士兵们正挤挤嚷嚷地从摊开的大衣上领取自己的一份早餐,有的在满意地说笑,有的则嘟哝着坐到铺上,把匙子放进饭盒里,咬起冻硬了的黑面包来。现在谁也顾不上卓娅了。
“戚比索夫!”库兹涅佐夫唤道。“快把我的饭盒拿给卫生指导员!”
“小护士!您怎么啦?”戚比索夫在车厢里用悦耳的声音答应着,“我们这儿,可以说,是一帮快活人。’
“是的……很好,”卓娅漫不经心地说。“也许……当然,库兹涅佐夫中尉。我没吃过早饭。不过……为什么要用您的饭盒?您自己呢?”
“我等一会。不会挨饿的,”库兹涅佐夫回答。
戚比索夫急急忙忙地咀嚼着,走列车门口,不知怎么一来,就从翻起的领子里过分殷勤地伸出了胡子拉碴的小脸,他象孩子做游戏那样,愉快地朝卓娅点点头。他长得很瘦小,身上穿着一件短得难看又宽得不象样子的军大衣。
“上来吧,小护士!这有什么关系!……”
“我在您的饭盒里吃一点好了,”卓娅对库兹涅佐夫说。“一定得跟您一道吃,否则我就不吃……”
士兵们呼哧呼哧地吃着早饭。但在喝了几勺子热羹和几口糖开水之后,他们又开始用探索的目光打量起卓娅来了。她解开了短皮袄的领口,展出洁白的脖子,小心翼翼地从库兹涅佐夫的饭盒里舀羹吃,她把饭盒放在膝盖上,在许多人目光的注视下低垂着眼睛。
库兹涅佐夫同卓娅一道吃着,尽量不去看她怎样斯文地把汤匙送到唇边,在吞咽食物时喉头怎样活动。她那低垂的睫毛已被溶化了的霜花沾湿,粘在一起,乌油油地恰好遮住她那心神不定的眼睛。卓娅在烧得通红的火炉边感到热,便脱下帽子,让栗色的头发披散在皮袄的白毛领子上。帽子一脱顿时使她换了一副无可掩饰的可怜巴巴的模样。她颧骨挺高,嘴巴很大,一张绷紧的、甚至怯生生的孩子气的脸,在炮兵们由于吃饭而热得出汗的红脸膛中间,显得异常突出。库兹涅佐夫第一次发现;她长得并不漂亮。他过去从未见过卓娅不戴帽子。
“察伊尔公园里玫瑰开,察伊尔公园里春天来……”
涅恰耶夫中士叉开两腿站在铺边,他喝过茶了,正在那儿卷烟卷,一面轻声哼着歌儿,带着温存的浅笑打量着卓娅。
戚比索夫则特别殷勤地倒来满满一杯茶递给卓娅。
她用手指接过很烫的茶杯,不好意思地说:“谢谢,戚比索夫。”
她抬起水汪汪的眼睛看着涅恰耶夫说:“您说说,中士,这是怎么样的公园和玫瑰呀?我不懂,为什么您老是唱这个?”
士兵们活跃起来了,怂恿涅恰耶夫说:“讲吧,讲吧,中士。问你这支歌是打哪儿来的?”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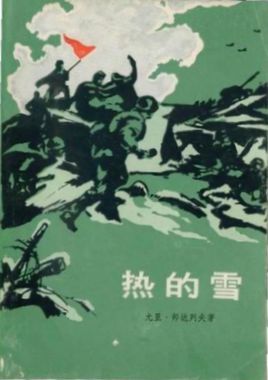 作者:邦达列夫(苏)
作者:邦达列夫(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