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个故事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说的是###世界大战中的短暂和平。1914年圣诞节,交战国的士兵们放下武器,在前线的无人区共同欢度圣诞节。几个星期来躺在无人区没有被埋葬的死者由敌对的双方在“永远安息”的祈祷声中共同掩埋。战场成了交换烟丝、烟斗、葡萄干布丁、雪茄、朗姆酒、啤酒、葡萄酒的场所。他们互相述说渴望,展示家人的照片,甚至比赛足球。战壕上面立起了圣诞树,铁丝网上燃起了蜡烛。互为敌人的士兵唱起了圣诞歌,祝福圣诞快乐,希望和平持久
前言 罂粟花开遍佛兰德大地
西方小说中曾用罂粟花比喻和纪念战场上牺牲的战士,当我译完《战争中的平安夜》时,我似乎找到了这一比喻的出典:位于比利时的佛兰德大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主战场,1914至1918年,成百万的交战国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在这里倒下,鲜血横流,最后都被埋在这片土地下。他们的鲜血哺育着罂粟花,于是罂粟花开得血红血红的。每当人们看见这些美丽鲜红的罂粟花,便会追思起为统治者利益而战死在这里的丈夫、儿子、父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出兵占领了比利时,于是英、法等协约国相继出兵对付德国,比利时的佛兰德成了西线大战场。伊珀尔是战役最频繁的地方,大战期间,英国军士在这里丧生的最多。从此以后,伊珀尔一直是英国人民纪念阵亡男儿的地方。
战争是德国发动的,在统治者、好战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蛊惑、煽动和欺骗下,无数德国青年作为志愿兵而激情满怀地踏上战场,“争取为祖国、为德意志而光荣地战死沙场”。然而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们醒悟过来,他们认识到英国士兵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倒霉的战争快点结束,早点回家去。
1914年圣诞节来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发生了——交战国士兵自发协议停战,共同欢度圣诞节。12月24日(平安夜)黄昏,德国士兵向英国士兵大声喊道:“圣诞快乐,英国人!”接着举起牌子“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英国士兵也举起牌子“我们不打仗,你们不打仗”。消息在佛兰德战场所有的战壕里传开,互为敌人的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战壕上面立起了圣诞树,点起了蜡烛,双方齐唱圣诞歌。第二天,几个星期来躺在战地无人区的阵亡士兵由双方士兵共同在“永远安息”的祈祷声中掩埋掉。战场成了交换烟丝、烟斗、烧酒、罐头食品……的市场,一天前还是互相敌视的男儿们掏出家里人的照片给对方看,诉说他们渴望家乡、思念家庭的衷肠……很多战区的士兵们甚至比赛起足球来。
然而“圣诞和平”令那些远离枪林弹雨的总参谋部先生们十分慌张,他们决不允许滋长和平,用军纪处罚和军事法庭来威胁士兵和下级军官,下令继续开火……1915年圣诞节前,交战国的总参谋部事先下达严格命令,以防止1914年的“圣诞和平”重新出现。尽管如此,不少战区的战士们还是斗胆跟上级指挥官玩花招,总参谋部来人视察了,双方士兵便乒乒乓乓地开起火来,可是子弹全部打偏,在双方脑袋上方飞过,没有一个人被命中。
和平终于没有能持续下去,战争打了4年,900万士兵为这次大战付出了生命。人们从战争中得出教训:应该让发动战争的人亲自上前线去打仗;全世界母亲联合起来,不要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上战场。
《战争中的平安夜》一书以丰富完整的真实资料为基础,向读者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好战分子的丑恶嘴脸、战场(阵地战)的残酷和严峻苦难的戎马生活、年轻一代被无辜糟蹋、士兵们从厌战反战到自发协议停战,写下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圣诞和平”篇章。
本书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于1945年出生在德国埃尔万根,在汉堡和克雷费尔德长大,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日尔曼学和历史学专业肄业。1965年起在《慕尼黑晚报》工作,1968年起担任该报副刊部主任。1986至1990年任《明星》周刊和《速度》杂志主编。1992至1993年担任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访谈节目副主持,2003年9月后执笔《德国金融时报》社论。
于尔格斯写过多种通俗专业书及人物传记,很多都被列入《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被拍成影片。主要作品有《罗密·施奈德的衰落》、《阿克赛尔·施普林格的衰落》、《受托人——英雄和骗子如何出卖民主德国》、《早老性痴呆者在无人区寻找踪迹》、《真想吻这些女人:理查德·陶贝尔传》、《公民格拉斯——一个德国文学家的生平》以及政治惊险小说《克列奥帕特拉阴谋》。
《战争中的平安夜》是一本提倡人道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报告文学,书中的许多真实细节十分感人,它们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至少能让读者掉下感动的眼泪。站在成百万无辜阵亡者的墓前,让我们一起朗诵“太阳纵然会落山,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
陈钰鹏
2006年7月于上海十方阁
第一章 静静的夜——莱茵河畔无设防
起先只是独唱“静静的夜,明亮的夜”,歌声轻轻飘逝在死一样寂静的佛兰德地区,但接着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地响彻战地,“越过一个一个的防卫墙,沿着整条又长又黑的战壕直冲云霄:‘睡吧,在美妙的宁静中’”。战地的这边,相隔一百米的地方,英军的阵地上非常安静。而德国士兵们兴致正高,歌儿一首接着一首,“犹如几千男歌喉组合成的音乐会”。直至唱完“蔷薇绽出花蕾”,喘不过气来为止。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后,英军的士兵们又等了一分钟,接着开始鼓掌,开始叫:“好!老弗里茨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受到这种方式表扬的弗里茨们用“圣诞快乐,英国人”及“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来回答,他们所叫喊的话是认真的,他们在几乎高出战壕边一米的防卫墙顶部放上蜡烛并将它们点着。接着,烛光像排成行的珍珠在黑暗中闪烁。一个英国士兵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就像剧院里的脚灯灯光。”
演出的舞台就这样被照得通亮,今后几天将在西线演出的戏剧总排练成功了。这儿,那儿,从北海到瑞士边界到处都是这样。天堂里的上帝为佛兰德地区创造了最好的外部条件。这是1914年12月24日,夜幕降临以后——16点左右天已经黑了——开始刮风了。清朗的星空“从上帝的住所向我们问候”,圆满的月亮“用她温柔的月光向伦勃朗故乡辽阔美丽的佛兰德大地预示着美好的和平”。
现在两者都在帮忙,月亮和蜡烛,无人区里的每一个可疑动作都看得很清楚。荣誉属于苍天和上帝,和平属于大地的人们,基督福音是如此宣告这一天的。而地上的高级长官显然不在,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自发地决定(法国士兵和比利时士兵有点犹豫),不等上帝的恩赐而停止互相射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和平,以后也没有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伟大的圣诞故事由许多小故事组成。
欲知这些故事的神妙,就必须把它们全讲出来。
开始,德国人的举动把对方给弄糊涂了,他们不敢相信会有和平。难道又是野蛮人的诡计?又是阴险的迷惑?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人记忆犹新:一支德国部队在英国部队的视野中趴在了地上,放下了武器,于是英国部队也扔下武器,朝德军走去。突然,在这些似乎厌倦了战争的德国士兵后面,从掩蔽部里冒出了带着尖顶头盔、把枪瞄准了英国士兵的德国兵,眼看这就是一场凶杀。普鲁士人,他们就是以冷酷无情出名的。瞬息间,几十个汤米① 倒在了铁丝网前面。
一位名叫马塔尼亚的战争画家根据目击者萨金特·梅加里的描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伦敦的《环球》杂志将这幅画刊印在两个版面上发表。“英国人永远不会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不管他们出生于哪个阶层,都不会做。”这是这幅画的标题,完全符合舆论的意见。对坦诚好意的人射击,就因为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因为是在打仗,这是没有人性的行为,如此卑鄙的事情和英国的国民性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这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英国皇家第10兵团的总司令布莱顿·麦金内尔( 利物浦 的苏格兰人)也是个典型的德国人了,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也让士兵们这么做。麦金内尔待在伊珀尔到维查特的公路上,在德国兵的对面。他在191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各种各样关于敌人在战壕间遭遇英国军队的故事都讲到了,所幸保卫我们战线的部队干脆就在等,一直等到德国人从他们的战壕里出来,于是快速射击,将他们击毙,从而结束了友好联谊这样的蠢事。”
麦金内尔的日记是收藏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博物馆里的文献之一,也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关于比利时北部战场的资料之一。收藏在伊珀尔的“佛兰德战地博物馆”——原来的大集市广场旁的布商商会,伊珀尔是今天常用的“伊普尔”的佛兰德语名字。由于英国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在这里阵亡的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多,也比其他“毁灭性战场”上多,所以这个人们通常以法文名字“伊普尔”相称的城市,对英国人来讲具有象征意义。
在这里发生过4次战役,最后伊珀尔成了废墟。德国人占领她只有一天时间,即1914年10月第一次伊珀尔战役时。在今后几年中,英军誓死保卫这个城市,以阻止德国联合兵团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挺进,因为德军想在这些地方断绝英军的给养。德国炮兵将这个中世纪以布商商会和圣马丁教堂出名的富庶小城夷为平地。被载入史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城已经没有一座房子了,教堂和商会的前面只留下塔的残骸。以前,在晴朗清澈的日子里,从塔上可以看到北海。
每次战役都会死去很多人,而实际上伊珀尔的战役是不断的。从1914年至1918年有50万英国人在这里丧生,1917年7月的第三次战役中就有25万人阵亡。同样,许多德国人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伊珀尔后面不远的帕森达勒有10万英国士兵献出了生命。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后来的英国宰相劳埃德·乔治谈到英国第一军团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将军时说:“失去多少士兵,对黑格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他干脆就是在糟蹋这些年轻小伙子的生命。”在所谓的英国重大胜利后,当他看到死亡名单上列着这些可怕的数字时,他可能会希望以后不要这么经常打胜仗了。
整个大战中,不列颠联合王国失去了76.4万名士兵,他们为了保卫伊珀尔,和德军确确实实战斗到阵亡为止。当时英国国防部长温斯顿因此于1919年1月建议,将废墟城伊珀尔从比利时买过来或者请求比利时人民将她作为礼物送给英国人民以纪念阵亡的英国将士:“我希望,我们能获得伊珀尔废墟……对英国人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更神圣的地方了。”以前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重建,伊珀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公墓,一个告诫后人的纪念碑,墓碑上写着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坟上开着罂粟花。
事情没有完全按英国人的愿望进行。但比利时也不需要用她的废墟来纪念不幸的事件,若利·埃莱皮特部长宣布说。1915年从伊珀尔逃亡出去的居民,战后,回到了他们被摧毁得只剩墙基的城市,在废墟上安下家来,然后重建家园。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在伊珀尔获得了他们的纪念碑——城门的残骸作为纪念碑的基础,马路从集市大广场穿过城门通往梅南。除此以外,战后的城门已没有剩下别的东西了。卡斯特尔运河上的大桥同样也躺在了废墟中。
“梅南门”于1927年隆重开放,一块白色的大石碑,它不像一个城门,倒是更像一个纪念馆;它不像比利时的拱形凯旋门,而更像 罗马 式凯旋门,壁上刻着将近55000名英国士兵的名字。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些士兵的踪迹,因此也就没法埋葬他们。这里的名字远远没有包括所有的士兵,真要将所有名字刻上去,地方也不够。
每天晚上将近8点钟,这个地方变得寂静无声,交通中断,本地的车辆绕道行驶,每当这个时候,凯旋门不准通行。8点整,号手们来到凯旋门的圆顶下吹起集合点名号——军人葬礼号,每天晚上是同样的程序。不到10分钟的仪式已经举行了75年,但在二次大战德军占领下没有举行,即1940年5月20日至1944年9月6日。每天晚上,两次大战后出生的人都等在凯旋门下,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本地人,有旅游者,有许多是英国人,德国人很少。
有一天晚上,在街道中间站着一个老人,他也许80岁,可能更老一些。船形军帽斜戴在他细发的头上,他的眼睛不朝任何地方看,他站直了身子,直至号声结束。然后他拉开嗓门,声音就像以前当兵时一样响亮,这位曾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 的士兵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士兵发誓:“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周围的人也轻声重复着他的话,以表认同:“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当然能背出劳伦斯·比尼恩于1914年9月为阵亡士兵所写的叙事诗《献给阵亡者》的第四小节。比尼恩早就去世了,他的作品也被忘却了,然而这几行诗却活着,每逢纪念日,在所有的纪念碑前被活着的人朗诵着,而这样的纪念碑在佛兰德地区太多了:
他们不会老,不像我们活着的人,
年龄不能屈服他们、不会压垮他们。
太阳纵然会落山,
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
老人将手靠到帽檐上,向死者致敬。从通向纪念碑平台两侧台阶的一侧,他登上平台。平台上永远有灯光照耀。他在那儿放了一个红色罂粟花做成的花环,罂粟花是佛兰德大地之花。“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纵然太阳落山了,就像现在一样,愿它明天早上仍然升起来。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他又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身回到街道中间,把眼角的一滴眼泪擦掉。
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来到这里,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代表大家放下一个花圈。大部分参与者——学生、老兵联谊会、妇女协会——坐渡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欧洲大陆,然后再坐汽车直到这里。伊珀尔成了朝圣地,多少代过去了,始终还是朝圣地。
在“梅南门”的附近,当年发生过战壕之间的流血事件,《环球》杂志用素描作品为读者表现了这些事件,证实了英国人的所有看法。英国人对德国人毫不留情的民族性颇有成见,德国人被讨厌地称为蛮子或匈奴。让人最初和匈奴联想起来的人是德国皇帝,因为他于1900年要求他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就像以前的匈奴那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今天,只要是跟德国人比赛足球,观众中仍然会产生愤恨的情绪;直至今天,德国人在英国的马路小报中仍然被这样臭骂。
所以,当这些所谓的匈奴在平安夜——圣诞节的前夜突然不再开枪而开始唱歌时,没有人敢相信他们,尽管他们的蜡烛在和平地闪烁。难道它们是为德国炮兵提供的目标,好让他们准确地对着英国人的战壕轰击?或者是为了引起英国士兵的好奇,让他们将身子露出防卫墙,轻而易举地成为德国优秀射手们的战利品?英国人还是继续隐蔽着,不相信德国人,尽管他们喜欢这些歌,尽管温馨的旋律感动着他们,但这不等于喜欢德国人,他们喜欢的是音乐——世界人民的语言。
有的英国人用至今在前线通用的方式作出反应。将近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区一支德国军乐队开始演奏圣诞歌曲时,苏格兰炮兵军官从后方指挥自己独有的“声部”——炮弹直接击中乐队。“你们可以想象,这些奏乐的人成了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马拉德夫妇的一个儿子向在怀特岛的父母报道说。
第二章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
不列颠联合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争端也是一场家族的不和。1914年6月的基尔,战争爆发前不到6周,德国皇帝穿着英国一位海军上将的制服拍照,他觉得“穿着洛德·纳尔逊穿过的制服”很威风。德皇不仅是英国轻骑兵的名誉上校,而且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上将,而他的堂兄乔治是普鲁士近卫军第一兵团的军官。4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在其伯父爱德华(英国国王)的葬礼后已经写道:“英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作为英国皇家的一员是美好的事情,威廉二世也就很自然地邀请他亲戚的海军去基尔参加帆船节,并愉快地结盟。
友好、建立兄弟般关系,不久便被视为谋反,这只是一个日期问题。1914年6月28日,这天,一个行刺者在萨拉热窝结束了奥地利加冕王子费迪南及其年轻妻子索菲的生命。因为塞尔维亚政府——至少是秘密警察——卷入了这次谋杀事件,所以一举杀两人的行刺事件带来了严重后果。战争发动者早就在寻找开战的借口了,这一次机会便是一个好借口。开始是唇枪舌战,接着于8月4日爆发了真正的战争。
首先,在德国政府的鼓动和支持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人宣战。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便做好了作战准备,德意志帝国立即作出反应,因为他觉得受到莫斯科及其同盟者巴黎的包围和威胁,因此打着“解放”的旗号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按闪电计划便是迅速朝法国首都方向进军。德意志帝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保证德军畅通无阻通过比利时,却遭到比利时政府的拒绝。
德军于是袭击这一中立国,开进了这个国家,他们不仅占领了比利时,而且还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大部分地方。现在,英国不得不作出反应了,并让英国在比利时的亲戚知道,在侵犯中立国比利时、袭击与英国结盟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后,这些国家之间要交战了。战争爆发了。战争为什么没有被阻止?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大约有7039种。
畅销书《世界大战》的作者H·G·威尔斯在回顾1914年夏天时写道,每一个聪明人都看到了可怕事情会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去避免这场灾难,而最不想避免灾难的是德国皇帝,他成了总参谋部里狂热的好战分子。
德国人民的宠儿威廉二世——由于在他摄政期间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一片升平——被普鲁士政权中的“优秀分子”所操纵,他们利用这位实际上懦弱、沾沾自喜和胆小怕事的专制君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直至这位皇帝的自吹自擂不再涉及他那些高贵的英国亲戚,而只会降格谈他们那些被人轻视的微不足道的弱小军队。
从此以后,英国的职业兵便自称“微不足道的老兵”。这种自豪的戏称实际上是国防部宣传处的成绩,他们想以此达到调动出征军团战斗力的目的。说其来自德国皇帝,这纯粹是无中生有,人们只是借他之口罢了。于是在英国激起了人们反德国人及其傲慢的最高统帅的情绪,预期效果达到了。
1914年8月3日,从海边度周末回来的英国人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碰到了数百名德国人。他们尽管多年来生活在英国,以 出租车 司机、服务生、理发师、商人为业,但现在却必须服从他们祖国的召唤。绝大部分人都以电报形式收到了这一召唤,要求他们赶快坐英国火车到海边的轮渡站,返回以前的家乡。他们把家庭留下了,告别了邻居和朋友。在德军袭击比利时并正式宣战后的第二天,这些邻居和朋友就成了这些德国人的敌人,而实际上他们之间毫无冤仇。
战争爆发的前几天,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示威反战,这么多人游行在欧洲任何大城市从来没有过。在柏林和巴黎有几千人失踪,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和德国人就想结束战争,在第一片树叶凋落以前,最晚到圣诞节以前。在英国对判定谁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军事独裁者是敌人,德国人民不是敌人。坐船到 汉堡 来回,8月8日旅行社的票价还是45先令,几天后报纸上还在为1915年德累斯顿之夏音乐会做广告呢。
然而,几个月后,即1914年底,黑色和白色成了时尚的流行色,人民的意志占了上风,但报纸上的基调是打仗;怀疑之色——不显眼的灰色已经没有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国,有的爱国者除掉了他们所养的猎獾狗,因为猎獾狗是德国品种;在德国,培养精英们的高贵女儿的教育机构,即按照英国的好传统培养“英国小姐”的机构,必须将名字改掉。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正在开始的民主时代被逼得无路可走,在重要的西欧国家,尽管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占大多数(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席位远远多于其他政党;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处于执政位置;在法国是社会主义党人掌握政权),然而,当战争爆发时,他们的理想破灭了。
德国人的形象——欧洲蛮子,这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许多看法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德国的将军、实业家、政治家、出版家,他们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了,他们以优越者自居,用强有力的口号“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上的一切”凌驾于别国之上。皇帝用来号召“德国人民”去发动战争的语言是当时典型的德意志时代精神:“战争势在必行,敌人在和平时期袭击我们,所以我发出号召!拿起武器!任何动摇、任何犹豫都是对祖国的背叛。事关我们父辈创立的帝国的存亡,事关德意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亡。我们要抵抗,直至人和马匹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们会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哪怕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德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只要团结一致,和上帝一起前进。上帝曾和我们的父辈们在一起,上帝也将和我们在一起。”用行动开始,不考虑后果,这是典型的日耳曼本性。这种本性只怕上帝。根据这种本性,世界应该按德意志精神发展才健康。皇帝的口号在30年以后还可以这么写,用这种腔调,用这种语言,在另外一个帝国,有一个人签字,他现在正兴高采烈地学着这一号召: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只有像1914年的德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能单独跟别的军队作战。”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御林军步兵团的编年史家大声说,“在军队里,每个人都通过经常骂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严格教育和训练,而成为没有缺陷的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像1914年的德军那样的团结一致的、德国人民和祖国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没有过。”而这样的咆哮,确实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德意志帝国有一首所谓的《仇恨英国歌》,它充分体现了德意志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头的流行小调。此歌为某一个名叫恩斯特·利绍尔的德国人所作,作为德国声嘶力竭追求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据、作为傲慢的普鲁士主义的证据。这首歌被译成英文,在许国英国报纸上刊登。一个未经训练的半吊子所写的语无伦次的东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个国家毕竟都有偏执者,何况那些年代已经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对英国的仇视竟然变成了一种民族诗,用来增强本民族的偏见,影响本国人民的情绪,毒害他们的思想。
这位笔杆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获得了一枚勋章。德国的小学生必须背诵他写的诗,威廉二世让人将这些诗印成传单、分发给部队:
我们只有唯一的敌人:
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
他蜷缩在灰色的海峡对面,
满怀嫉妒、满怀愤恨、
充满阴险、充满狡诈,
一水之隔,水浓于血,
我们要控告。
我们发誓,共同发誓。
我们发誓,风吹不动。
我们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发誓。
听着这句话,重复这句话,
它传遍整个欧洲:
不放弃仇恨,
我们只有一个恨,
我们一起爱,我们一起恨,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
后来发表在《每日图报》上的反击诗体现出了激情——“打到德国人 / 全部打到……
前言 罂粟花开遍佛兰德大地
西方小说中曾用罂粟花比喻和纪念战场上牺牲的战士,当我译完《战争中的平安夜》时,我似乎找到了这一比喻的出典:位于比利时的佛兰德大地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西线主战场,1914至1918年,成百万的交战国士兵(包括下级军官)在这里倒下,鲜血横流,最后都被埋在这片土地下。他们的鲜血哺育着罂粟花,于是罂粟花开得血红血红的。每当人们看见这些美丽鲜红的罂粟花,便会追思起为统治者利益而战死在这里的丈夫、儿子、父亲……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德国出兵占领了比利时,于是英、法等协约国相继出兵对付德国,比利时的佛兰德成了西线大战场。伊珀尔是战役最频繁的地方,大战期间,英国军士在这里丧生的最多。从此以后,伊珀尔一直是英国人民纪念阵亡男儿的地方。
战争是德国发动的,在统治者、好战分子和极端民族主义者的蛊惑、煽动和欺骗下,无数德国青年作为志愿兵而激情满怀地踏上战场,“争取为祖国、为德意志而光荣地战死沙场”。然而残酷的现实终于使他们醒悟过来,他们认识到英国士兵不是他们的敌人。他们只有一个想法:倒霉的战争快点结束,早点回家去。
1914年圣诞节来临,人类战争史上的奇迹发生了——交战国士兵自发协议停战,共同欢度圣诞节。12月24日(平安夜)黄昏,德国士兵向英国士兵大声喊道:“圣诞快乐,英国人!”接着举起牌子“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英国士兵也举起牌子“我们不打仗,你们不打仗”。消息在佛兰德战场所有的战壕里传开,互为敌人的士兵们纷纷放下武器,战壕上面立起了圣诞树,点起了蜡烛,双方齐唱圣诞歌。第二天,几个星期来躺在战地无人区的阵亡士兵由双方士兵共同在“永远安息”的祈祷声中掩埋掉。战场成了交换烟丝、烟斗、烧酒、罐头食品……的市场,一天前还是互相敌视的男儿们掏出家里人的照片给对方看,诉说他们渴望家乡、思念家庭的衷肠……很多战区的士兵们甚至比赛起足球来。
然而“圣诞和平”令那些远离枪林弹雨的总参谋部先生们十分慌张,他们决不允许滋长和平,用军纪处罚和军事法庭来威胁士兵和下级军官,下令继续开火……1915年圣诞节前,交战国的总参谋部事先下达严格命令,以防止1914年的“圣诞和平”重新出现。尽管如此,不少战区的战士们还是斗胆跟上级指挥官玩花招,总参谋部来人视察了,双方士兵便乒乒乓乓地开起火来,可是子弹全部打偏,在双方脑袋上方飞过,没有一个人被命中。
和平终于没有能持续下去,战争打了4年,900万士兵为这次大战付出了生命。人们从战争中得出教训:应该让发动战争的人亲自上前线去打仗;全世界母亲联合起来,不要让自己的丈夫和儿子为了统治阶级的利益上战场。
《战争中的平安夜》一书以丰富完整的真实资料为基础,向读者展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好战分子的丑恶嘴脸、战场(阵地战)的残酷和严峻苦难的戎马生活、年轻一代被无辜糟蹋、士兵们从厌战反战到自发协议停战,写下人类战争史上绝无仅有的“圣诞和平”篇章。
本书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于1945年出生在德国埃尔万根,在汉堡和克雷费尔德长大,慕尼黑大学政治学、日尔曼学和历史学专业肄业。1965年起在《慕尼黑晚报》工作,1968年起担任该报副刊部主任。1986至1990年任《明星》周刊和《速度》杂志主编。1992至1993年担任北德意志广播电视台访谈节目副主持,2003年9月后执笔《德国金融时报》社论。
于尔格斯写过多种通俗专业书及人物传记,很多都被列入《明镜》周刊的畅销书排行榜并被拍成影片。主要作品有《罗密·施奈德的衰落》、《阿克赛尔·施普林格的衰落》、《受托人——英雄和骗子如何出卖民主德国》、《早老性痴呆者在无人区寻找踪迹》、《真想吻这些女人:理查德·陶贝尔传》、《公民格拉斯——一个德国文学家的生平》以及政治惊险小说《克列奥帕特拉阴谋》。
《战争中的平安夜》是一本提倡人道主义和反对战争的报告文学,书中的许多真实细节十分感人,它们甚至可以改变一个人的观念,至少能让读者掉下感动的眼泪。站在成百万无辜阵亡者的墓前,让我们一起朗诵“太阳纵然会落山,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
陈钰鹏
2006年7月于上海十方阁
第一章 静静的夜——莱茵河畔无设防
起先只是独唱“静静的夜,明亮的夜”,歌声轻轻飘逝在死一样寂静的佛兰德地区,但接着如潮水般汹涌澎湃地响彻战地,“越过一个一个的防卫墙,沿着整条又长又黑的战壕直冲云霄:‘睡吧,在美妙的宁静中’”。战地的这边,相隔一百米的地方,英军的阵地上非常安静。而德国士兵们兴致正高,歌儿一首接着一首,“犹如几千男歌喉组合成的音乐会”。直至唱完“蔷薇绽出花蕾”,喘不过气来为止。最后一个音符消失后,英军的士兵们又等了一分钟,接着开始鼓掌,开始叫:“好!老弗里茨①,再来一个,再来一个。”
受到这种方式表扬的弗里茨们用“圣诞快乐,英国人”及“我们不开枪,你们不开枪”来回答,他们所叫喊的话是认真的,他们在几乎高出战壕边一米的防卫墙顶部放上蜡烛并将它们点着。接着,烛光像排成行的珍珠在黑暗中闪烁。一个英国士兵在给他父母的信中写道:“就像剧院里的脚灯灯光。”
演出的舞台就这样被照得通亮,今后几天将在西线演出的戏剧总排练成功了。这儿,那儿,从北海到瑞士边界到处都是这样。天堂里的上帝为佛兰德地区创造了最好的外部条件。这是1914年12月24日,夜幕降临以后——16点左右天已经黑了——开始刮风了。清朗的星空“从上帝的住所向我们问候”,圆满的月亮“用她温柔的月光向伦勃朗故乡辽阔美丽的佛兰德大地预示着美好的和平”。
现在两者都在帮忙,月亮和蜡烛,无人区里的每一个可疑动作都看得很清楚。荣誉属于苍天和上帝,和平属于大地的人们,基督福音是如此宣告这一天的。而地上的高级长官显然不在,德国士兵和英国士兵自发地决定(法国士兵和比利时士兵有点犹豫),不等上帝的恩赐而停止互相射击,战争史上从来没有过这种自下而上的和平,以后也没有过。以今天的眼光来看,这个伟大的圣诞故事由许多小故事组成。
欲知这些故事的神妙,就必须把它们全讲出来。
开始,德国人的举动把对方给弄糊涂了,他们不敢相信会有和平。难道又是野蛮人的诡计?又是阴险的迷惑?几个星期前的某一天发生的事情让人记忆犹新:一支德国部队在英国部队的视野中趴在了地上,放下了武器,于是英国部队也扔下武器,朝德军走去。突然,在这些似乎厌倦了战争的德国士兵后面,从掩蔽部里冒出了带着尖顶头盔、把枪瞄准了英国士兵的德国兵,眼看这就是一场凶杀。普鲁士人,他们就是以冷酷无情出名的。瞬息间,几十个汤米① 倒在了铁丝网前面。
一位名叫马塔尼亚的战争画家根据目击者萨金特·梅加里的描述表现了当时的情景。伦敦的《环球》杂志将这幅画刊印在两个版面上发表。“英国人永远不会做这种不光明正大的事情,不管他们出生于哪个阶层,都不会做。”这是这幅画的标题,完全符合舆论的意见。对坦诚好意的人射击,就因为他们穿着不同的军服、因为是在打仗,这是没有人性的行为,如此卑鄙的事情和英国的国民性是格格不入的。
如果这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的话,那么英国皇家第10兵团的总司令布莱顿·麦金内尔( 利物浦 的苏格兰人)也是个典型的德国人了,他毫不掩饰地承认,他也让士兵们这么做。麦金内尔待在伊珀尔到维查特的公路上,在德国兵的对面。他在1915年1月14日的日记中这样写道:“各种各样关于敌人在战壕间遭遇英国军队的故事都讲到了,所幸保卫我们战线的部队干脆就在等,一直等到德国人从他们的战壕里出来,于是快速射击,将他们击毙,从而结束了友好联谊这样的蠢事。”
麦金内尔的日记是收藏在一个非常特殊的博物馆里的文献之一,也是目击者和当事人关于比利时北部战场的资料之一。收藏在伊珀尔的“佛兰德战地博物馆”——原来的大集市广场旁的布商商会,伊珀尔是今天常用的“伊普尔”的佛兰德语名字。由于英国在1914至1918年的战争中损失惨重,在这里阵亡的英国人比其他欧洲人多,也比其他“毁灭性战场”上多,所以这个人们通常以法文名字“伊普尔”相称的城市,对英国人来讲具有象征意义。
在这里发生过4次战役,最后伊珀尔成了废墟。德国人占领她只有一天时间,即1914年10月第一次伊珀尔战役时。在今后几年中,英军誓死保卫这个城市,以阻止德国联合兵团向英吉利海峡的港口挺进,因为德军想在这些地方断绝英军的给养。德国炮兵将这个中世纪以布商商会和圣马丁教堂出名的富庶小城夷为平地。被载入史册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该城已经没有一座房子了,教堂和商会的前面只留下塔的残骸。以前,在晴朗清澈的日子里,从塔上可以看到北海。
每次战役都会死去很多人,而实际上伊珀尔的战役是不断的。从1914年至1918年有50万英国人在这里丧生,1917年7月的第三次战役中就有25万人阵亡。同样,许多德国人也成了战争的牺牲品。在伊珀尔后面不远的帕森达勒有10万英国士兵献出了生命。当时的英国财政大臣,后来的英国宰相劳埃德·乔治谈到英国第一军团司令道格拉斯·黑格将军时说:“失去多少士兵,对黑格来说完全是无所谓的,他干脆就是在糟蹋这些年轻小伙子的生命。”在所谓的英国重大胜利后,当他看到死亡名单上列着这些可怕的数字时,他可能会希望以后不要这么经常打胜仗了。
整个大战中,不列颠联合王国失去了76.4万名士兵,他们为了保卫伊珀尔,和德军确确实实战斗到阵亡为止。当时英国国防部长温斯顿因此于1919年1月建议,将废墟城伊珀尔从比利时买过来或者请求比利时人民将她作为礼物送给英国人民以纪念阵亡的英国将士:“我希望,我们能获得伊珀尔废墟……对英国人民来说,在这个世界上再没有更神圣的地方了。”以前的任何东西都不需要重建,伊珀尔是一个独一无二的大公墓,一个告诫后人的纪念碑,墓碑上写着所有死难者的名字,坟上开着罂粟花。
事情没有完全按英国人的愿望进行。但比利时也不需要用她的废墟来纪念不幸的事件,若利·埃莱皮特部长宣布说。1915年从伊珀尔逃亡出去的居民,战后,回到了他们被摧毁得只剩墙基的城市,在废墟上安下家来,然后重建家园。尽管如此,英国人还是在伊珀尔获得了他们的纪念碑——城门的残骸作为纪念碑的基础,马路从集市大广场穿过城门通往梅南。除此以外,战后的城门已没有剩下别的东西了。卡斯特尔运河上的大桥同样也躺在了废墟中。
“梅南门”于1927年隆重开放,一块白色的大石碑,它不像一个城门,倒是更像一个纪念馆;它不像比利时的拱形凯旋门,而更像 罗马 式凯旋门,壁上刻着将近55000名英国士兵的名字。在地球上已经找不到这些士兵的踪迹,因此也就没法埋葬他们。这里的名字远远没有包括所有的士兵,真要将所有名字刻上去,地方也不够。
每天晚上将近8点钟,这个地方变得寂静无声,交通中断,本地的车辆绕道行驶,每当这个时候,凯旋门不准通行。8点整,号手们来到凯旋门的圆顶下吹起集合点名号——军人葬礼号,每天晚上是同样的程序。不到10分钟的仪式已经举行了75年,但在二次大战德军占领下没有举行,即1940年5月20日至1944年9月6日。每天晚上,两次大战后出生的人都等在凯旋门下,有年轻的,有年老的,有本地人,有旅游者,有许多是英国人,德国人很少。
有一天晚上,在街道中间站着一个老人,他也许80岁,可能更老一些。船形军帽斜戴在他细发的头上,他的眼睛不朝任何地方看,他站直了身子,直至号声结束。然后他拉开嗓门,声音就像以前当兵时一样响亮,这位曾是第二次 世界大战 的士兵向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阵亡士兵发誓:“我们不会忘记他们,我们不会忘记他们。”周围的人也轻声重复着他的话,以表认同:“是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当然能背出劳伦斯·比尼恩于1914年9月为阵亡士兵所写的叙事诗《献给阵亡者》的第四小节。比尼恩早就去世了,他的作品也被忘却了,然而这几行诗却活着,每逢纪念日,在所有的纪念碑前被活着的人朗诵着,而这样的纪念碑在佛兰德地区太多了:
他们不会老,不像我们活着的人,
年龄不能屈服他们、不会压垮他们。
太阳纵然会落山,
明早我们还会纪念他们。
老人将手靠到帽檐上,向死者致敬。从通向纪念碑平台两侧台阶的一侧,他登上平台。平台上永远有灯光照耀。他在那儿放了一个红色罂粟花做成的花环,罂粟花是佛兰德大地之花。“我们不会忘记他们”。纵然太阳落山了,就像现在一样,愿它明天早上仍然升起来。所有的人都沉默着,他又敬了个军礼,然后转身回到街道中间,把眼角的一滴眼泪擦掉。
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来到这里,每天晚上总有一个像他那样的人代表大家放下一个花圈。大部分参与者——学生、老兵联谊会、妇女协会——坐渡船穿过英吉利海峡来到欧洲大陆,然后再坐汽车直到这里。伊珀尔成了朝圣地,多少代过去了,始终还是朝圣地。
在“梅南门”的附近,当年发生过战壕之间的流血事件,《环球》杂志用素描作品为读者表现了这些事件,证实了英国人的所有看法。英国人对德国人毫不留情的民族性颇有成见,德国人被讨厌地称为蛮子或匈奴。让人最初和匈奴联想起来的人是德国皇帝,因为他于1900年要求他的军队残酷地镇压中国的义和团起义,就像以前的匈奴那样无情地对待敌人。直至今天,只要是跟德国人比赛足球,观众中仍然会产生愤恨的情绪;直至今天,德国人在英国的马路小报中仍然被这样臭骂。
所以,当这些所谓的匈奴在平安夜——圣诞节的前夜突然不再开枪而开始唱歌时,没有人敢相信他们,尽管他们的蜡烛在和平地闪烁。难道它们是为德国炮兵提供的目标,好让他们准确地对着英国人的战壕轰击?或者是为了引起英国士兵的好奇,让他们将身子露出防卫墙,轻而易举地成为德国优秀射手们的战利品?英国人还是继续隐蔽着,不相信德国人,尽管他们喜欢这些歌,尽管温馨的旋律感动着他们,但这不等于喜欢德国人,他们喜欢的是音乐——世界人民的语言。
有的英国人用至今在前线通用的方式作出反应。将近下午4点半钟的时候,在另外一个战区一支德国军乐队开始演奏圣诞歌曲时,苏格兰炮兵军官从后方指挥自己独有的“声部”——炮弹直接击中乐队。“你们可以想象,这些奏乐的人成了什么,后来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声音。”马拉德夫妇的一个儿子向在怀特岛的父母报道说。
第二章 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
不列颠联合王国和德意志帝国之间的争端也是一场家族的不和。1914年6月的基尔,战争爆发前不到6周,德国皇帝穿着英国一位海军上将的制服拍照,他觉得“穿着洛德·纳尔逊穿过的制服”很威风。德皇不仅是英国轻骑兵的名誉上校,而且是英国皇家海军的上将,而他的堂兄乔治是普鲁士近卫军第一兵团的军官。4年前,德皇威廉二世在其伯父爱德华(英国国王)的葬礼后已经写道:“英国是我的第二故乡。”作为英国皇家的一员是美好的事情,威廉二世也就很自然地邀请他亲戚的海军去基尔参加帆船节,并愉快地结盟。
友好、建立兄弟般关系,不久便被视为谋反,这只是一个日期问题。1914年6月28日,这天,一个行刺者在萨拉热窝结束了奥地利加冕王子费迪南及其年轻妻子索菲的生命。因为塞尔维亚政府——至少是秘密警察——卷入了这次谋杀事件,所以一举杀两人的行刺事件带来了严重后果。战争发动者早就在寻找开战的借口了,这一次机会便是一个好借口。开始是唇枪舌战,接着于8月4日爆发了真正的战争。
首先,在德国政府的鼓动和支持下,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人宣战。塞尔维亚的保护国俄国便做好了作战准备,德意志帝国立即作出反应,因为他觉得受到莫斯科及其同盟者巴黎的包围和威胁,因此打着“解放”的旗号向俄国和法国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按闪电计划便是迅速朝法国首都方向进军。德意志帝国向比利时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比利时在12小时内保证德军畅通无阻通过比利时,却遭到比利时政府的拒绝。
德军于是袭击这一中立国,开进了这个国家,他们不仅占领了比利时,而且还占领了法国北部的大部分地方。现在,英国不得不作出反应了,并让英国在比利时的亲戚知道,在侵犯中立国比利时、袭击与英国结盟的法兰西共和国以后,这些国家之间要交战了。战争爆发了。战争为什么没有被阻止?有关这个问题的书大约有7039种。
畅销书《世界大战》的作者H·G·威尔斯在回顾1914年夏天时写道,每一个聪明人都看到了可怕事情会发生,但是没有一个人知道如何去避免这场灾难,而最不想避免灾难的是德国皇帝,他成了总参谋部里狂热的好战分子。
德国人民的宠儿威廉二世——由于在他摄政期间祖国繁荣昌盛、人民幸福、一片升平——被普鲁士政权中的“优秀分子”所操纵,他们利用这位实际上懦弱、沾沾自喜和胆小怕事的专制君主来达到自己的目的,直至这位皇帝的自吹自擂不再涉及他那些高贵的英国亲戚,而只会降格谈他们那些被人轻视的微不足道的弱小军队。
从此以后,英国的职业兵便自称“微不足道的老兵”。这种自豪的戏称实际上是国防部宣传处的成绩,他们想以此达到调动出征军团战斗力的目的。说其来自德国皇帝,这纯粹是无中生有,人们只是借他之口罢了。于是在英国激起了人们反德国人及其傲慢的最高统帅的情绪,预期效果达到了。
1914年8月3日,从海边度周末回来的英国人在伦敦维多利亚火车站碰到了数百名德国人。他们尽管多年来生活在英国,以 出租车 司机、服务生、理发师、商人为业,但现在却必须服从他们祖国的召唤。绝大部分人都以电报形式收到了这一召唤,要求他们赶快坐英国火车到海边的轮渡站,返回以前的家乡。他们把家庭留下了,告别了邻居和朋友。在德军袭击比利时并正式宣战后的第二天,这些邻居和朋友就成了这些德国人的敌人,而实际上他们之间毫无冤仇。
战争爆发的前几天,伦敦有成千上万的人示威反战,这么多人游行在欧洲任何大城市从来没有过。在柏林和巴黎有几千人失踪,大部分是社会民主党或社会党人中的和平主义者。甚至在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英国人和德国人就想结束战争,在第一片树叶凋落以前,最晚到圣诞节以前。在英国对判定谁是敌人还有不同的看法,认为德国皇帝和普鲁士军事独裁者是敌人,德国人民不是敌人。坐船到 汉堡 来回,8月8日旅行社的票价还是45先令,几天后报纸上还在为1915年德累斯顿之夏音乐会做广告呢。
然而,几个月后,即1914年底,黑色和白色成了时尚的流行色,人民的意志占了上风,但报纸上的基调是打仗;怀疑之色——不显眼的灰色已经没有位置。令人费解的是,在英国,有的爱国者除掉了他们所养的猎獾狗,因为猎獾狗是德国品种;在德国,培养精英们的高贵女儿的教育机构,即按照英国的好传统培养“英国小姐”的机构,必须将名字改掉。
所有国家的民族主义者都为自己的民族欢呼。正在开始的民主时代被逼得无路可走,在重要的西欧国家,尽管自由党派和社会民主党派在议会中占大多数(在德国,德国社会民主党的席位远远多于其他政党;在英国,工党和自由党处于执政位置;在法国是社会主义党人掌握政权),然而,当战争爆发时,他们的理想破灭了。
德国人的形象——欧洲蛮子,这该由他们自己负责,许多看法每天都在证明这一点。德国的将军、实业家、政治家、出版家,他们的统治者更不用说了,他们以优越者自居,用强有力的口号“德意志高于一切,高于世上的一切”凌驾于别国之上。皇帝用来号召“德国人民”去发动战争的语言是当时典型的德意志时代精神:“战争势在必行,敌人在和平时期袭击我们,所以我发出号召!拿起武器!任何动摇、任何犹豫都是对祖国的背叛。事关我们父辈创立的帝国的存亡,事关德意志政权和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存亡。我们要抵抗,直至人和马匹只剩最后一口气。我们会经得住这场战争的考验,哪怕面对全世界的敌人。德国从来没有被战胜过,只要团结一致,和上帝一起前进。上帝曾和我们的父辈们在一起,上帝也将和我们在一起。”用行动开始,不考虑后果,这是典型的日耳曼本性。这种本性只怕上帝。根据这种本性,世界应该按德意志精神发展才健康。皇帝的口号在30年以后还可以这么写,用这种腔调,用这种语言,在另外一个帝国,有一个人签字,他现在正兴高采烈地学着这一号召:他就是阿道夫·希特勒。
“只有像1914年的德国军队那样的军队,才能单独跟别的军队作战。”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的御林军步兵团的编年史家大声说,“在军队里,每个人都通过经常骂人的普鲁士军国主义的严格教育和训练,而成为没有缺陷的守纪律的德国士兵。像1914年的德军那样的团结一致的、德国人民和祖国的军队,在世界上还没有过。”而这样的咆哮,确实不是独一无二的。
在德意志帝国有一首所谓的《仇恨英国歌》,它充分体现了德意志式的狂妄自大,成了街头的流行小调。此歌为某一个名叫恩斯特·利绍尔的德国人所作,作为德国声嘶力竭追求统治世界的有力证据、作为傲慢的普鲁士主义的证据。这首歌被译成英文,在许国英国报纸上刊登。一个未经训练的半吊子所写的语无伦次的东西,在正常的年代根本不值得一提。每个国家毕竟都有偏执者,何况那些年代已经是不正常的年代了。对英国的仇视竟然变成了一种民族诗,用来增强本民族的偏见,影响本国人民的情绪,毒害他们的思想。
这位笔杆子因此立了大功,甚至获得了一枚勋章。德国的小学生必须背诵他写的诗,威廉二世让人将这些诗印成传单、分发给部队:
我们只有唯一的敌人:
你们都知道,你们都知道,
他蜷缩在灰色的海峡对面,
满怀嫉妒、满怀愤恨、
充满阴险、充满狡诈,
一水之隔,水浓于血,
我们要控告。
我们发誓,共同发誓。
我们发誓,风吹不动。
我们向孩子和孩子的孩子发誓。
听着这句话,重复这句话,
它传遍整个欧洲:
不放弃仇恨,
我们只有一个恨,
我们一起爱,我们一起恨,
我们只有一个敌人:英国……
后来发表在《每日图报》上的反击诗体现出了激情——“打到德国人 / 全部打到……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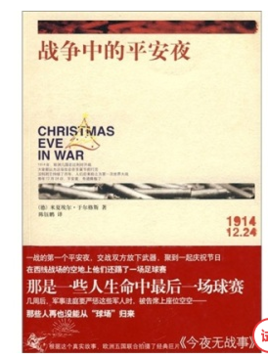 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德)
作者:米夏埃尔·于尔格斯 (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