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巴中尉并不是真的被吞噬了,但是“吞噬”却是第一个进
入他脑海里的字眼。
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巨大。
浩阔无云的天空,海浪翻涌一般的草原。除此之外,极目囚
望,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没有道路,没有车辆行驶过的轨迹,完
完全全的一片空旷原野。
他被震撼了,他的心脏以一种截然陌生的节奏跳动。
他坐在乎但开放的大草原上,让身体随着草原的律动而摇
动。虽然被震撼同化,但是他的血液并没有潮湃急流,很奇怪地,
他的血流平缓舒适,只感觉一阵阵的喜悦,他想要形容此刻的感
受,字句和片语不断地涌现脑海,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它们缀连
成有意义的同句。
终于,他开口吐出,三度出现脑海的句子:“这是一种信仰。“
虽然,这个句子似乎十分正确地描述他的感受,但是,他并不是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于虔敬庄严等宗教情感,他不知如何去
表达。
要是在平常,能够集中意识时,他会努力解释,但是现在,思
潮起伏,他一任幻想奔驰,而把这个艰难的解释掠过。
邓巴中尉已经堕人爱河之中,他的恋人是这片蛮荒的土地,
他爱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于这片土地,他的期望和对待爱人一
样:无私、无疑、虔敬以及永远。他的心灵受到鼓舞,心跳舒畅而
愉快,或许,这就是使一位英勇的骑兵中尉,联想宗教的缘故吧!
从眼角,他看到提马斯把头倾向一边,对着高及人腰的水牛
草吐口本,他已经吐了几千次,嘴角下淌着一条涎沫,一会儿之
后,才伸手将嘴角拭净,邓巴没有说话——当提马斯再次偏头去
对长草吐口水时,他只是往椅子内侧移动身体。
他不喜欢提马斯吐口水;就像不喜欢有人不停地在他面前
挖鼻孔一样,提马斯是个大老粗,除了吐口水外,他的狐臭,也令
邓巴中尉退避三舍。一整个早上,他们就这样并肩而坐,如果风
向好,他闻不到提马斯的味道,如果风向不对,提马斯的体臭便
像恶云一样笼罩他,邓巴虽然不到三十岁,但他见过不少死人,
提马斯的味道比任何死人都还要臭,他可以拖走或埋葬死者,但
却不能把活生生的马车夫埋葬。
在这种时候,风向错误时,他便会离开座位爬上篷车的货物
上,他可以在车床上待上好几个小时,偶尔也会跳人高高的长草
中,解开西斯可,上前侦察个一、两哩的路。
现在,他就回头往后看,西斯可在马车后缓缓跟着,它的鼻
子不时埋进食袋中,鹿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邓已对着他
的马微笑,只希望马和人类,有一样长的寿命,很幸运的,西斯可
大约还有十或十二年以上的时间可活,这匹马没有了,他还可以
买其他的马,但是西斯可是一生难见的好畜牲,一旦离去,便无
可取代。
像是回复邓已中尉的注视,西斯可突然从食料中抬起头,玻
璃色的眼睛,仿佛十分满意似地,又低下来,继续咬它的食料。
邓巴中尉坐直身体,伸手进军服里,拿出一张摺叠的纸张,
这是一纸军令,他的命令就写在上面,自从离开海斯营地以后,
他至少拿出来看了六、七次以上,愈看愈着急,心情从没有好过。
他的名字被拼错两次,满嘴酒气的少校,混混饨饨地签写派
令,抽子扫过还没有于的墨水,使整张军令污渍不堪,军令上没
有日期,所以邓巴只好在上路后自己写上,然而,他用铅笔所写
出来的工整字迹,和少校的潦草字迹,又未免太不符合了。
邓巴中尉对手中的纸叹了一口气,它不像军令,只像垃圾
纸。
想起少校,令他苦恼不堪,然而少校却是唯一有权安排他来
此地的人,他回想起初见少校的情景。
少校大概是喝过酒,他双眼布满血丝,一言不发地瞪了他许
久后,才开口说话。
“原来你是要去打红番的,嗯?“
邓巴从未见过印第安人,更别说和他们作战了。
“我不是,不过,长官,如果有需要,我是可以战斗的。”
“嗯。
邓巴中尉闭紧嘴,少校也不再说话。然后,少校拿出一技笔,
开始颤抖书写,喝了酒使他双手发抖不已,汗水自头皮间流下,
整张脸显得红光晶亮,写到一半时,他停下来,一口痰梗在喉间,
他大力咳出来,几乎把肺也咳出来。
邓巴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人,这名少校令人联想到病态不
健康,当他把痰吐在桌子边的一只脏桶子时,邓已中尉几乎也跟
着差点吐出来,他只希望少校尽快写好派令,让他离开这个令人
作呕的房间。
其实,邓巴中尉不知道他已经十分幸运了,因为在他踏人少
校办公室十分钟以前,少校才从醉酒之中清醒。他坐在书桌前
面,双子交握,搁在胸前,状至冷静,然而,他的心灵理智却一片
空白。他的人生是无权的人生,人们服从地送给他没有标记的廉
价物品,日子就是这样地过去,许多年来,他过着寂寞的单身生
活,一直和酒瓶奋斗挣扎,在酒精的借力下,他常有美妙幻想,或
许,在晚饭以前,他会被加冕为海斯营地之王。
他终于签好派令。
“我派你到席格威治营地,直接向卡吉尔上尉报到。”
邓巴中尉注视着污脏的派令。
“遵命,但是,我如何到达那里呢?”
“你认为我应该知道吗?”少校锐声反问。
“不,一点也不,我只是不知道路而已。”
少校把身体靠在椅背上,两只手在裤裆上掏掏扯扯,龌龊地
笑着。
“我今天心情好,特别恩准你的请求,出去外面找一个叫提
马斯的农夫,做为你的马车夫,你的任务是运送补给品,总共有
两辆车。”然后,他把派令递给邓巴中尉。“有我的印章,可以保证
你在这个地区方圆一百五十哩内的安全。”
邓已中尉急欲离开这名少校,他不再多问有关任务的内容,
只是行了一个礼,便离开办公室。他在门外找到提马斯,又牵来
自己的马,很快地在三十分钟内出发前往席格威治营地。
现在,他已离开海斯营地一百哩之外了,注视手中派令,他
告诉自己,事情不致太糟。
马车慢了下来,提马斯在草丛里,发现了奇怪东西。
邓巴也看到了,距离他们不到二十尺的地方,有一堆白白的
东西藏在草丛里,这两个人一起跳下来。
原来是一具人体骷髅,看来已死多时,骨头精白耀眼,头颅
注视着天空。
他是被人用箭射死的,许多箭齐插在胸腔上,而青草则从下
面长出来,这种情形,使得尸骨宛如一块绿色的针垫,而上面的
箭,就像无数的针。
邓巴中尉拔出其中一支,轻轻拗弯它。
当他的手指在箭干上移动时,提马斯在他肩上哈哈大笑。
“这家伙死得没人知晓,家里或许还在怪他不写信,没音没
讯的,哈!”
2
这一个晚上,大雨如注,但是倾盆大雨和夏日暴风雨一样,
来得快也会得急,草地上并不比其他的日子来得潮湿,所以,这
两个旅人,在篷车底下睡得鼾声大作。
.第四夭和前三夭一样,没有任何不同,至于第五天和第六
天,由于没有看到水牛,邓巴觉得帐然若失,他听说过大草原上
的野牛群,设想到却无缘一见,提马斯要他不必担心,他说兽群
有时候会同时消失,但总会回来,像蝗虫过境般地横扫过大草
原。
除了没有见到野兽外,他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印第安人,
提马斯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只是告诉他,如果见到一位印第
安人,很快地便会引来其他更多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没什么专
长,只会偷窃和行乞。
到了第六天,邓已已不再兴致勃勃听提马斯讲话了。
在最后几哩路时,他花了愈来愈多的时间,思考到达目的地
后的工作。
3
当卡吉尔上尉集中注意力时,他的眼睛全往上吊,并且感受
口腔的内缘,现在,他就在这种感觉之中,不过,现实很快粉碎他
的感觉,他对自己皱眉。
该死,又失神迷惘了。
他抬起眼珠子注视着一扇墙面,然后再环视这间潮湿阴晦
的营房,无啥可看,这个房间宛如牢房。
营房?他自我讥讽,该死的营房!
这个名词已经被使用了一个月以上,包括他自己,都毫不羞
耻地使用它,他对部下宣布这问简陋的小房间是营房,部下也这
样回复它,不当的形容,并没有在同志中形成谈笑的话题,反而
成为真正的诅咒。
恶运来临了。
卡吉尔上尉的手从嘴边落下来,营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坐
在他妈的该死的暗影中,凝神倾听外面的动静。外面寂静无声,
入他脑海里的字眼。
周围的一切竟是如此巨大。
浩阔无云的天空,海浪翻涌一般的草原。除此之外,极目囚
望,看不到其他任何东西,没有道路,没有车辆行驶过的轨迹,完
完全全的一片空旷原野。
他被震撼了,他的心脏以一种截然陌生的节奏跳动。
他坐在乎但开放的大草原上,让身体随着草原的律动而摇
动。虽然被震撼同化,但是他的血液并没有潮湃急流,很奇怪地,
他的血流平缓舒适,只感觉一阵阵的喜悦,他想要形容此刻的感
受,字句和片语不断地涌现脑海,但是却没有办法,将它们缀连
成有意义的同句。
终于,他开口吐出,三度出现脑海的句子:“这是一种信仰。“
虽然,这个句子似乎十分正确地描述他的感受,但是,他并不是
一个有宗教信仰的人,对于虔敬庄严等宗教情感,他不知如何去
表达。
要是在平常,能够集中意识时,他会努力解释,但是现在,思
潮起伏,他一任幻想奔驰,而把这个艰难的解释掠过。
邓巴中尉已经堕人爱河之中,他的恋人是这片蛮荒的土地,
他爱这片土地上的一切,对于这片土地,他的期望和对待爱人一
样:无私、无疑、虔敬以及永远。他的心灵受到鼓舞,心跳舒畅而
愉快,或许,这就是使一位英勇的骑兵中尉,联想宗教的缘故吧!
从眼角,他看到提马斯把头倾向一边,对着高及人腰的水牛
草吐口本,他已经吐了几千次,嘴角下淌着一条涎沫,一会儿之
后,才伸手将嘴角拭净,邓巴没有说话——当提马斯再次偏头去
对长草吐口水时,他只是往椅子内侧移动身体。
他不喜欢提马斯吐口水;就像不喜欢有人不停地在他面前
挖鼻孔一样,提马斯是个大老粗,除了吐口水外,他的狐臭,也令
邓巴中尉退避三舍。一整个早上,他们就这样并肩而坐,如果风
向好,他闻不到提马斯的味道,如果风向不对,提马斯的体臭便
像恶云一样笼罩他,邓巴虽然不到三十岁,但他见过不少死人,
提马斯的味道比任何死人都还要臭,他可以拖走或埋葬死者,但
却不能把活生生的马车夫埋葬。
在这种时候,风向错误时,他便会离开座位爬上篷车的货物
上,他可以在车床上待上好几个小时,偶尔也会跳人高高的长草
中,解开西斯可,上前侦察个一、两哩的路。
现在,他就回头往后看,西斯可在马车后缓缓跟着,它的鼻
子不时埋进食袋中,鹿色的皮毛在阳光下闪闪发亮,邓已对着他
的马微笑,只希望马和人类,有一样长的寿命,很幸运的,西斯可
大约还有十或十二年以上的时间可活,这匹马没有了,他还可以
买其他的马,但是西斯可是一生难见的好畜牲,一旦离去,便无
可取代。
像是回复邓已中尉的注视,西斯可突然从食料中抬起头,玻
璃色的眼睛,仿佛十分满意似地,又低下来,继续咬它的食料。
邓巴中尉坐直身体,伸手进军服里,拿出一张摺叠的纸张,
这是一纸军令,他的命令就写在上面,自从离开海斯营地以后,
他至少拿出来看了六、七次以上,愈看愈着急,心情从没有好过。
他的名字被拼错两次,满嘴酒气的少校,混混饨饨地签写派
令,抽子扫过还没有于的墨水,使整张军令污渍不堪,军令上没
有日期,所以邓巴只好在上路后自己写上,然而,他用铅笔所写
出来的工整字迹,和少校的潦草字迹,又未免太不符合了。
邓巴中尉对手中的纸叹了一口气,它不像军令,只像垃圾
纸。
想起少校,令他苦恼不堪,然而少校却是唯一有权安排他来
此地的人,他回想起初见少校的情景。
少校大概是喝过酒,他双眼布满血丝,一言不发地瞪了他许
久后,才开口说话。
“原来你是要去打红番的,嗯?“
邓巴从未见过印第安人,更别说和他们作战了。
“我不是,不过,长官,如果有需要,我是可以战斗的。”
“嗯。
邓巴中尉闭紧嘴,少校也不再说话。然后,少校拿出一技笔,
开始颤抖书写,喝了酒使他双手发抖不已,汗水自头皮间流下,
整张脸显得红光晶亮,写到一半时,他停下来,一口痰梗在喉间,
他大力咳出来,几乎把肺也咳出来。
邓巴没想到会碰到这样的人,这名少校令人联想到病态不
健康,当他把痰吐在桌子边的一只脏桶子时,邓已中尉几乎也跟
着差点吐出来,他只希望少校尽快写好派令,让他离开这个令人
作呕的房间。
其实,邓巴中尉不知道他已经十分幸运了,因为在他踏人少
校办公室十分钟以前,少校才从醉酒之中清醒。他坐在书桌前
面,双子交握,搁在胸前,状至冷静,然而,他的心灵理智却一片
空白。他的人生是无权的人生,人们服从地送给他没有标记的廉
价物品,日子就是这样地过去,许多年来,他过着寂寞的单身生
活,一直和酒瓶奋斗挣扎,在酒精的借力下,他常有美妙幻想,或
许,在晚饭以前,他会被加冕为海斯营地之王。
他终于签好派令。
“我派你到席格威治营地,直接向卡吉尔上尉报到。”
邓巴中尉注视着污脏的派令。
“遵命,但是,我如何到达那里呢?”
“你认为我应该知道吗?”少校锐声反问。
“不,一点也不,我只是不知道路而已。”
少校把身体靠在椅背上,两只手在裤裆上掏掏扯扯,龌龊地
笑着。
“我今天心情好,特别恩准你的请求,出去外面找一个叫提
马斯的农夫,做为你的马车夫,你的任务是运送补给品,总共有
两辆车。”然后,他把派令递给邓巴中尉。“有我的印章,可以保证
你在这个地区方圆一百五十哩内的安全。”
邓已中尉急欲离开这名少校,他不再多问有关任务的内容,
只是行了一个礼,便离开办公室。他在门外找到提马斯,又牵来
自己的马,很快地在三十分钟内出发前往席格威治营地。
现在,他已离开海斯营地一百哩之外了,注视手中派令,他
告诉自己,事情不致太糟。
马车慢了下来,提马斯在草丛里,发现了奇怪东西。
邓巴也看到了,距离他们不到二十尺的地方,有一堆白白的
东西藏在草丛里,这两个人一起跳下来。
原来是一具人体骷髅,看来已死多时,骨头精白耀眼,头颅
注视着天空。
他是被人用箭射死的,许多箭齐插在胸腔上,而青草则从下
面长出来,这种情形,使得尸骨宛如一块绿色的针垫,而上面的
箭,就像无数的针。
邓巴中尉拔出其中一支,轻轻拗弯它。
当他的手指在箭干上移动时,提马斯在他肩上哈哈大笑。
“这家伙死得没人知晓,家里或许还在怪他不写信,没音没
讯的,哈!”
2
这一个晚上,大雨如注,但是倾盆大雨和夏日暴风雨一样,
来得快也会得急,草地上并不比其他的日子来得潮湿,所以,这
两个旅人,在篷车底下睡得鼾声大作。
.第四夭和前三夭一样,没有任何不同,至于第五天和第六
天,由于没有看到水牛,邓巴觉得帐然若失,他听说过大草原上
的野牛群,设想到却无缘一见,提马斯要他不必担心,他说兽群
有时候会同时消失,但总会回来,像蝗虫过境般地横扫过大草
原。
除了没有见到野兽外,他们也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印第安人,
提马斯没有向他解释为什么,他只是告诉他,如果见到一位印第
安人,很快地便会引来其他更多的印第安人,印第安人没什么专
长,只会偷窃和行乞。
到了第六天,邓已已不再兴致勃勃听提马斯讲话了。
在最后几哩路时,他花了愈来愈多的时间,思考到达目的地
后的工作。
3
当卡吉尔上尉集中注意力时,他的眼睛全往上吊,并且感受
口腔的内缘,现在,他就在这种感觉之中,不过,现实很快粉碎他
的感觉,他对自己皱眉。
该死,又失神迷惘了。
他抬起眼珠子注视着一扇墙面,然后再环视这间潮湿阴晦
的营房,无啥可看,这个房间宛如牢房。
营房?他自我讥讽,该死的营房!
这个名词已经被使用了一个月以上,包括他自己,都毫不羞
耻地使用它,他对部下宣布这问简陋的小房间是营房,部下也这
样回复它,不当的形容,并没有在同志中形成谈笑的话题,反而
成为真正的诅咒。
恶运来临了。
卡吉尔上尉的手从嘴边落下来,营房里只有他一个人,他坐
在他妈的该死的暗影中,凝神倾听外面的动静。外面寂静无声,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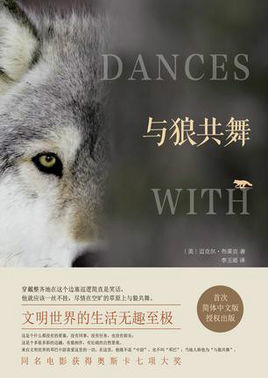 作者:迈克尔·布莱克 (美)
作者:迈克尔·布莱克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