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司声称要像"调教母猪"那样对待我们,一切就像我读过的书中描写的那样,但是我故意不去想那些教官的、甚至是最残酷的教官的名字。要学会含而不露的诀窍,要学会默默无声地顺从。有一次,我假装有黄疸——我把沙丁鱼罐头里的油加热喝了,后来又说得了新兵营地流行的疖病,从而逃脱了训练。不过,医务室所在的棚屋始终人满为患,只能供你短时避难,过后你还得去受折磨。
我们的教官从年龄来看都还算年轻,但上前线一两年就僵化成了未老先衰的玩世不恭者。他们是小队副级别,曾获得肉搏奖章和"冻肉勋章",现在打算把自己在库班河桥头堡和库尔斯克坦克战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时而严肃得可怕,时而无情地挖苦,时而又由着性子胡来。他们或是大声嚷,或是低声说,嘴里的传统行话劈头盖脸朝我们涌来。要论刁难人的手段,他们更是一个比一个会动脑筋,其中有些手段是新发明,有些则是从有军队的那会儿起就有了。
许多手段我都忘了。只有他们逼学生就范的一种手段,依然更像个笑话段子似的储存在我的记忆里,尽管我不是很有把握,当时被刁难者的反应只是想要报复而已,还是我确实报复了,而且如同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不管怎么说,这段故事的高潮还是够精彩的。
拂晓时,我看见自己在一片积着深深的雪,但还是像夜里那样黑咕隆咚的树林里摸索着前行,身上一左一右背着铁皮壶。去时一路小跑,回时慢条斯理。一座宫殿般的庄园藏在树林深处,不过窗口的灯光暴露了它的所在。我估计庄园里住着高官,有一次我似乎听见从那里飘来的音乐声。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在演奏海顿或者莫扎特的作品。不过,这和我在万籁俱寂时发生的故事毫不相干。
几天来,我一直遵命为小队副们和小队长准备早餐的饮料,也就是特意为他们去弄两壶咖啡。咖啡必须是热的,而且要不时加热供他们喝一整天。树林后的炊事棚里有咖啡。连我们这些新兵都能喝到那里沏好送来的麦芽茶或大麦茶,听人私下传说,这些代替咖啡的茶里放了抑制肉欲的苏打。我为养尊处优的小队长和六个小队副送来而且必须尽量保温的东西,却可能是用咖啡豆做出来的美味。至少壶里的香味闻起来像是真咖啡。
一个来回跑下来,我的早餐时间就只剩一半了。在余下的几分钟里,我还要把粗布军服上昨天溅上的泥浆结成的硬块拍打、刷洗干净,所以早点名时我经常迟到,迟到就要受罚:背起行军包,扎上防毒面具,在一块高低不平的地里上上下下不停地跑,靴底的泥土弄也弄不掉。这种折磨给戴着防毒面具的新兵带来的是仇恨,终身的仇恨。
不难想象,当时防毒面具的圆镜片上蒙着一层雾气,我戴着它一边哭号,一边制订了复仇计划,而且反复考虑了每个细节。
在从炊事棚回来的路上,我停下脚步,以银装素裹的冷杉树为掩护。我能看见远处庄园闪闪烁烁,庄园里的人却发现不了我。万籁俱寂,只能听见我的呼吸声。
现在我把壶里的咖啡倒了些在雪地上,倒了两指宽的样子。然后把壶放在地上,往里面撒尿,这壶里撒一点,那壶里撒一点,两只壶又都满了。还有些富余,就撒在两棵树之间,可以想象,雪地上顿时泛黄了。
更妙的是这会儿又下起了雪,掩盖了我的痕迹。在这寒风刺骨的冬天,我却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一种与幸福感相去不远的东西。
我们的教官从年龄来看都还算年轻,但上前线一两年就僵化成了未老先衰的玩世不恭者。他们是小队副级别,曾获得肉搏奖章和"冻肉勋章",现在打算把自己在库班河桥头堡和库尔斯克坦克战中积累的经验传授给我们,时而严肃得可怕,时而无情地挖苦,时而又由着性子胡来。他们或是大声嚷,或是低声说,嘴里的传统行话劈头盖脸朝我们涌来。要论刁难人的手段,他们更是一个比一个会动脑筋,其中有些手段是新发明,有些则是从有军队的那会儿起就有了。
许多手段我都忘了。只有他们逼学生就范的一种手段,依然更像个笑话段子似的储存在我的记忆里,尽管我不是很有把握,当时被刁难者的反应只是想要报复而已,还是我确实报复了,而且如同一段可以娓娓道来的故事?不管怎么说,这段故事的高潮还是够精彩的。
拂晓时,我看见自己在一片积着深深的雪,但还是像夜里那样黑咕隆咚的树林里摸索着前行,身上一左一右背着铁皮壶。去时一路小跑,回时慢条斯理。一座宫殿般的庄园藏在树林深处,不过窗口的灯光暴露了它的所在。我估计庄园里住着高官,有一次我似乎听见从那里飘来的音乐声。今天回想起来,当时应该是一支弦乐四重奏乐队在演奏海顿或者莫扎特的作品。不过,这和我在万籁俱寂时发生的故事毫不相干。
几天来,我一直遵命为小队副们和小队长准备早餐的饮料,也就是特意为他们去弄两壶咖啡。咖啡必须是热的,而且要不时加热供他们喝一整天。树林后的炊事棚里有咖啡。连我们这些新兵都能喝到那里沏好送来的麦芽茶或大麦茶,听人私下传说,这些代替咖啡的茶里放了抑制肉欲的苏打。我为养尊处优的小队长和六个小队副送来而且必须尽量保温的东西,却可能是用咖啡豆做出来的美味。至少壶里的香味闻起来像是真咖啡。
一个来回跑下来,我的早餐时间就只剩一半了。在余下的几分钟里,我还要把粗布军服上昨天溅上的泥浆结成的硬块拍打、刷洗干净,所以早点名时我经常迟到,迟到就要受罚:背起行军包,扎上防毒面具,在一块高低不平的地里上上下下不停地跑,靴底的泥土弄也弄不掉。这种折磨给戴着防毒面具的新兵带来的是仇恨,终身的仇恨。
不难想象,当时防毒面具的圆镜片上蒙着一层雾气,我戴着它一边哭号,一边制订了复仇计划,而且反复考虑了每个细节。
在从炊事棚回来的路上,我停下脚步,以银装素裹的冷杉树为掩护。我能看见远处庄园闪闪烁烁,庄园里的人却发现不了我。万籁俱寂,只能听见我的呼吸声。
现在我把壶里的咖啡倒了些在雪地上,倒了两指宽的样子。然后把壶放在地上,往里面撒尿,这壶里撒一点,那壶里撒一点,两只壶又都满了。还有些富余,就撒在两棵树之间,可以想象,雪地上顿时泛黄了。
更妙的是这会儿又下起了雪,掩盖了我的痕迹。在这寒风刺骨的冬天,我却热血沸腾,浑身洋溢着一种与幸福感相去不远的东西。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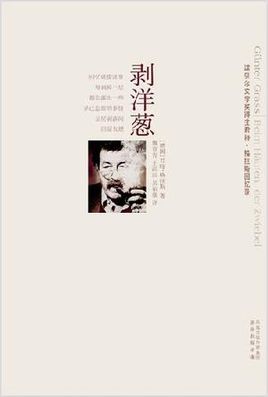 作者:君特·格拉斯(德)
作者:君特·格拉斯(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