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下飞机,K就嚷着头晕,约莫是高原反应的作用。你拿出一剂增血红素的药锭给他服用,自己也吞下了一颗以备心安。之后,你们在冷清的航厦前,等待着发往丽江大研镇古城的最末一班公车。
子夜时分,雨依旧下着。入秋的微雨,使丽江一雨成冬。你和K各自背着行囊,还合力扛起一辆装箱的自行车。K没走几步路,便央求停下来休息,其实你也喘着,只是努力地装作镇定把气虚压下而已,你不想在首站两千四百米的地方就暴露出自己孱弱的窘状。
暗黑中,撑伞的妇人远远走来,趁机问你们:“要住宿吗?”K湿着发额无语地望着你。你有点烦躁地回答,不用,已订好房了,急着想摆脱她。她仍继续争取,连忙叫唤杵在对街吸烟的丈夫:“喂!来帮这俩小伙子扛箱啊!”不管你如何推托,他们就是直嚷嚷说:“看看就好,看看,不满意,包再帮你换到你指定的地方。”K放下他垂软的双手,将箱子一端交给那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你也不好再坚持什么了。
你一向认为在街头上拦街叫宿的,十之八九肯定是些投机的店家。跨进三坊一照壁家庭式的小客栈,男主人不先领你们去看房,你们卸了行囊,他便递烟,倒茶,唤着他的妻去热几个东北大肉包。四颗蓬松白软的大包子端上,你勉强噙住口水问,这房钱儿怎么算?女主人缓声道:“放心吃吧!不收钱的。”该算就算吧,你说,怕他们把额外的服务加码在房价上。男主人吐着烟气,露出一口黑牙:“小伙子,给你图个最省的,标间一人二十五元。二十五行吗?”价钱尚可,且热包子咬下去嘴软,你开不了口拒绝和杀价。
听说今年滇藏沿线一带,雨季特别的漫长。
隔床的K已经睡去,你竟辗转翻覆难以成眠,便倚着枕头坐起,回想一天的由始至终,从台湾,飞香港,入深圳,转机丽江。你拿出簿本,想着想着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你必须设想一个对象,然后才能开始说话。
你开始专注地竖起听觉神经,去聆听那细雨淅沥的脚步匍匐在窗外的石阶,檐角和风铃,而后弹跃至窗棂的眼线上,秘密窥探着;还有些雨水自屋檐的承汇聚引落,轻盈地歌唱,像是舒伯特的音乐,舒缓,易感,富有节制的想象。
三天来,你和K就住在这幢名为“龙Ⅹ”的客栈,纳西式仿古建筑,楼高两层,全为木造,一共六个房间。老板夫妇俩来自东北,男主人说,沿房外这条街的客栈,几乎都是他们东北老乡所开,且大家不约而同都取了 “龙Ⅹ”什么的店名。因而古城里某一条青石板街道,真有那么一条东北的龙脉蜿蜒盘踞。
与他们混熟了,你便叫起满面皱纹的当家——大爷,他老婆年轻许多,你却不论辈分地唤她姨。你依然被称台湾小伙子。偶尔住客来,大爷总将客人拉到你的面前,看你这准备独自骑单车进西藏的台湾小伙子。你注意到店里唯一的服务员小妹,是因为听到姨每每那番严声酷吏般吼她,但转身一见你就变成慈和的妇人了。你不禁有点同情这十六岁的长工小妹,每月领三百五十元——所有杂务必须一肩担下,她住在大门旁柜台后的一间只容得一人钻进的橱柜里。二十四小时的守门员。古镇的宿店,大多是这等自乡间来的稚嫩小工,刻苦且宿命。小妹最常对你说:“怪奇怪的,从来没听过有人会说那么多的‘谢谢’。”笑得眼睛总小得眯成一线。
柔软的时光(2)
很喜欢丽江古城的怀旧情调,这是他第一次自助旅行。你与K相识十多年,他不久前才卸下替代役职务,学校老师们还为此特别颁发匾额褒扬他的认真付出。你筹备流浪计划时,K信誓旦旦说要跟上你一段路,学习如何过耐苦冒险的日子,以备日后出社会之用。K的出现,分担了你超重的飞航行李,你承诺将带他在云南境内见识些不同的风景。
但三天来,你几乎只是走路,迷路,不停地穿梭在市集人群中,对琳琅满目的商贩,美食,酒吧,收门票的景点,全不感兴趣,而偏爱停伫某个偏僻的巷弄或荒芜的废墟,不然就回到旅栈的庭院,看书,发呆,抽烟,仰望着檐角,沉湎于自我的情绪里。有时K会独自外出游荡,但都撑得不久,每当你看见他返回旅栈时,都觉得他有种莫名的寂寥和惆怅。
你们总一道吃饭,可不在古城里,常得绕上大半个小时出城,只为了便宜半价的饮食。丽江古城,隔着一条外环柏油马路,与新城相对。新城全为一派现代的水泥建物,其实古城也并不算古,一九九六年丽江地区,遭遇里氏七级大地震,古城内建筑泰半倾颓,随后九七年,联合国册封它为 “世界文化遗产”,便造就这座古城两三年内以惊人的速度重建起来,仿佛恢复了它在旧时茶马古道上的荣光。虽然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发展观光产业,可又有什么能置喙的余地呢。古城处处仿古,大多观光化了,你也仍是喜欢它,不过只限定清晨与深夜时分,散步于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能听见细密的渠水流经的时候。散去人潮的大研古城,似乎就真的变老了,老在无人的拥挤相伴,晚年的凄清。
古城的水泉,源自玉龙雪山上。你决定带K去虎跳峡。
那里据说是飞鸟不敢回望的地方。金沙江居中,自西而东,忍痛下切,切分了南面丽江县区五五九六米的屏障——玉龙雪山,与北面中甸县区五三八六米的哈巴雪山。
在桥头下车,你们马上遭到当地向导们包围。你自顾地走,几位向导紧追在后威胁,没他们带领你们肯定会迷失的。入口处,没人管收门票,只有看似管理员的人挡在路中,说里头封闭了,因为不久前落石才砸死一整车的游客,现在峡谷内在整治,如果你们执意要入,安危就自行负责。你硬着头皮,略过K脸上的难色,决定闯闯。在沿着江岸路线与岔去山上的路口前,你询问K想选择哪条路,故作分析说,低路好走三十多公里,但有落石可能,而高路得翻山越岭死命地爬。他选择低路,你倒也松了一口气。于是你们顺着低路东行,又有向导骑马追来嘲讽你们绝对到不了的,说得K忧心忡忡,你的士气似乎也有些动摇了。
顶着烈阳天,天空蛮横地养着几片云朵,然后渐渐的,两岸山势逐步朝中线靠拢,举头仰看几可覆额。k说他累了想吃些东西,你看表,才步行两个小时,不知道距离上虎跳还有多远,你有点着急,不过仍停下来休息。你在一旁拿起相机,又蹲又趴想试着拍摄南面十几座绵延的雪峰,奈何镜头窄得连座山都容纳不下,遂放弃了,你只能干巴巴地用心看。
路途中,你对K说:“我们不能觉得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这条路还远着呢,一切都得省一点。”他低头默默地听,额上淌着汗水,没有回应。中午你们坐在路旁的大石上,你拆开一包四块装的压缩干粮,同K对分。你吃完,不见K有何动静。他说他吃不下。你知道他在生你的闷气,你还是恼怒严厉地对他教训:“不吃等会还有体力走吗,吃不下也得勉强吃,你以为这是哪里,哪由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K脸一沉,不情愿地吃了,仿佛将哭的样子。你自觉说的话有些过分,却拉不下脸来对他道歉。
柔软的时光(3)
走至上虎跳,你和K便和好如初了,你为他拍照纪念,他也为你留下记录。再继续往前几里,几个当地的民众稀疏地散在路边,前头的路上满布着沙砾碎石堆起足有腰身那么高,远远望去,间或还有拒栏和施工人员的身影。
你探视周围情况,达达达~,钢钻钻凿岩壁的声音从望不见的左上方传来,随后沙尘石头滚滚而落,掀起一片烟硝。刺耳的声音总算停顿了好一会,你便看到提着菜篮的妇女、扛着米袋的男人越过警戒线,你马上唤着K一起向前冲。没想到只落后几步的你们被戴帽的施工人员拦下,你匆忙问工人,为什么他们能过,你们不行,工人竟然回答:“他们是当地人啊,你们是游客。他们砸死自个儿负责,不用赔的。如果让你们过,万一出事儿,我们没有法律责任也有道义责任啊。”你愤愤不平地退出警戒区外。
“那别过去了吧!”K说。你见仍有几个当地人悠闲地坐在路旁,就说再等等。你与一个蓄着日本胡的青年,蹲在地上聊了起来。K始终沉默不语。又是一长串达达达~,夹杂爆破的声音。而这一等竟等了三个小时。青年说:“没一会儿,他们肯定要停住,放人过去的,不然我们怎回家。你们待会夹在这些人群中就没事的。”你告诉K这好消息,他面无表情,你想,他又生闷气了。
陆续加上再来的居民约莫二十多个,全聚集在警戒线前,你们这次紧紧贴住人群。你让K在身前,自己垫后,紧张地捻着他的衣脚。终于等到前方远远的工人大喊:“行了”,挥着手,大伙便像逃命般的拔腿狂奔。你眼见自己落到最后了,爬上石砾堆,踩在凹凸的岩块上,居然禁不住就 “哇~妈啊~干!”的,一路发狂似的喊着跑。整路上只有你一人叫喊。短短几十秒,你感到胸口强烈被血液极度挤缩。跑出乱石堆外,你腿软得跪在地上直说好险好险啊,K弯着腰喘气吁吁,转头面色惨白,脸扭拧着啐一口口水:“尬你娘勒,这简直玩命嘛!”
之后蓄胡的青年领着你们到了一间盖在崖边的瓦屋。青年说瓦屋主人是他好友,他们准备在这翻挖一条下到江畔“满天星”的路,这样他们便可学中虎跳那儿民宿主人一样,收下游客的“买路钱”。青年把满天星形容得像是虎跳峡里最凶险景观最好的一段地带,仿佛无人知晓的处女地。他问你们想去看看吗?请瓦屋的十岁小主人带你们去。
你们沿屋旁的灌丛蜿蜒而下,没有路径,只有方向,时不时得拨开山壁岩缝间刺人的蒺藜与枝叶。K踩在湿滑的土石上,摔了好几回,你把登山杖借他支撑。总算下到岸边数层楼高的嶙峋叠垛的巨岩背上,黄褐的江水怒怒地流着,你问小男孩,这就是满天星吗?他点点头,还不曾听他说过一句话。原来满天星,只不过是急流涌动的江水遭遇乱石密布的河床,所激起的无数的漩涡和白沫的浪花,必须加诸点浪漫的想象才能组构出一幅跃动在浊黄黄水面上一闪一闪的星星风景。你有点被骗了的感觉。
从下往上爬,K竟又摔倒了几回,一次比一次严重,你虽替他惊心,但看他摔得夸张的模样,还是忍不住捧腹大笑。你们返回低路时,天已经暗了。青年从屋里出来探视,勾搭着你的肩细声:“这小孩父亲病了。他领你们去满天星,能不能给点儿意思意思。”青年没敢开口喊个数字,有点谍对谍的味道,你询问一旁的K,K说:“小孩这么辛苦就给二十吧,”你摇头,最后只决定付出十元。小男孩腼腆地笑了,倒是青年看来相当不满,他原本说要带你们去中虎跳的住宿处,显然因为如此,便站在门口邪邪地道: “那不送了,你们慢走喔。”而几里之内,峡谷除了此户人家外,再也没有照路的灯火了。
子夜时分,雨依旧下着。入秋的微雨,使丽江一雨成冬。你和K各自背着行囊,还合力扛起一辆装箱的自行车。K没走几步路,便央求停下来休息,其实你也喘着,只是努力地装作镇定把气虚压下而已,你不想在首站两千四百米的地方就暴露出自己孱弱的窘状。
暗黑中,撑伞的妇人远远走来,趁机问你们:“要住宿吗?”K湿着发额无语地望着你。你有点烦躁地回答,不用,已订好房了,急着想摆脱她。她仍继续争取,连忙叫唤杵在对街吸烟的丈夫:“喂!来帮这俩小伙子扛箱啊!”不管你如何推托,他们就是直嚷嚷说:“看看就好,看看,不满意,包再帮你换到你指定的地方。”K放下他垂软的双手,将箱子一端交给那操着东北口音的男人。你也不好再坚持什么了。
你一向认为在街头上拦街叫宿的,十之八九肯定是些投机的店家。跨进三坊一照壁家庭式的小客栈,男主人不先领你们去看房,你们卸了行囊,他便递烟,倒茶,唤着他的妻去热几个东北大肉包。四颗蓬松白软的大包子端上,你勉强噙住口水问,这房钱儿怎么算?女主人缓声道:“放心吃吧!不收钱的。”该算就算吧,你说,怕他们把额外的服务加码在房价上。男主人吐着烟气,露出一口黑牙:“小伙子,给你图个最省的,标间一人二十五元。二十五行吗?”价钱尚可,且热包子咬下去嘴软,你开不了口拒绝和杀价。
听说今年滇藏沿线一带,雨季特别的漫长。
隔床的K已经睡去,你竟辗转翻覆难以成眠,便倚着枕头坐起,回想一天的由始至终,从台湾,飞香港,入深圳,转机丽江。你拿出簿本,想着想着却什么也写不出来。你必须设想一个对象,然后才能开始说话。
你开始专注地竖起听觉神经,去聆听那细雨淅沥的脚步匍匐在窗外的石阶,檐角和风铃,而后弹跃至窗棂的眼线上,秘密窥探着;还有些雨水自屋檐的承汇聚引落,轻盈地歌唱,像是舒伯特的音乐,舒缓,易感,富有节制的想象。
三天来,你和K就住在这幢名为“龙Ⅹ”的客栈,纳西式仿古建筑,楼高两层,全为木造,一共六个房间。老板夫妇俩来自东北,男主人说,沿房外这条街的客栈,几乎都是他们东北老乡所开,且大家不约而同都取了 “龙Ⅹ”什么的店名。因而古城里某一条青石板街道,真有那么一条东北的龙脉蜿蜒盘踞。
与他们混熟了,你便叫起满面皱纹的当家——大爷,他老婆年轻许多,你却不论辈分地唤她姨。你依然被称台湾小伙子。偶尔住客来,大爷总将客人拉到你的面前,看你这准备独自骑单车进西藏的台湾小伙子。你注意到店里唯一的服务员小妹,是因为听到姨每每那番严声酷吏般吼她,但转身一见你就变成慈和的妇人了。你不禁有点同情这十六岁的长工小妹,每月领三百五十元——所有杂务必须一肩担下,她住在大门旁柜台后的一间只容得一人钻进的橱柜里。二十四小时的守门员。古镇的宿店,大多是这等自乡间来的稚嫩小工,刻苦且宿命。小妹最常对你说:“怪奇怪的,从来没听过有人会说那么多的‘谢谢’。”笑得眼睛总小得眯成一线。
柔软的时光(2)
很喜欢丽江古城的怀旧情调,这是他第一次自助旅行。你与K相识十多年,他不久前才卸下替代役职务,学校老师们还为此特别颁发匾额褒扬他的认真付出。你筹备流浪计划时,K信誓旦旦说要跟上你一段路,学习如何过耐苦冒险的日子,以备日后出社会之用。K的出现,分担了你超重的飞航行李,你承诺将带他在云南境内见识些不同的风景。
但三天来,你几乎只是走路,迷路,不停地穿梭在市集人群中,对琳琅满目的商贩,美食,酒吧,收门票的景点,全不感兴趣,而偏爱停伫某个偏僻的巷弄或荒芜的废墟,不然就回到旅栈的庭院,看书,发呆,抽烟,仰望着檐角,沉湎于自我的情绪里。有时K会独自外出游荡,但都撑得不久,每当你看见他返回旅栈时,都觉得他有种莫名的寂寥和惆怅。
你们总一道吃饭,可不在古城里,常得绕上大半个小时出城,只为了便宜半价的饮食。丽江古城,隔着一条外环柏油马路,与新城相对。新城全为一派现代的水泥建物,其实古城也并不算古,一九九六年丽江地区,遭遇里氏七级大地震,古城内建筑泰半倾颓,随后九七年,联合国册封它为 “世界文化遗产”,便造就这座古城两三年内以惊人的速度重建起来,仿佛恢复了它在旧时茶马古道上的荣光。虽然这一切似乎都是为了发展观光产业,可又有什么能置喙的余地呢。古城处处仿古,大多观光化了,你也仍是喜欢它,不过只限定清晨与深夜时分,散步于湿漉漉的青石板路上,能听见细密的渠水流经的时候。散去人潮的大研古城,似乎就真的变老了,老在无人的拥挤相伴,晚年的凄清。
古城的水泉,源自玉龙雪山上。你决定带K去虎跳峡。
那里据说是飞鸟不敢回望的地方。金沙江居中,自西而东,忍痛下切,切分了南面丽江县区五五九六米的屏障——玉龙雪山,与北面中甸县区五三八六米的哈巴雪山。
在桥头下车,你们马上遭到当地向导们包围。你自顾地走,几位向导紧追在后威胁,没他们带领你们肯定会迷失的。入口处,没人管收门票,只有看似管理员的人挡在路中,说里头封闭了,因为不久前落石才砸死一整车的游客,现在峡谷内在整治,如果你们执意要入,安危就自行负责。你硬着头皮,略过K脸上的难色,决定闯闯。在沿着江岸路线与岔去山上的路口前,你询问K想选择哪条路,故作分析说,低路好走三十多公里,但有落石可能,而高路得翻山越岭死命地爬。他选择低路,你倒也松了一口气。于是你们顺着低路东行,又有向导骑马追来嘲讽你们绝对到不了的,说得K忧心忡忡,你的士气似乎也有些动摇了。
顶着烈阳天,天空蛮横地养着几片云朵,然后渐渐的,两岸山势逐步朝中线靠拢,举头仰看几可覆额。k说他累了想吃些东西,你看表,才步行两个小时,不知道距离上虎跳还有多远,你有点着急,不过仍停下来休息。你在一旁拿起相机,又蹲又趴想试着拍摄南面十几座绵延的雪峰,奈何镜头窄得连座山都容纳不下,遂放弃了,你只能干巴巴地用心看。
路途中,你对K说:“我们不能觉得累了就休息饿了就吃,这条路还远着呢,一切都得省一点。”他低头默默地听,额上淌着汗水,没有回应。中午你们坐在路旁的大石上,你拆开一包四块装的压缩干粮,同K对分。你吃完,不见K有何动静。他说他吃不下。你知道他在生你的闷气,你还是恼怒严厉地对他教训:“不吃等会还有体力走吗,吃不下也得勉强吃,你以为这是哪里,哪由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K脸一沉,不情愿地吃了,仿佛将哭的样子。你自觉说的话有些过分,却拉不下脸来对他道歉。
柔软的时光(3)
走至上虎跳,你和K便和好如初了,你为他拍照纪念,他也为你留下记录。再继续往前几里,几个当地的民众稀疏地散在路边,前头的路上满布着沙砾碎石堆起足有腰身那么高,远远望去,间或还有拒栏和施工人员的身影。
你探视周围情况,达达达~,钢钻钻凿岩壁的声音从望不见的左上方传来,随后沙尘石头滚滚而落,掀起一片烟硝。刺耳的声音总算停顿了好一会,你便看到提着菜篮的妇女、扛着米袋的男人越过警戒线,你马上唤着K一起向前冲。没想到只落后几步的你们被戴帽的施工人员拦下,你匆忙问工人,为什么他们能过,你们不行,工人竟然回答:“他们是当地人啊,你们是游客。他们砸死自个儿负责,不用赔的。如果让你们过,万一出事儿,我们没有法律责任也有道义责任啊。”你愤愤不平地退出警戒区外。
“那别过去了吧!”K说。你见仍有几个当地人悠闲地坐在路旁,就说再等等。你与一个蓄着日本胡的青年,蹲在地上聊了起来。K始终沉默不语。又是一长串达达达~,夹杂爆破的声音。而这一等竟等了三个小时。青年说:“没一会儿,他们肯定要停住,放人过去的,不然我们怎回家。你们待会夹在这些人群中就没事的。”你告诉K这好消息,他面无表情,你想,他又生闷气了。
陆续加上再来的居民约莫二十多个,全聚集在警戒线前,你们这次紧紧贴住人群。你让K在身前,自己垫后,紧张地捻着他的衣脚。终于等到前方远远的工人大喊:“行了”,挥着手,大伙便像逃命般的拔腿狂奔。你眼见自己落到最后了,爬上石砾堆,踩在凹凸的岩块上,居然禁不住就 “哇~妈啊~干!”的,一路发狂似的喊着跑。整路上只有你一人叫喊。短短几十秒,你感到胸口强烈被血液极度挤缩。跑出乱石堆外,你腿软得跪在地上直说好险好险啊,K弯着腰喘气吁吁,转头面色惨白,脸扭拧着啐一口口水:“尬你娘勒,这简直玩命嘛!”
之后蓄胡的青年领着你们到了一间盖在崖边的瓦屋。青年说瓦屋主人是他好友,他们准备在这翻挖一条下到江畔“满天星”的路,这样他们便可学中虎跳那儿民宿主人一样,收下游客的“买路钱”。青年把满天星形容得像是虎跳峡里最凶险景观最好的一段地带,仿佛无人知晓的处女地。他问你们想去看看吗?请瓦屋的十岁小主人带你们去。
你们沿屋旁的灌丛蜿蜒而下,没有路径,只有方向,时不时得拨开山壁岩缝间刺人的蒺藜与枝叶。K踩在湿滑的土石上,摔了好几回,你把登山杖借他支撑。总算下到岸边数层楼高的嶙峋叠垛的巨岩背上,黄褐的江水怒怒地流着,你问小男孩,这就是满天星吗?他点点头,还不曾听他说过一句话。原来满天星,只不过是急流涌动的江水遭遇乱石密布的河床,所激起的无数的漩涡和白沫的浪花,必须加诸点浪漫的想象才能组构出一幅跃动在浊黄黄水面上一闪一闪的星星风景。你有点被骗了的感觉。
从下往上爬,K竟又摔倒了几回,一次比一次严重,你虽替他惊心,但看他摔得夸张的模样,还是忍不住捧腹大笑。你们返回低路时,天已经暗了。青年从屋里出来探视,勾搭着你的肩细声:“这小孩父亲病了。他领你们去满天星,能不能给点儿意思意思。”青年没敢开口喊个数字,有点谍对谍的味道,你询问一旁的K,K说:“小孩这么辛苦就给二十吧,”你摇头,最后只决定付出十元。小男孩腼腆地笑了,倒是青年看来相当不满,他原本说要带你们去中虎跳的住宿处,显然因为如此,便站在门口邪邪地道: “那不送了,你们慢走喔。”而几里之内,峡谷除了此户人家外,再也没有照路的灯火了。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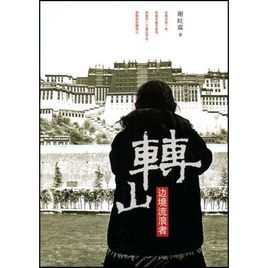 作者:谢旺霖(当代)
作者:谢旺霖(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