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有幸和一位被我称为G·7的侦探——下边您会看到我为什么称他为G·7——一起调查过几起案件。在讲述这些调查之前,我要说说我是如何结识这位警探的,而且对我来说,和他相识在很长一段时期也是一个谜。
一九二……年十月九日。
偶尔一次,大约是在清晨两点,我在蒙马特高地一家小酒馆和邻桌的一位聊了起来。他是一名外国人,我很难确定是哪国人,因为我觉得他说话带点英国口音,一会儿又觉得有点斯拉夫味,虽然英国口音和斯拉夫味道相差何止万里。
我们一起走出酒馆。头上的天空很美,既清冷又明朗。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一起溜达一段路。我们一同走到德洛海特街。可是我感觉太冷了,于是开始等出租车。车从身旁呼啸而过,无一辆是空的。走到圣乔治广场,一辆红色轿车,他等到的,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全身裹着裘皮的年轻女士从车内急速跳出来。她递给司机一张钞票,不等找钱便匆匆而去。
“您上这辆车吧!”我说。
“不!不行,您上吧!”
“我住得离这儿不远……”
“那又怎么样!还是您请吧……”我让步了。我向他伸出手去。虽然我们才刚刚认识。他伸给我的是左手。整整一个晚上,他的右手始终插在上衣兜里。我刚上车又想把他唤住,因为我突然发现遇上了一场悲剧,完全迷惑了。在我坠入的这个汽车深渊里,我碰到了什么东西!我用手摸了摸,发现是一个人的身躯。
司机已经将车门关上,车起动了,我没有想到叫司机立刻停车。待意识到此,为时已晚。我们沿着蒙马特郊区前行。我的酒馆伙伴以及年轻女子大概已经消失。我当时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这一意外事件使我感到燥热,我脸烧得通红,同时喉咙发紧,我身边的这个人已经从座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动不动。
路旁咖啡馆里的灯光现在照到他的身上,我发现这是一张年轻的面孔,头发红棕色、身着一套灰色西装。他的一只手上有血。我触摸了一下这个陌生人的肩头,我的手沾上了一种红色的、热乎乎的液体。我的嘴唇在颤抖,我犹豫不决。最后,我突然做出决定:“去我家!”
如果当初我没有看到那个年轻的、长得十分漂亮的女人从同一辆出租车里走出的话,我要司机去的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警察局,也可能是一家医院。但是,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事件,我也不愿意它是一个平常事件。
此人并没有死。我甚至怀疑他没有昏过去,他的呼吸是那么有力,脉膊跳动节奏是如此清晰。
司机去了。我把车中人背到走廊里。一刻钟之后这位陌生人已经躺在我的床上。我凝视着他那个小小的伤口,这伤口极有可能是用尖刀划的。“为女人用的武器所伤?……反正他还未苏醒过来,而且也需要治疗……”伤口不深。他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想大概是失血过多所致。
可是他确实流了很多血吗?他的衣服上可是一滴也没有啊,“甭管它了!应该请医生……”我出了门,跑到一个朋友家。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医科大学生,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一把将他从床上拽起来。
我们很快回到我的住处。我打开门。我说:“在床上……在左边……”我的双眼立刻睁得老大,因为,我的伤员,几乎可以说我的囚犯——因为我出去前已经把门锁上了——不见了。我查看房间。房间里乱成一团。所有的抽屉都大开着。我办公桌上的证件、材料给翻了个乱七八糟,捆好的一摞信上全是墨水。
我的朋友哆哆嗦嗦地微笑:“你家里是否放了很多钱?”我的朋友这样问。
“你什么意思?” 我生气了。我恼火了!我感到自己很可笑,想想这样保护一个陌生人,便感到自己更加荒唐,更加滑稽了,“他不是小偷,他什么也没有拿走。”
“你肯定吗?”
“非常肯定!你总不会说我连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都不清楚吧?东西全在……”
“哼!”
“哼什么?”
“没什么!我可以回去再睡我的觉了吧?不过,你是否先给我来杯烧酒喝。外边实在太冷,我是让你从床上拽起来……”我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狗熊,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间。
那么,我既然讲述这个故事,就一定要把它全部交待清楚。我的朋友刚刚离开,我后脚就出门了,我又回到圣乔治广场,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在那里找到那个女人的踪迹。这太愚蠢了。我明明看到她匆匆地走了。她并没有进入附近的任何一所房子,而是朝圣拉扎尔街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这儿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我烦躁不安,竟大声自言自语起来。直到清晨五时,我才回家睡到我那张我曾那么小心翼翼地将我的那位受伤人安顿躺下的床上,上午九点,我被看门人唤醒,她给我送来一封信。
我只瞥了一眼信封,决定再回床睡觉。但是,我发现信封上未贴邮票。信封内掉出的是一份正式公文,要我十点到位于索赛街的安全部。召见公文上注明我应去的办公室的门牌号码。我至少改变了十次主意,一会儿决定想去说明事实真相,马上又想编造一个神话故事,一会儿又决定改变某些细节。毫无疑问,我的表现幼稚得像个小孩。可是我又不愿承认这一点,哪怕是对自己都不肯承认。
一九二……年十月九日。
偶尔一次,大约是在清晨两点,我在蒙马特高地一家小酒馆和邻桌的一位聊了起来。他是一名外国人,我很难确定是哪国人,因为我觉得他说话带点英国口音,一会儿又觉得有点斯拉夫味,虽然英国口音和斯拉夫味道相差何止万里。
我们一起走出酒馆。头上的天空很美,既清冷又明朗。两个人不约而同地想一起溜达一段路。我们一同走到德洛海特街。可是我感觉太冷了,于是开始等出租车。车从身旁呼啸而过,无一辆是空的。走到圣乔治广场,一辆红色轿车,他等到的,在离我们几米远的地方停了下来,一个全身裹着裘皮的年轻女士从车内急速跳出来。她递给司机一张钞票,不等找钱便匆匆而去。
“您上这辆车吧!”我说。
“不!不行,您上吧!”
“我住得离这儿不远……”
“那又怎么样!还是您请吧……”我让步了。我向他伸出手去。虽然我们才刚刚认识。他伸给我的是左手。整整一个晚上,他的右手始终插在上衣兜里。我刚上车又想把他唤住,因为我突然发现遇上了一场悲剧,完全迷惑了。在我坠入的这个汽车深渊里,我碰到了什么东西!我用手摸了摸,发现是一个人的身躯。
司机已经将车门关上,车起动了,我没有想到叫司机立刻停车。待意识到此,为时已晚。我们沿着蒙马特郊区前行。我的酒馆伙伴以及年轻女子大概已经消失。我当时的感受真是无法形容,这一意外事件使我感到燥热,我脸烧得通红,同时喉咙发紧,我身边的这个人已经从座位上滑落下来,他一动不动。
路旁咖啡馆里的灯光现在照到他的身上,我发现这是一张年轻的面孔,头发红棕色、身着一套灰色西装。他的一只手上有血。我触摸了一下这个陌生人的肩头,我的手沾上了一种红色的、热乎乎的液体。我的嘴唇在颤抖,我犹豫不决。最后,我突然做出决定:“去我家!”
如果当初我没有看到那个年轻的、长得十分漂亮的女人从同一辆出租车里走出的话,我要司机去的很可能就是另一个地方,可能是一个警察局,也可能是一家医院。但是,我感到这不是一个一般的事件,我也不愿意它是一个平常事件。
此人并没有死。我甚至怀疑他没有昏过去,他的呼吸是那么有力,脉膊跳动节奏是如此清晰。
司机去了。我把车中人背到走廊里。一刻钟之后这位陌生人已经躺在我的床上。我凝视着他那个小小的伤口,这伤口极有可能是用尖刀划的。“为女人用的武器所伤?……反正他还未苏醒过来,而且也需要治疗……”伤口不深。他却一直处于昏迷状态。我想大概是失血过多所致。
可是他确实流了很多血吗?他的衣服上可是一滴也没有啊,“甭管它了!应该请医生……”我出了门,跑到一个朋友家。他家就住在附近,他是医科大学生,再有一年就毕业了。我一把将他从床上拽起来。
我们很快回到我的住处。我打开门。我说:“在床上……在左边……”我的双眼立刻睁得老大,因为,我的伤员,几乎可以说我的囚犯——因为我出去前已经把门锁上了——不见了。我查看房间。房间里乱成一团。所有的抽屉都大开着。我办公桌上的证件、材料给翻了个乱七八糟,捆好的一摞信上全是墨水。
我的朋友哆哆嗦嗦地微笑:“你家里是否放了很多钱?”我的朋友这样问。
“你什么意思?” 我生气了。我恼火了!我感到自己很可笑,想想这样保护一个陌生人,便感到自己更加荒唐,更加滑稽了,“他不是小偷,他什么也没有拿走。”
“你肯定吗?”
“非常肯定!你总不会说我连自己家里有什么东西都不清楚吧?东西全在……”
“哼!”
“哼什么?”
“没什么!我可以回去再睡我的觉了吧?不过,你是否先给我来杯烧酒喝。外边实在太冷,我是让你从床上拽起来……”我像一头被关在笼子里的狗熊,怒气冲冲地回到房间。
那么,我既然讲述这个故事,就一定要把它全部交待清楚。我的朋友刚刚离开,我后脚就出门了,我又回到圣乔治广场,为什么?我也不知道!或许是怀着一线渺茫的希望,在那里找到那个女人的踪迹。这太愚蠢了。我明明看到她匆匆地走了。她并没有进入附近的任何一所房子,而是朝圣拉扎尔街去了。尽管如此,我还是在这儿转悠了近一个小时,我烦躁不安,竟大声自言自语起来。直到清晨五时,我才回家睡到我那张我曾那么小心翼翼地将我的那位受伤人安顿躺下的床上,上午九点,我被看门人唤醒,她给我送来一封信。
我只瞥了一眼信封,决定再回床睡觉。但是,我发现信封上未贴邮票。信封内掉出的是一份正式公文,要我十点到位于索赛街的安全部。召见公文上注明我应去的办公室的门牌号码。我至少改变了十次主意,一会儿决定想去说明事实真相,马上又想编造一个神话故事,一会儿又决定改变某些细节。毫无疑问,我的表现幼稚得像个小孩。可是我又不愿承认这一点,哪怕是对自己都不肯承认。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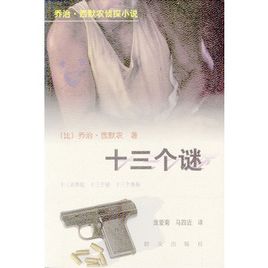 作者:乔治·西默农(美)
作者:乔治·西默农(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