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条纹的有序和无序条纹的有序和无序
你不要穿由两种(面料)做成的衣服。
(《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
“今夏,敢叫条纹流行”,几个月前一家广告公司在巴黎地铁的墙上贴得到处都是的这句广告词有点哗众取宠的味道,其中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不过我觉得最有分量的还是一个“敢”字。它表明穿条纹衣服招摇过市既不朴实也不自然,为了穿上条纹衣服必须拿出勇气,战胜羞耻心,不惧怕表现自己。不过,勇敢者会得到补偿,他领导潮流,也就是说,将成为自由、潇洒和优雅的人。我们这个时代常常就是这样:所有社会法则都可以反过来,所有法则,为了很好地实行,都不得不反过来,一开始残缺或低微的东西最终将得到升华。
对历史学家来说,这里面有值得思考的东西。跨越数个世纪,在现代条纹所表现出来的大胆和中世纪条纹频频引起公愤之间建立联系,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长期以来条纹一直是一个问题,而衣服是条纹最直观的载体。
在中世纪的西方,有许多人—真实的人或虚拟的人—被社会、文学或画像裹上了条纹服装。这些人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都是被社会排斥和被天主弃绝的人,从犹太人和异教徒到小丑或江湖艺人,其中不但有麻风病人、刽子手或妓女,而且还有小说中背叛主人的圆桌骑士,《诗篇》里的疯子或犹大。所有这些人都多多少少与魔鬼有关联,企图破坏或颠覆现有的秩序。如果说列出这些穿条纹衣服的不法之徒的名单并不难,那么要弄懂为什么会选中这样的衣服来突出他们的反面角色就更容易了,因为,这其中既无偶然性也不神秘;相反,自十二三世纪以来,各个领域都有大量史料对衣服上的条纹的贬义性或赤裸裸的魔鬼特征大书特书。
这涉及文化问题,中世纪的基督教继承了以前的价值体系,认为在《圣经》中可以找到谴责条纹服装的理由。事实上在禁止混合做法的道德书和文化书《利未记》第十九章第十九节中写道:Veste, quae ex duobus texta est, non indueris (你不要穿由两种做成的衣服)。正如《圣经•旧约》的希腊文译本一样,拉丁文版本的《圣经》很含混。也许在“duobus”这个词后面应该有一个名词,明确说明禁止在衣服上组合的是什么性质的东西,应该根据“texta”这个词和《旧约》中的其他许多章节解释为:“不要穿用两种不同的衣料做成的衣服”,也就是指由羊毛(动物的)和亚麻(植物的)织成的衣服。[1]或者应该在形容词“duobus”后面加上名词“coloribus”,理解为:“不要穿由两种颜色构成的衣服”?现代人对《圣经》的解释保留了第一种解决办法,忠实于希伯来文版本。不过中世纪的《圣经》注释者和高级神职人员有时更喜欢第二种解释,认为是指有关纤维和衣料的装饰和颜色的禁忌。
然而,也许这并不涉及(或不仅仅涉及)《圣经》问题,而是一个视觉问题?中世纪的人似乎对所有表面结构都感到厌恶,由于表面结构对外形和本质区分不清,因此会扰乱目击者的视线。中世纪人的眼睛特别注意逐层阅读。所有形象、所有表面在他看来都是有厚度的结构,也就是说是可以切割成一页一页的。它是由连续层面叠放而成的,为了读懂它,必须—与我们现代人的习惯相反—从背景层开始,经过所有中间层,最后到达最上面的一层。然而,就条纹而言,这样的阅读方式就行不通了:没有背景层和图案层,背景色和图案色;只有惟一的一层,是双色的,由许多对色彩交替出现的线条组成。就条纹而言—如同触动中世纪人的敏感神经的另一图像—异色方格一样,结构就是外形。这就是引起公愤的缘由吗?
本书希望能回答这些问题。不过,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书既不局限于中世纪也不局限于服装,相反,它将条纹和条纹服装的历史一直推进到我们所处的20世纪末,试图描述各个时代在不摒弃以前的习俗和规则的同时是如何使得条纹的有形世界和象征世界的分化越来越明显的。文艺复兴时期和浪漫主义时代使“好的”条纹(喜庆、异国情调和自由的符号)大为流行但并未因此而使“坏的”条纹消失。现代是过去所有习俗和所有法则的大荟萃,因为它让仍然魔鬼般的(死亡营里囚犯的耻辱标志)和危险的(例如公路交通信号)条纹与随着时代的发展变得卫生的(床单和内衣)、游戏的(儿童世界)、体育的(休闲服装和竞技服装)或象征性的(制服、徽章和旗帜)条纹共存。
中世纪的条纹是无序和颠覆的缘由。现代的条纹逐渐变成了建立秩序的工具。不过,如果说条纹组建世界和社会,那么它本身似乎仍然对抗一切过于严密的或过于局限的组织,它不仅在一切载体上发挥作用,而且它还可以成为自己的载体。在成为自己的载体时,它变得难以把握。一个条纹表面也可以构成另一个面积更大的条纹表面的一部分,依次类推,条纹的符号学意义是无限的。[2]
这就是为什么在以下章节中我们谈论的不是符号学的意义,而是社会史。条纹的问题事实上引出了对特定社会中直观的东西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思考。为什么在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社会分类学大都首先表现为视觉法则,视觉比听觉或触觉能更好地进行分类么?看—就一定是分类?不管是在所有文化中还是就动物世界而言,这都不是真的。同样,为什么贬义的信号,即让人注意那些被社会排斥的人、危险的地方或负面作用的符号比褒义的符号更加突出(也更加醒目)?为什么历史学家对批驳的资料比对颂扬的资料更加得心应手?
对于这些复杂深奥的问题我只能给出简洁的答案。一方面是因为本书不打算写成长篇大论[3];另一方面,因为条纹是一种如此活跃的表面结构以至只能对它一眼扫过,条纹不等待、不停留。它处于永恒的运动状态(因为这一点艺术家们为之倾倒:画家、摄影家、电影工作者),激活它所碰到的一切,不停地前进,好像乘着风一样。在中世纪,转动人类命运车轮的命运女神常常穿一件条纹长袍。今天,在游乐场,穿条纹服装的小学生常常比其他孩子更活跃。还有,在运动场上,条纹鞋比单色鞋跑得更快。[4]因此,一本探讨条纹的书也应体现出迅速和快捷的特点。
二、穿条纹衣服的魔鬼加尔默罗修士的耻辱
所有丑闻都留下了证据和文献。通过这些证据和文献,古代历史学家们常常对秩序的破坏比对社会秩序本身知道得更多。中世纪以来有关条纹和条纹服装的情况就是这样。单色没有什么文献资料,因为它代表普通的、日常的和“标准的”,而条纹却有大量文献资料,因为它引起混乱,因为它遭人非议。
(一)加尔默罗*修士的耻辱
丑闻发生在13世纪的法国,就在1254年夏末,当时圣路易正经历了一次不幸的十字军东征,在遭到悲惨的囚禁和长达四年逗留圣地的日子后返回巴黎。国王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他带回了一些来法国的新教徒,在这些新教徒中有几个是加尔默罗山圣母会的修士。丑闻因他们而起:他们穿着条纹大衣。
加尔默罗会修士最早的由来是12世纪居住在巴勒斯坦的卡尔迈勒山**附近的几个隐修士,他们试图体会最初的沙漠修士的祈祷和苦修生活。根据传说,一位卡拉布里亚骑士贝托德于1154年把他们集合在一起。随后,朝圣者和十字军参加者加入了他们的行列。1209年,耶路撒冷的主教给他们制定了以极端禁欲主义为基础的清规戒律。不过后来教皇格列高利九世稍稍放松了对他们的规定,主要是允许他们在城市定居和专心布道。加尔默罗于是进入了托钵修会的行列,像方济各会和多明我会一样。此外,他们的组织也模仿后者,像所有托钵修会一样,加尔默罗会的修士们也开始在大学、波伦亚和巴黎教书[5]。这是因为耶路撒冷的拉丁王国处境艰难,总是受到穆斯林的压迫和威胁,被迫永远离开圣地。事实上,在圣路易回来前几年他们分散在西方各地(例如从1247年起他们在剑桥)。不过,我们感兴趣的是,正是由于他们在1254年来到巴黎才开始了持续几十年的有关服装的长期论战。
现在我们找不到有关13世纪中叶加尔默罗修士服饰的图像证据,相反,文字证据却很多。文字记述的主要不是长袍的颜色—棕色、浅黄褐色、灰色、黑色,总之是深色—而是大衣的图案:条纹图案,有时是白色和棕色相间的,有时是白色和黑色相间的,不过后者比较少见。很早就有了传说,解释与《圣经》有关的神圣的条纹长袍起源。据说这是模仿加尔默罗会的神秘创始人先知艾利的长袍:在天上乘着火的战车奔驰时,他将白色大斗篷扔向信徒艾利斯,斗篷以棕色条纹的形式保存了穿越火焰留下的烧焦痕迹。美丽的传说把中世纪的人最为着迷的一个《圣经》人物搬上了舞台:救世英雄艾利,他是《圣经》中少有的不死的人物之一。传说还强调了通过长袍授职的象征意义:对于中世纪的文化来说,长袍是符号的载体,交付长袍的举动与通行仪式和进入新的状态有关。
13世纪末的某些文章将象征性注释发展到明确指出加尔默罗长袍上有四条白色条纹,代表四德:勇、义、智、节,白色条纹之间的三条棕色条纹,让人想起对神三德(信、望、爱)。事实上,从不曾有过任何规定对加尔默罗修士长袍上的条纹的数量、宽度和方向加以限制。在后来的图像资料中能够看到各种条纹:窄条纹、宽条纹、竖条纹、横条纹、斜条纹,似乎这些既不重要也无意义。重要的是长袍是条纹的,也就是说不是单色的,与其他人—乞丐、僧侣或军人的长袍不一样,总而言之是与众不同的,事实上,它是如此与众不同,以致于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众矢之的。
一到巴黎,加尔默罗修士们就成为人们讥讽和诅咒的对象,人们对他们指指点点,破口大骂,嘲笑讥讽,管他们叫“斜条修士”,“斜条”是一个极带贬义的词,在古法语中不仅表示条纹而且还表示私生子(16世纪流行的一种讽刺诗保留了这种含义)。[6]
讥讽条纹服装并不是巴黎独有的现象,在英国、意大利、普罗旺斯、朗格多克的城市里,在罗讷和莱茵河山谷的城市里,新来定居的加尔默罗修士们同样受到人们的嘲笑。有时,人们不但动口还动手,身体伤害伴随着言语伤害。人们“痛打”加尔默罗会修士就像常常“痛打”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一样。多明我会修士和方济各会修士也生活在城市里,在世俗社会中,而不是像僧侣们一样生活在偏僻的修道院。[7]人们谴责他们不只是因为他们的衣着,还因为他们贪婪、虚伪、不忠。人们把他们看作是魔鬼和反基督者。加尔默罗会修士也以化缘为生,但他们的修会不那么强大,对王储的影响没有那么大,与宗教或政治压迫工具的联系也没有那么密切。对于可怜的加尔默罗会修士,人们主要是谴责他们穿条纹长袍。
在巴黎他们有另一项罪名,就是与不发愿的修女们,即住在塞纳河右岸的他们的近邻,来往过密。在一首猛烈抨击托钵修会的诗中,诗人吕特伯夫指责他们已经成了巴黎作恶多端的罪人,对这种近邻关系和可能产生的后果感到愤慨。
斜条修士挨着不发愿的修女
一墙之隔,咫尺之遥……[8]
不过最大的问题还是斜条长袍,也就是条纹长袍。在1260年初,在城里,由于群情激愤,以致亚历山大四世特意要求加尔默罗会修士们放弃条纹长袍,改穿单色长袍。拒绝、论战、威胁,冲突白热化,难以平息,持续超过1/4个世纪的时间。加尔默罗会先后与10个教皇交过锋。1274年在里昂的全体宗教评议会上,加尔默罗修士的毫不妥协差一点要了他们的命。如果说他们的修会没有像其他20个“次要的”托钵修会那样被取缔,那是因为他们的新会长皮埃尔•德米罗(1274-1294)许诺服从教皇的意愿,尽快解决长袍问题。事实上,此后经过长达13年之久的争论、谈判、承诺、让步,最后才在1287年,在蒙彼利埃的会长教务会上,玛丽-马德莱娜节那天,修士们决定放弃“斜条”长袍,改穿全白的无袖长袍。但在某些偏远省份,莱茵河沿岸地区和西班牙、匈牙利的加尔默罗修士拒绝服从命令,仍然穿招人非议的服装,直至14世纪初。不过在1295年,卜尼法斯八世教皇为此专门下达教皇谕旨,进一步肯定了1287年更换长袍的决定并再次重申严禁一切修会的信徒穿条纹衣服。[9]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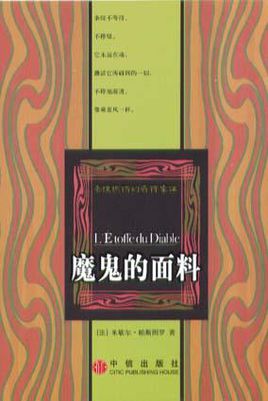 作者:米歇尔・帕斯图罗 (法)
作者:米歇尔・帕斯图罗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