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萨克村镇的果园、街道、房屋、篱笆,都沉没到望不到边的、 暑热的尘雾里,闷得喘不过气来,只有那塔形的白杨的尖顶,高髙 地窥视着。
说话声、喧闹声、犬吠声、马嘶声、孩子的哭声、难听的谩骂声、 女人的呼应声,以及含着醉意的手风琴声伴着的放荡的沙哑的歌 声,各种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就象一个空前巨大的没王的蜂 巢,张惶失措地发着嘈杂、沉痛的声音。
这无边无际的热烘烘的一团混乱,吞没了草原,一直到那土岗 上的风磨跟前,——就在那里也是一片经久不息的千万人的喊声。
一条冰凉的山水,从村外流过。那山水泡沫飞溅,奔腾喧嚣。暑 热的尘雾遮不住的只有这奔腾喧嚣的河水声。河那边远远的高大 的蓝山,把半个天都遮住了。
号称褐色草原强盗的老鹰,在暑热的闪闪发光的青空,惊奇地 飞翔着,谛听着,转动着勾嘴,一点也摸不清,——还没有过这样的 情况呢。
也许这是庙会吧。可是为什么到处都不见帐棚,没有商人,也 没有成堆的货物呢?
也许这是移民的宿营地吧。可是哪来的这些大炮、弹药箱、两 轮车和架着的步枪呢?
也许这是部队吧。可是为什么到处有孩子哭;步枪上晒着尿
布;大炮上吊着摇篮;青年妇女喂着孩子吃奶;牛和拉炮车的马一 块吃干草;晒黑了的女人和姑娘们,把锅吊在烧着干牛粪的冒烟的 火上煮腌猪油小米饭呢?
一片混乱、莫名其妙、漫天灰尘、乱七八糟;叫嚣、喧闹、异常嘈 杂的声音,都混杂在一起。
只有哥萨克女人、老婆婆和孩子们留在村镇里。哥萨克男人都 忽然消失了,连一个也不见了。哥萨克女人在屋里隔着窗子,望着 那大街小巷尘雾迷漫的所多玛和俄摩拉①说:
“迟早要把你们的眼睛都挖掉!……”
在这一片乱哄哄的牛叫、鸡鸣和说话声里,忽而听到一阵伤风 的嘶哑的声音,忽而又传来一阵粗犷的草原上的嘹亮嗓音:
“同志们,开大会去!……”
“开会去!……”
“喂,集合吧,弟兄们!……”
“到山岗踉前去! ”
“到风磨跟前去! ”
灼热的灰尘,随着逐渐凉爽下来的太阳,慢慢落下去,白杨的 塔形的高大尖顶,整个儿都露出来了。
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果园都露出来了,农舍都发着白色。所 有大街小巷,果园里里外外,从村这边到村那边,一直到草原的土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所多玛和俄摩拉是罪恶之地。耶和华降琉 灌与火,毁灭之后,成为一片混乱。
岗上,到那向四面伸着蹼状长指的风磨跟前,到处都挤满了运货马 车、大车、两轮车、马和牛。
风磨周围,人海随着越来越喧闹的声音,也扩大起来,青铜色 的人脸,象一个个斑点,消失在无边的人海里。白胡子老头、面容憔 悴的女人,姑娘们快活的眼睛;孩子们在腿下乱钻;狗急促地喘着 气,抽动着伸出的舌头,——这一切都沉没在庞大的、淹没一切的 战士群里。有些戴着长毛的英武的高筒帽,有些戴着肮脏的军帽, 有些戴着帽缘下垂的山民的毡帽。有的穿着破烂的军便服,有的穿 着褪色的印花布衬衣,有的穿着契尔克斯装?,有些光着上身,青 铜色的肌肉发达的身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机枪子弹带。头顶上是一 片凌乱的深蓝色枪刺。黑魆越的旧风磨,惊奇地凝视着:从来没有 过这样的情況呢。
团长、营长、连长、参谋长都聚集到土岗上的风磨跟前。这些团 长、营长、连长都是些什么人呢?有的是沙皇军队的士兵提升成军 官的,有的是从各城镇来的理发匠、箍桶匠、细木匠、渔民和水手。 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街道上、自己的村镇里、自己的庄子里、自 己的村子里组织起来的红军小队的队长。也有些是来投靠革命的 旧军官。
长胡子、宽肩膀的大个子团长沃洛比约夫,爬到一端有轮子的 横梁上,横梁在他脚下吱吱乱响,他用宏亮的声音,对群众喊道:
“同志们! ”
在这成千上万的青铜色的面庞前边,在这万目睽睽的群众面 前,他和他的声音显得多么微弱啊。其余的指挥员统统都聚在他跟 前。
①契尔克斯装是离加索山民和哥萨克穿的一种束黷无领的长袍或长掛。
“同志们!……”
“滾你的!”……”
“打倒!……”
“滚你妈的!……”
“不要……”
“官长,你妈的!……”
“难道他没有戴过肩章?吗?! ”
“不过他早都撕掉了……”
“你干吗乱嚷呢?……”
“揍他,他妈的! ”
无边的人海掀起了森林一般的人手。难道能辨清谁在喊叫什 么吗!
风磨跟前站着一个整个身子活像用铅捶成的矮个子,紧紧咬 着方形下颚。一双小小的灰眼睛,像两把锥子一样,在又短又齐的 眉毛下边闪闪发光,无论什么也逃不过这双眼睛。他那短短的身 影,投到地上——周围的人脚踏着他的头影。
长胡子的人从横梁上疲劳地大声喊着:
“等一等,都听着!……应当把情况讨论讨论……”
“滚你妈的! ”
喧噪、谩骂,把他的孤零零的声音都淹没了。
在一片手海、声海中,举起一只枯瘦的女人的手。这是一只细 长的、受尽风吹日晒以及劳苦和灾难折磨的手。她用那受尽折磨的 声音喊起来:
“我们不听,别瞎叫吧,你这死畜生……啊——啊!我的一头母
①沙皇军官均戴金边肩章,说某人戴过肩聿,即指当过白党军官的童思。 10
牛,两对公牛,一所房子和一把茶坎一这些都到哪去了?”
人群里又掀起一阵愤怒的风暴,——谁都不听,都只管喊自己
的。
“要是收了庄稼,我现在就带上粮食逃跑了。”
“都说应当逃到罗斯托夫去。”
“为什么不发给军便服?不发裹腿,也不发靴子呢?”
横梁上的人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跟来呢,要是……”
人们发起火来: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都是你们把事情弄糟了。你们这些混蛋, 你们把我们骗了!我们大家都坐在家里,都有家业,可是现在都像 丧家犬一样,要在草原上流浪了。”
“我们知道,是你们把我们带错了路,”战士们大叫着,乌黑的 枪刺乱摆起来。
“我们现在到哪去呢?! ”
“到叶卡捷琳诺达尔①去。”
“那里有沙皇士官生呢。”
“没处去……”
站在风磨跟前的有一副铁颚的人,用锐利得像锥子一样的灰 眼睛望着。
于是一阵不可收拾的吼声,从群众上面掠过:
“出卖了!”
这声音到处都能听见,那些在马车、摇篮、马匹、营火、弹药箱 跟前听不见讲话的人,也都猜着了。一阵惊慌从群众中掠过,都闷
①现名克拉斯诺达尔。
11
得上不来气。一个女人的声音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可是叫喊的却 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小兵。他有一只勾鼻子,光着上半身,穿一双不 合脚的大皮靴。
“像卖死牲口一样,把咱们的弟兄出卖了!……”
一个比人群高一头的美男子,留着刚生出来的黑髭胡,戴着海 军帽,两根飘带在晒得黑红的长脖子上飘动。他不作声地用两肘推 着,从人群里往风磨跟前挤。他恶狠狠地握紧闪闪发光的步枪,目 不转睛地盯着一群军官,往前乱挤。
“啊……算了吧! ”
那个铁颚的人,把牙关咬得更紧了。他心烦意乱地对咆哮的人 海环顾了一下:那尽是些大喊大叫的黑魆魆的嘴、黑红的脸和眉下 恶狠狠地冒着火星的眼睛。
“我的老婆在哪里?……”
那个戴海军帽的人,飘带在迎风飘动,眼看已经不远了,他依 然握紧步枪,仿佛怕失掉目标似的,眼睛盯着。他照旧在喧闹和喊 声里,在拥济不动的人群里乱挤。
那个紧咬牙关的人特别觉得难过:他曾当过机枪手,同他们肩 并肩在土耳其前线打过仗。血海……九死一生……最后这几个月 一同打过沙皇军官团、哥萨克和白党将军们:转战在叶斯克、杰木 留克、塔曼、库班的各村镇……
他张开口,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起来,可是在这片喧嚣里, 却到处都能听见他的话:?
“同志们,你们都晓得我。咱们一起流过血。你们自己推选我 当指挥员。可是现在要是都这样干,咱们就都要完蛋了。哥萨克和 沙皇军官团从四面打来了。连一点工夫也不能耽误了。”
他这满嘴乌克兰口音,才贏得了人们的好感。
12
“可是难道你没有戴过肩章吗?! ”光着上半身的小兵,用剌耳 的尖声叫起来。
“难道是我去找肩章戴吗?你们自己知道,我在前方打仗,当官 的硬给我戴上的。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人吗?难道我不是同大家一 样,像牛一样干活,受尽艰难困苦吗?……不是同你们在一起犁过 地,种过地吗?……”
“对,对,”乱哄哄的人声说,“是咱们的人! ”
穿海军服的高个子,终于从人丛中挤出来,两步跑到跟前,依 然不作声地望着,用全力把枪剌一挥,枪托把后边的人撞了一下。 有一副铁颚的人,一点也没躲闪,只有那好像微笑似的一阵痉挛, 刹那间从那黄得象熟皮子似的脸上掠过。
一个矮个子的、光身子的人,像小公牛似的勾着头,从旁边用 肩膀使劲在水手的肘子下边一撞。
“你干吗呢! ”
这么一来,举起的枪刺,被推到一边,没有剌到咬紧牙关的那 人身上,却剌进一个站在旁边的青年营长的肚子上,剌刀一直插到 刀颈跟前。那人大声出了一口气,像蒸气喷出来似的,仰天倒下去 了。那大高个子怒气冲冲地用力拔着刺到脊椎骨上的刀尖。
一个没胡子、脸像姑娘似的连长,抓住风磨的轮翅,爬上去。轮 翅吱吱响着转下来,他又落到地上。除了有一副方颚的人以外,其 余的人都掏出手枪,——在那些变得难看的苍白的脸上,都流露出 伤心的样子。
又有几个人疯狂地睁大眼睛,慌忙握紧步枪,从人丛中钻出 来,朝风磨跟前冲去。
“这些狗东西不得好死! ”
“揍他们!叫他们绝种!……”
13
忽然间,鸦雀无声。所有的人头都转过来,所有的眼睛都朝一 个方向望去。
一匹黑马,伸成一条线,肚皮几乎要挨着地,在草原上飞跑,一 个人骑在马上,身着红条子布衫,胸和头贴到马鬃上,两手垂在两 旁。跑近了,越跑越近了……疯狂的马,看来是在拼全力飞跑。灰尘 在后面飞扬。雪片似的白沫,喷到胸脯上。马的两肋汗淋淋的,像水 洗过一样。骑马的人把头依旧贴到马鬃上,随着马跑的步子摇摆。
草原上又腾起一团黑色的烟尘。
人群里传出说话声:
“又一个飞跑来了!”
“瞧,跑得多快……”
一匹黑马跑过来,鼻子呼呼出着气,口里流着白沫,跑到人群 前面即刻停住,后腿打了一个弯卧下去;穿红条子布衫的骑马的 人,像一条布袋似的,从马头上翻下去,闷腾腾地扑通一声落到地 上,两手展开,很不自然地垂着头。
一些人扑到倒下去的人跟前,另一些人跑到陡立起来的马跟 前。马的黑肚子上染着又粘又红的血。
“这是奥赫里姆呀! ”跑到跟前的人叫着,小心地把僵冷了的尸 体放好。肩上和胸上的刀口,都血淋淋地张着,背上有凝结了的黑 血斑。
可是在风磨那面,在马车中间,在大街小巷里,在整个人群里, 掀起一阵难以熄灭的惊慌:
“哥萨克把奥赫里姆砍死了!……”
“唉,真可怜!……”
“把哪个奥赫里姆砍死了?”
“呸,发昏了吗!不晓得吗!巴甫洛夫村里的。就是山沟里有
14
房子的那个。”
第二匹马跑来了。人脸、汗透了的小衫、手、光着的脚、裤子,满 是血迹斑斑,是自己的血呢,还是别人的血?——眼睛瞪得圆圆的。 他从摇摆不定的马背上跳下来,扑到躺着的人跟前,躺着的人脸上 流着一种透明的蜡一般的黄汁,苍绳在眼睛上爬来爬去。
“奥赫里姆! ”
后来,他即刻扑到地上,把耳朵贴到血污的胸口上,即刻又站 起来,立在他跟前,低着头说:
“儿子……我的儿子!……”
“死了, ”周围的人用镇静的声音说。
那人又站了一会,就用那永远伤风的哑嗓子喊起来,声音一直 传到马车跟前最边上的房子里:
“斯拉夫村、波达夫村、彼得罗夫村和斯季布利耶夫村,都叛乱 了。每个村的教堂前的广场上,即刻都竖起了绞架,只要一落到他 们手里,就都会被绞死。白党来到斯季布利耶夫村,用马刀砍,绞 杀,枪毙,骑着马把人往库班河里赶。遇到外乡人,不管是老头子, 还是老婆子,毫不留情一齐杀光。他们以为我们全是布尔什维克。 看瓜的老头子奥帕斯纳,就是他的房子对着亚夫多哈的那个老头 子……”
“我们知道! ”轰然响起一阵简短的说话声。
“……他跪到他们脚下求情,——也把他绞死了。他们的武器 多极了。女人们、孩子们,白天夜里都在菜园里、果园里挖埋藏的步 枪、机枪,把藏在干草垛里的装满炮弹和子弹的木箱,都搬出来, ——这些都是从土耳其战场上弄回来的,真是多得数不清。还有大 炮呢。说也奇怪。像着火了,全库班都燃烧起来。咱们的当兵的弟 兄们,也被折磨得要命,把他们吊死在树上。有些部队单独向各地
15
说话声、喧闹声、犬吠声、马嘶声、孩子的哭声、难听的谩骂声、 女人的呼应声,以及含着醉意的手风琴声伴着的放荡的沙哑的歌 声,各种的声音,从四面八方传来。就象一个空前巨大的没王的蜂 巢,张惶失措地发着嘈杂、沉痛的声音。
这无边无际的热烘烘的一团混乱,吞没了草原,一直到那土岗 上的风磨跟前,——就在那里也是一片经久不息的千万人的喊声。
一条冰凉的山水,从村外流过。那山水泡沫飞溅,奔腾喧嚣。暑 热的尘雾遮不住的只有这奔腾喧嚣的河水声。河那边远远的高大 的蓝山,把半个天都遮住了。
号称褐色草原强盗的老鹰,在暑热的闪闪发光的青空,惊奇地 飞翔着,谛听着,转动着勾嘴,一点也摸不清,——还没有过这样的 情况呢。
也许这是庙会吧。可是为什么到处都不见帐棚,没有商人,也 没有成堆的货物呢?
也许这是移民的宿营地吧。可是哪来的这些大炮、弹药箱、两 轮车和架着的步枪呢?
也许这是部队吧。可是为什么到处有孩子哭;步枪上晒着尿
布;大炮上吊着摇篮;青年妇女喂着孩子吃奶;牛和拉炮车的马一 块吃干草;晒黑了的女人和姑娘们,把锅吊在烧着干牛粪的冒烟的 火上煮腌猪油小米饭呢?
一片混乱、莫名其妙、漫天灰尘、乱七八糟;叫嚣、喧闹、异常嘈 杂的声音,都混杂在一起。
只有哥萨克女人、老婆婆和孩子们留在村镇里。哥萨克男人都 忽然消失了,连一个也不见了。哥萨克女人在屋里隔着窗子,望着 那大街小巷尘雾迷漫的所多玛和俄摩拉①说:
“迟早要把你们的眼睛都挖掉!……”
在这一片乱哄哄的牛叫、鸡鸣和说话声里,忽而听到一阵伤风 的嘶哑的声音,忽而又传来一阵粗犷的草原上的嘹亮嗓音:
“同志们,开大会去!……”
“开会去!……”
“喂,集合吧,弟兄们!……”
“到山岗踉前去! ”
“到风磨跟前去! ”
灼热的灰尘,随着逐渐凉爽下来的太阳,慢慢落下去,白杨的 塔形的高大尖顶,整个儿都露出来了。
眼睛所能看到的地方,果园都露出来了,农舍都发着白色。所 有大街小巷,果园里里外外,从村这边到村那边,一直到草原的土
①《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记载,所多玛和俄摩拉是罪恶之地。耶和华降琉 灌与火,毁灭之后,成为一片混乱。
岗上,到那向四面伸着蹼状长指的风磨跟前,到处都挤满了运货马 车、大车、两轮车、马和牛。
风磨周围,人海随着越来越喧闹的声音,也扩大起来,青铜色 的人脸,象一个个斑点,消失在无边的人海里。白胡子老头、面容憔 悴的女人,姑娘们快活的眼睛;孩子们在腿下乱钻;狗急促地喘着 气,抽动着伸出的舌头,——这一切都沉没在庞大的、淹没一切的 战士群里。有些戴着长毛的英武的高筒帽,有些戴着肮脏的军帽, 有些戴着帽缘下垂的山民的毡帽。有的穿着破烂的军便服,有的穿 着褪色的印花布衬衣,有的穿着契尔克斯装?,有些光着上身,青 铜色的肌肉发达的身上;十字交叉地背着机枪子弹带。头顶上是一 片凌乱的深蓝色枪刺。黑魆越的旧风磨,惊奇地凝视着:从来没有 过这样的情況呢。
团长、营长、连长、参谋长都聚集到土岗上的风磨跟前。这些团 长、营长、连长都是些什么人呢?有的是沙皇军队的士兵提升成军 官的,有的是从各城镇来的理发匠、箍桶匠、细木匠、渔民和水手。 这些都是他们在自己的街道上、自己的村镇里、自己的庄子里、自 己的村子里组织起来的红军小队的队长。也有些是来投靠革命的 旧军官。
长胡子、宽肩膀的大个子团长沃洛比约夫,爬到一端有轮子的 横梁上,横梁在他脚下吱吱乱响,他用宏亮的声音,对群众喊道:
“同志们! ”
在这成千上万的青铜色的面庞前边,在这万目睽睽的群众面 前,他和他的声音显得多么微弱啊。其余的指挥员统统都聚在他跟 前。
①契尔克斯装是离加索山民和哥萨克穿的一种束黷无领的长袍或长掛。
“同志们!……”
“滾你的!”……”
“打倒!……”
“滚你妈的!……”
“不要……”
“官长,你妈的!……”
“难道他没有戴过肩章?吗?! ”
“不过他早都撕掉了……”
“你干吗乱嚷呢?……”
“揍他,他妈的! ”
无边的人海掀起了森林一般的人手。难道能辨清谁在喊叫什 么吗!
风磨跟前站着一个整个身子活像用铅捶成的矮个子,紧紧咬 着方形下颚。一双小小的灰眼睛,像两把锥子一样,在又短又齐的 眉毛下边闪闪发光,无论什么也逃不过这双眼睛。他那短短的身 影,投到地上——周围的人脚踏着他的头影。
长胡子的人从横梁上疲劳地大声喊着:
“等一等,都听着!……应当把情况讨论讨论……”
“滚你妈的! ”
喧噪、谩骂,把他的孤零零的声音都淹没了。
在一片手海、声海中,举起一只枯瘦的女人的手。这是一只细 长的、受尽风吹日晒以及劳苦和灾难折磨的手。她用那受尽折磨的 声音喊起来:
“我们不听,别瞎叫吧,你这死畜生……啊——啊!我的一头母
①沙皇军官均戴金边肩章,说某人戴过肩聿,即指当过白党军官的童思。 10
牛,两对公牛,一所房子和一把茶坎一这些都到哪去了?”
人群里又掀起一阵愤怒的风暴,——谁都不听,都只管喊自己
的。
“要是收了庄稼,我现在就带上粮食逃跑了。”
“都说应当逃到罗斯托夫去。”
“为什么不发给军便服?不发裹腿,也不发靴子呢?”
横梁上的人说:
“那么,你们为什么要跟来呢,要是……”
人们发起火来:
“都是你们干的好事。都是你们把事情弄糟了。你们这些混蛋, 你们把我们骗了!我们大家都坐在家里,都有家业,可是现在都像 丧家犬一样,要在草原上流浪了。”
“我们知道,是你们把我们带错了路,”战士们大叫着,乌黑的 枪刺乱摆起来。
“我们现在到哪去呢?! ”
“到叶卡捷琳诺达尔①去。”
“那里有沙皇士官生呢。”
“没处去……”
站在风磨跟前的有一副铁颚的人,用锐利得像锥子一样的灰 眼睛望着。
于是一阵不可收拾的吼声,从群众上面掠过:
“出卖了!”
这声音到处都能听见,那些在马车、摇篮、马匹、营火、弹药箱 跟前听不见讲话的人,也都猜着了。一阵惊慌从群众中掠过,都闷
①现名克拉斯诺达尔。
11
得上不来气。一个女人的声音歇斯底里地大叫起来,可是叫喊的却 不是女人,而是一个小兵。他有一只勾鼻子,光着上半身,穿一双不 合脚的大皮靴。
“像卖死牲口一样,把咱们的弟兄出卖了!……”
一个比人群高一头的美男子,留着刚生出来的黑髭胡,戴着海 军帽,两根飘带在晒得黑红的长脖子上飘动。他不作声地用两肘推 着,从人群里往风磨跟前挤。他恶狠狠地握紧闪闪发光的步枪,目 不转睛地盯着一群军官,往前乱挤。
“啊……算了吧! ”
那个铁颚的人,把牙关咬得更紧了。他心烦意乱地对咆哮的人 海环顾了一下:那尽是些大喊大叫的黑魆魆的嘴、黑红的脸和眉下 恶狠狠地冒着火星的眼睛。
“我的老婆在哪里?……”
那个戴海军帽的人,飘带在迎风飘动,眼看已经不远了,他依 然握紧步枪,仿佛怕失掉目标似的,眼睛盯着。他照旧在喧闹和喊 声里,在拥济不动的人群里乱挤。
那个紧咬牙关的人特别觉得难过:他曾当过机枪手,同他们肩 并肩在土耳其前线打过仗。血海……九死一生……最后这几个月 一同打过沙皇军官团、哥萨克和白党将军们:转战在叶斯克、杰木 留克、塔曼、库班的各村镇……
他张开口,用低沉而坚定的声音说起来,可是在这片喧嚣里, 却到处都能听见他的话:?
“同志们,你们都晓得我。咱们一起流过血。你们自己推选我 当指挥员。可是现在要是都这样干,咱们就都要完蛋了。哥萨克和 沙皇军官团从四面打来了。连一点工夫也不能耽误了。”
他这满嘴乌克兰口音,才贏得了人们的好感。
12
“可是难道你没有戴过肩章吗?! ”光着上半身的小兵,用剌耳 的尖声叫起来。
“难道是我去找肩章戴吗?你们自己知道,我在前方打仗,当官 的硬给我戴上的。难道我不是你们的人吗?难道我不是同大家一 样,像牛一样干活,受尽艰难困苦吗?……不是同你们在一起犁过 地,种过地吗?……”
“对,对,”乱哄哄的人声说,“是咱们的人! ”
穿海军服的高个子,终于从人丛中挤出来,两步跑到跟前,依 然不作声地望着,用全力把枪剌一挥,枪托把后边的人撞了一下。 有一副铁颚的人,一点也没躲闪,只有那好像微笑似的一阵痉挛, 刹那间从那黄得象熟皮子似的脸上掠过。
一个矮个子的、光身子的人,像小公牛似的勾着头,从旁边用 肩膀使劲在水手的肘子下边一撞。
“你干吗呢! ”
这么一来,举起的枪刺,被推到一边,没有剌到咬紧牙关的那 人身上,却剌进一个站在旁边的青年营长的肚子上,剌刀一直插到 刀颈跟前。那人大声出了一口气,像蒸气喷出来似的,仰天倒下去 了。那大高个子怒气冲冲地用力拔着刺到脊椎骨上的刀尖。
一个没胡子、脸像姑娘似的连长,抓住风磨的轮翅,爬上去。轮 翅吱吱响着转下来,他又落到地上。除了有一副方颚的人以外,其 余的人都掏出手枪,——在那些变得难看的苍白的脸上,都流露出 伤心的样子。
又有几个人疯狂地睁大眼睛,慌忙握紧步枪,从人丛中钻出 来,朝风磨跟前冲去。
“这些狗东西不得好死! ”
“揍他们!叫他们绝种!……”
13
忽然间,鸦雀无声。所有的人头都转过来,所有的眼睛都朝一 个方向望去。
一匹黑马,伸成一条线,肚皮几乎要挨着地,在草原上飞跑,一 个人骑在马上,身着红条子布衫,胸和头贴到马鬃上,两手垂在两 旁。跑近了,越跑越近了……疯狂的马,看来是在拼全力飞跑。灰尘 在后面飞扬。雪片似的白沫,喷到胸脯上。马的两肋汗淋淋的,像水 洗过一样。骑马的人把头依旧贴到马鬃上,随着马跑的步子摇摆。
草原上又腾起一团黑色的烟尘。
人群里传出说话声:
“又一个飞跑来了!”
“瞧,跑得多快……”
一匹黑马跑过来,鼻子呼呼出着气,口里流着白沫,跑到人群 前面即刻停住,后腿打了一个弯卧下去;穿红条子布衫的骑马的 人,像一条布袋似的,从马头上翻下去,闷腾腾地扑通一声落到地 上,两手展开,很不自然地垂着头。
一些人扑到倒下去的人跟前,另一些人跑到陡立起来的马跟 前。马的黑肚子上染着又粘又红的血。
“这是奥赫里姆呀! ”跑到跟前的人叫着,小心地把僵冷了的尸 体放好。肩上和胸上的刀口,都血淋淋地张着,背上有凝结了的黑 血斑。
可是在风磨那面,在马车中间,在大街小巷里,在整个人群里, 掀起一阵难以熄灭的惊慌:
“哥萨克把奥赫里姆砍死了!……”
“唉,真可怜!……”
“把哪个奥赫里姆砍死了?”
“呸,发昏了吗!不晓得吗!巴甫洛夫村里的。就是山沟里有
14
房子的那个。”
第二匹马跑来了。人脸、汗透了的小衫、手、光着的脚、裤子,满 是血迹斑斑,是自己的血呢,还是别人的血?——眼睛瞪得圆圆的。 他从摇摆不定的马背上跳下来,扑到躺着的人跟前,躺着的人脸上 流着一种透明的蜡一般的黄汁,苍绳在眼睛上爬来爬去。
“奥赫里姆! ”
后来,他即刻扑到地上,把耳朵贴到血污的胸口上,即刻又站 起来,立在他跟前,低着头说:
“儿子……我的儿子!……”
“死了, ”周围的人用镇静的声音说。
那人又站了一会,就用那永远伤风的哑嗓子喊起来,声音一直 传到马车跟前最边上的房子里:
“斯拉夫村、波达夫村、彼得罗夫村和斯季布利耶夫村,都叛乱 了。每个村的教堂前的广场上,即刻都竖起了绞架,只要一落到他 们手里,就都会被绞死。白党来到斯季布利耶夫村,用马刀砍,绞 杀,枪毙,骑着马把人往库班河里赶。遇到外乡人,不管是老头子, 还是老婆子,毫不留情一齐杀光。他们以为我们全是布尔什维克。 看瓜的老头子奥帕斯纳,就是他的房子对着亚夫多哈的那个老头 子……”
“我们知道! ”轰然响起一阵简短的说话声。
“……他跪到他们脚下求情,——也把他绞死了。他们的武器 多极了。女人们、孩子们,白天夜里都在菜园里、果园里挖埋藏的步 枪、机枪,把藏在干草垛里的装满炮弹和子弹的木箱,都搬出来, ——这些都是从土耳其战场上弄回来的,真是多得数不清。还有大 炮呢。说也奇怪。像着火了,全库班都燃烧起来。咱们的当兵的弟 兄们,也被折磨得要命,把他们吊死在树上。有些部队单独向各地
15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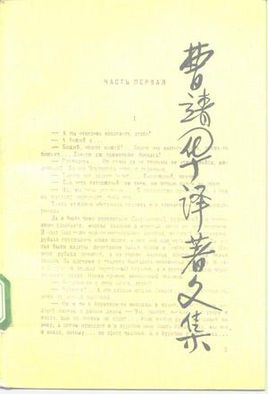 作者:曹靖华 (现代)
作者:曹靖华 (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