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写传缘起
公元2004年,中华古夏历岁在甲申,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头,我当然是从《 红楼梦 》研究的视角而言。这一年,是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 红楼梦 〉评论 》,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 曹雪芹 》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 红楼夺目红 》等红学书籍的热销,造成了一种红学热持久不衰的综合效应。周汝昌先生无疑是这一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甚至于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了“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的讨论。周汝昌坎坷了一辈子,这一下真“红”了起来,情形大概可以和周先生的开山之作《〈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刚出版不久时相比拟吧?这前后相隔也正好是半百之数——五十年。
还有凑巧的事。我于6月13日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 百家讲坛 》节目,连讲两场,题目分别是《〈 红楼梦 〉探佚 》和《 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 》。6月12日先去拜访周先生,周先生提醒我,明天是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此处不用阿拉伯数字,以显示“阴历”也 ),正好是曹雪芹的生日,也是小说中贾宝玉的生日。第二天我演讲时,开头就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两场演讲就有了“凤头”,至于后面是不是“猪肚”和“豹尾”,那当然要观众来评判了。而就在我赴北京前夕,国家图书馆的青年“红迷”于鹏打长途电话来大连,说漓江出版社刘文莉编辑与出版界友人正策划要出周汝昌先生的传记,他们属意于我。不一会刘女士也来电话,说已经和周先生接触过,征求了周先生的意见,意思要我捉刀,约好6月13日在现代文学馆晤面,演讲后请我吃饭,即作商谈。这当然也有通过听我的演讲以“考核”我是否有写作“实力”的意思。计划大体不爽,只是饭局成了《 百家讲坛 》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请我和刘女士及随刘女士同来的同事汪正球编辑吃工作餐。就这中午饭半个小时光景,与刘女士、汪先生初步约定了写周汝昌先生的传记。
我答应在8月份开始动手写传,因为此前必须要把《 红楼赏诗 》的稿子杀青。到了7月下旬,就开始阅读周先生的几种著作。周先生的大著我大体上都有,但以前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层面,这一次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全人”观照。虽然我和周先生交往已经有二十余年,但真正面炙馨颏的机会也没有几次。毕竟,我和周先生是隔了“世代”的人,周先生前半生所经历见证的那些历史政治风云、社会人生世相,我缺少生动的“质感”。对周先生家世、家庭等情状的了解,除了极少几次与周夫人及周先生的子女浮表的接触外,大多数也只能从周先生著作中窥探吉光片羽而已。
既然情况如此,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周先生以红学家名世,他的学术,首推红学。但究其实,《 红楼梦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最杰出代表,周先生其实是通过《 红楼梦 》研究中华文化,除了红学,他在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等多方面也都有精深的赏会和研究,他深通英语,却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光辉。所以,应该称周汝昌为中华文化学家才更准确更本质。同时,在为这一独特的文化学术事业之毕生奋斗中,他历经曲折坎坷,正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周汝昌给红学的定位是“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顺理成章,这门学术的掌门人和泰斗自然也就是“中华文化学家”了。而且,“中华文化学家”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一位先贤所启用过,也算笔者的一点“创意”。
如何展现周汝昌的学术人生?如果变成对周先生著述的一种“注解”:何年出了第一本书,其意义如何;何年又出了第二本书,其价值安在……那也未免太笨了。以《 红楼梦 》研究的行迹为主线,而写出周先生的“人”,写出一种文化精神,写出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写出一种“意义”,是这本传记追求的目标。至于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当然需要读者的检验了。
写周先生的传记,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背景情况的了解。周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友和同事等,许多已经仙逝,而某些具体的事件和情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绝对“真实”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除了对一些硕果仅存的当事人作采访以求尽量客观之外,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的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当然这样作也许会减少某种“深刻”和“趣味”,但限于我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了。
周先生很讨厌“洋式白话文”,推崇“运用传统汉字语文、诗赋的形态与精神”,而目前新潮的文风则和周先生的雅趣颇有距离,时兴一点俏皮再加一点甜腻的格调。我的笔触达不到周先生的词气渊雅曲折,也学不来时髦的华美俗艳,却还奢望既能得到周先生的首肯,又能不被市场所厌弃,想走走中间路线,不知自己的笔力能行到什么境界,也许竟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吧。
在网上浏览时,读到《 中国艺术报 》第403期一篇署名商泽军的诗《 致周汝昌 》,颇有点意味。在此就先斩后奏,掠美转录于此,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 商先生如果看到了,请和我联系,当签赠两本拙著以表谢意 )。
这是一竿竹子,摇曳在
文字筑成的
土壤里
这是一竿头白的竹子
那华发
那清瘦的面容
那聋去的耳朵
该是怎样特殊的竹子?
听不见风声的竹子
白头的竹子
那也是
像瘦金体一样
写意的竹子
这竿竹子
从《 红楼梦 》中逸出
在唐诗宋词里长叶
用墨汁浇灌的竹子啊
却浇出了白头!
① 石建国,1920年生,河北省滦县石矿调度室统计员。
2少年被绑票的经历
“周会长家的‘老先生’魁娃也被土匪劫作秧子了!”
这条消息在咸水沽正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此际的时间背景是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历1937年。“劫秧子”就是被绑票,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土语。“老先生”则是当地对文化家庭中最幼小儿子的赞美性称呼,“老”与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恰相反,是指排行最末、年龄最幼小的意思,“先生”是对男子之尊称。寻味其词义演变来由,或者有生最小的孩子时父母年纪已经较为老大,也就是“老生子”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少爷”、“小爷”一类称谓。
这个“魁娃”就是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红学大师周汝昌,时年十九岁。
周汝昌在少年时曾有一段被土匪绑票的传奇性经历。欲知这段经历的来龙去脉,当然先得“吊吊胃口”,追溯一下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了。周汝昌乳名魁,有时候也写作奎,出生于民国七年阴历戊午三月初四辰时,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1918年4月14日上午八时左右。出生地当然是天津老家咸水沽西头周家了—— 一所门楣榜有“春晖里”的院落。
那一辈的周家子弟,本来是单名,都用“三点水”的字,如湘、潇等等,很有诗的意境。后来可能是为了填写科举考试的名讳,改成了双名,第二字排“昌”。子弟起名,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都是从《 易经 》卦名而来。汝昌则还取意《 诗经 》,祖父给起了一个字叫“寿康”,名与字相关,即《 诗经·鲁颂·宫 》“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之意,“尔”当然就是“汝”,“臧”是善美之意,祝福小孙子能一生长寿安康,兴旺发达。后来祖父又赠一字曰“禹言”,出自《 尚书·大禹谟 》中“禹拜昌言”,周汝昌长大后,嫌与晚清名人丁汝昌字“禹廷”迹近模仿,改作“玉言”,是取《 诗经·大雅·民劳 》“王欲玉女(‘玉’意为‘玉成’,‘女’意同‘汝’ )”句断章取义,表达努力成才的愿望。
这倒也是一种巧合,“玉言”似乎是一种“预言”,标示出周汝昌将以研究《 石头记 》,体会贾宝玉、林黛玉、妙玉的精神感情为毕生事业。从祖父给周汝昌起名赠字之典故来源,亦可见周汝昌的祖父是文史素养很高的人。
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就是七十二条水流,相应地,也就成了沽畔居民所在地域的称谓。在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古海河东南岸,有一条咸水沽,就是天津自古相沿的八大镇之一,乃交通要冲。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 读史方舆纪要 》中考证说,此处是南北朝、隋时之豆子。其实,豆子就是现在沽东端之“窦家岗”读音讹变。咸水沽在明朝属于河间府静海县。镇中有一座“老爷庙”( 关帝庙 ),当年供桌上有口铁磬,上面铸有一行楷字:“大明嘉靖五年月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圣帝庙”。到了清朝雍正六年或八年,才改属天津。
咸水沽是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市镇,魁娃是镇上商业会长周景颐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在家族大排行里则是第十五,也居末位,本家后辈称为“十五叔”。景颐会长本名梦薪——那一辈起名第一字用“梦”,字幼章,字是和其父的字相连属的,父亲名周铜,字印章。幼章是印章的独生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名列第五。幼章和八堂侄考取清光绪末科秀才,“景颐”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登录榜名而起的大名。周景颐的生母是周铜原配徐氏,但周汝昌没见过。周汝昌记忆中的奶奶,是徐氏死后周铜的续弦刘氏。这位刘奶奶是富家之女,但长相不佳,周铜不喜欢,夫妻感情冷淡。刘奶奶晚年缠绵病榻,周汝昌偶尔去看望,奶奶很高兴,周汝昌还记得已经说不清话的奶奶摸出一个苹果给自己。
周家是咸水沽的一个大户人家,族人众多,分居易爨,习惯上叫“东院里”、“西院里”、“北院里”……孩子们在院落里穿来穿去,跳跳蹦蹦,洋溢着很旺的人气。
周家是“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家有大木船,一艘,或者两三艘,在渤海作航运,运售东北三省的粮米和木材等物品。拥有海船,当然是财富和地位的一个标志。往上追溯,周家的先人是“担筐荷篓”从外地移民而来。周铜的兄长周锐,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就挣得自己有了船,发起家来,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到后来,周家有了当地最大的船,号称“同和周家”。据刘国华《 古镇稗史 》( 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中考述,周家有三艘海船,分别叫“登悠”、“双梯子”和“五百万”;河边也有了自己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
咸水沽的中心地带是“三里长街”,街两侧店铺栉比鳞次,商贾繁荣,周家在长街的最西头。周家的来历,从周锐、周铜往前推,已经历史烟云模糊,似乎是从江浙绍兴一带迁来的。周家的子弟,大多“北人南相”,身材容貌,不是北方的粗犷型,而是南方的清秀型,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就长得极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以至得了一个“周建人”的绰号。
周家大概天生有些文学艺术的基因,家里的子弟都能书善画,吹拉弹唱,管弦丝竹,在院落里不绝于耳。自从发家创业,周梦薪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当地的文化事业方面。这里自古是渔盐之地,读书的人不多,当时唯一一所私立小学,就是周梦薪策划经费,担任“校董”。对民间文艺更是热心扶持,逢年过节,高跷、秧歌、龙灯、法鼓,种种活动,都由他主持,出资购买衣装道具,组织表演,热闹非凡。做这些公益事业,既有一种服务乡梓的成就感,也满足了自己的天分爱好,他干得很是起劲。当然,周家的威信也就在乡里渐渐树立了起来。
周梦薪的这些作为,其实是由来有自,有血胤遗传的。周汝昌后来这样忆述自己的祖父周印章( 周铜 ):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 周锐 ),创了业,任凭他施为,从其所好,买些心爱的艺术品,虽然够不上古玩的级别,但也是房屋里摆得般般样样,琳琅满目,别有奇趣。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给各种耍会的买“行头”,买乐器,自己喜欢乐器,好听唱曲,也就支持“穷哥们”耍乐自娱。凡是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他总是独力支持的赞助者,如西头的“同乐高跷老会”等。他极爱音乐、工艺、书画、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是“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
祖、父遗泽,周家一族,辈辈出音乐能手,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乡下人讲“风水迷信”,有一个说法是:“老周家坟地,祖辈出吹觱捏眼儿的人。”每逢夏日晚凉,西院里周汝昌的八堂兄周紫登( 名懋昌 )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群人,笙管笛箫,丝弦钟磬,登楼而合奏起来。
《 古镇稗史 》中说,周景颐五子分别叫震昌( 字伯安 )、祚昌( 字福民 )、泽昌( 字雨仁 )、祜昌( 字屡易未定,后来顾随赠以“受百”、“寿白” )、汝昌,都深受祖父周铜爱好文艺的影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二子祚昌是吹箫能手,箫一到他的手里,略一调停,立即妙音如缕,因此得一绰号,就叫“老箫”;三子泽昌,京胡的演奏技艺在沽上远近闻名,1949年后,沽上艺人京剧演员邵汉良回沽省亲,和沽上票友联袂演出京剧《 打渔杀家 》,主要的一个操琴伴奏者就是周泽昌。
咸水沽当地的水质是甜美滋润的,何以名“咸”?有一种传说是,咸水沽其实原名“涵水沽”,因为在海河东南岸,这块地方的河道形成一个大湾,水势颇盛大,涵水最多,故名。因为涵和咸两个字古代读音相同,时间长了,就讹“涵”为“咸”了。也许,临海就有渔盐之利,盐当然也有“咸”意了。
咸水沽这个明清古镇,距今二三十年前,镇上那个明朝嘉靖年间的关帝庙还在,庙前空地不大,四周是店铺,当中是个小小的集市,售卖食品杂物,人们叫“庙前头”。当年咸水沽遍地都是港汊溪流,芦苇草树,街镇南边是居民区,豆棚瓜架横曳竖立,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油菜花一片金黄,稻花香里蛙声不断,古柳垂杨萧飒飘曳,号称“小江南”。这样的风物民情,配上周家楼阁上传出的弦管音乐歌唱,弥漫在悠悠古镇的时空中,当真让人恍然有五柳先生陶渊明“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潜《 五柳先生传 》)的幻觉。
公元2004年,中华古夏历岁在甲申,是一个饶有意味的年头,我当然是从《 红楼梦 》研究的视角而言。这一年,是红学作为近现代意义上的“学术”而独立门户成为专学整整第一百个年头,王国维正是在1904年发表了《〈 红楼梦 〉评论 》,可以看作红学由玩笑之词而正式成“学”的一个标志。而无论从癸未说或甲申说甚至壬午说的立场,2004年也都可以看作曹雪芹仙逝第二百四十周年。由于2003年岁末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电视剧《 红楼梦 》演员“二十年再聚首”和科学教育频道《 百家讲坛 》的红学讲座以及影视频道电视剧《 曹雪芹 》的热播,还有作家出版社《 红楼夺目红 》等红学书籍的热销,造成了一种红学热持久不衰的综合效应。周汝昌先生无疑是这一热潮中最引人瞩目的人物,也是一个“毁誉参半”的人物,甚至于在网络论坛中出现了“周汝昌为什么这样火”的讨论。周汝昌坎坷了一辈子,这一下真“红”了起来,情形大概可以和周先生的开山之作《〈 红楼梦 〉新证 》在1953年刚出版不久时相比拟吧?这前后相隔也正好是半百之数——五十年。
还有凑巧的事。我于6月13日应邀在中国现代文学馆做《 百家讲坛 》节目,连讲两场,题目分别是《〈 红楼梦 〉探佚 》和《 曹雪芹思想的超前性 》。6月12日先去拜访周先生,周先生提醒我,明天是阴历四月二十六日( 此处不用阿拉伯数字,以显示“阴历”也 ),正好是曹雪芹的生日,也是小说中贾宝玉的生日。第二天我演讲时,开头就说:“大家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这两场演讲就有了“凤头”,至于后面是不是“猪肚”和“豹尾”,那当然要观众来评判了。而就在我赴北京前夕,国家图书馆的青年“红迷”于鹏打长途电话来大连,说漓江出版社刘文莉编辑与出版界友人正策划要出周汝昌先生的传记,他们属意于我。不一会刘女士也来电话,说已经和周先生接触过,征求了周先生的意见,意思要我捉刀,约好6月13日在现代文学馆晤面,演讲后请我吃饭,即作商谈。这当然也有通过听我的演讲以“考核”我是否有写作“实力”的意思。计划大体不爽,只是饭局成了《 百家讲坛 》主持人傅光明先生请我和刘女士及随刘女士同来的同事汪正球编辑吃工作餐。就这中午饭半个小时光景,与刘女士、汪先生初步约定了写周汝昌先生的传记。
我答应在8月份开始动手写传,因为此前必须要把《 红楼赏诗 》的稿子杀青。到了7月下旬,就开始阅读周先生的几种著作。周先生的大著我大体上都有,但以前主要是着眼于学术层面,这一次则把注意力集中到“全人”观照。虽然我和周先生交往已经有二十余年,但真正面炙馨颏的机会也没有几次。毕竟,我和周先生是隔了“世代”的人,周先生前半生所经历见证的那些历史政治风云、社会人生世相,我缺少生动的“质感”。对周先生家世、家庭等情状的了解,除了极少几次与周夫人及周先生的子女浮表的接触外,大多数也只能从周先生著作中窥探吉光片羽而已。
既然情况如此,我确定写传记的策略,只能以“学术”为主体。周先生以红学家名世,他的学术,首推红学。但究其实,《 红楼梦 》是中华文化的一个最杰出代表,周先生其实是通过《 红楼梦 》研究中华文化,除了红学,他在传统诗词、文论、书法、禅宗、戏曲、民俗等多方面也都有精深的赏会和研究,他深通英语,却通过中西文化比较的方式彰显出中华文化的独特光辉。所以,应该称周汝昌为中华文化学家才更准确更本质。同时,在为这一独特的文化学术事业之毕生奋斗中,他历经曲折坎坷,正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锋镝犹加,痴情未已。周汝昌给红学的定位是“新国学”和“中华文化之学”,顺理成章,这门学术的掌门人和泰斗自然也就是“中华文化学家”了。而且,“中华文化学家”似乎还没有被任何一位先贤所启用过,也算笔者的一点“创意”。
如何展现周汝昌的学术人生?如果变成对周先生著述的一种“注解”:何年出了第一本书,其意义如何;何年又出了第二本书,其价值安在……那也未免太笨了。以《 红楼梦 》研究的行迹为主线,而写出周先生的“人”,写出一种文化精神,写出一种时代的文化氛围,写出一种“意义”,是这本传记追求的目标。至于实际上能做到什么程度,那当然需要读者的检验了。
写周先生的传记,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背景情况的了解。周先生当年的一些老友和同事等,许多已经仙逝,而某些具体的事件和情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视角和态度,绝对“真实”有时其实是很难的。除了对一些硕果仅存的当事人作采访以求尽量客观之外,我确定了一个原则,就是只从周先生的经历这一角度写,而且只从正面写。当然这样作也许会减少某种“深刻”和“趣味”,但限于我自己的能力,也只能如此了。
周先生很讨厌“洋式白话文”,推崇“运用传统汉字语文、诗赋的形态与精神”,而目前新潮的文风则和周先生的雅趣颇有距离,时兴一点俏皮再加一点甜腻的格调。我的笔触达不到周先生的词气渊雅曲折,也学不来时髦的华美俗艳,却还奢望既能得到周先生的首肯,又能不被市场所厌弃,想走走中间路线,不知自己的笔力能行到什么境界,也许竟是非驴非马的“四不像”吧。
在网上浏览时,读到《 中国艺术报 》第403期一篇署名商泽军的诗《 致周汝昌 》,颇有点意味。在此就先斩后奏,掠美转录于此,作为本书的一个“引子”( 商先生如果看到了,请和我联系,当签赠两本拙著以表谢意 )。
这是一竿竹子,摇曳在
文字筑成的
土壤里
这是一竿头白的竹子
那华发
那清瘦的面容
那聋去的耳朵
该是怎样特殊的竹子?
听不见风声的竹子
白头的竹子
那也是
像瘦金体一样
写意的竹子
这竿竹子
从《 红楼梦 》中逸出
在唐诗宋词里长叶
用墨汁浇灌的竹子啊
却浇出了白头!
① 石建国,1920年生,河北省滦县石矿调度室统计员。
2少年被绑票的经历
“周会长家的‘老先生’魁娃也被土匪劫作秧子了!”
这条消息在咸水沽正不胫而走,传得纷纷扬扬。此际的时间背景是中华民国廿六年,公历1937年。“劫秧子”就是被绑票,这是天津卫的方言土语。“老先生”则是当地对文化家庭中最幼小儿子的赞美性称呼,“老”与通常理解的字面意义恰相反,是指排行最末、年龄最幼小的意思,“先生”是对男子之尊称。寻味其词义演变来由,或者有生最小的孩子时父母年纪已经较为老大,也就是“老生子”的意义?有意思的是,这里并没有“少爷”、“小爷”一类称谓。
这个“魁娃”就是后来的中国古典文学研究专家、红学大师周汝昌,时年十九岁。
周汝昌在少年时曾有一段被土匪绑票的传奇性经历。欲知这段经历的来龙去脉,当然先得“吊吊胃口”,追溯一下周汝昌的“家庭出身”和“历史渊源”了。周汝昌乳名魁,有时候也写作奎,出生于民国七年阴历戊午三月初四辰时,换算成公元纪年,就是1918年4月14日上午八时左右。出生地当然是天津老家咸水沽西头周家了—— 一所门楣榜有“春晖里”的院落。
那一辈的周家子弟,本来是单名,都用“三点水”的字,如湘、潇等等,很有诗的意境。后来可能是为了填写科举考试的名讳,改成了双名,第二字排“昌”。子弟起名,如履昌、懋昌、恒昌、泰昌、永昌,都是从《 易经 》卦名而来。汝昌则还取意《 诗经 》,祖父给起了一个字叫“寿康”,名与字相关,即《 诗经·鲁颂·宫 》“俾尔炽而昌,俾尔寿而臧”之意,“尔”当然就是“汝”,“臧”是善美之意,祝福小孙子能一生长寿安康,兴旺发达。后来祖父又赠一字曰“禹言”,出自《 尚书·大禹谟 》中“禹拜昌言”,周汝昌长大后,嫌与晚清名人丁汝昌字“禹廷”迹近模仿,改作“玉言”,是取《 诗经·大雅·民劳 》“王欲玉女(‘玉’意为‘玉成’,‘女’意同‘汝’ )”句断章取义,表达努力成才的愿望。
这倒也是一种巧合,“玉言”似乎是一种“预言”,标示出周汝昌将以研究《 石头记 》,体会贾宝玉、林黛玉、妙玉的精神感情为毕生事业。从祖父给周汝昌起名赠字之典故来源,亦可见周汝昌的祖父是文史素养很高的人。
天津卫有七十二沽,就是七十二条水流,相应地,也就成了沽畔居民所在地域的称谓。在天津市与大沽海口正中间,古海河东南岸,有一条咸水沽,就是天津自古相沿的八大镇之一,乃交通要冲。历史地理学者顾祖禹在《 读史方舆纪要 》中考证说,此处是南北朝、隋时之豆子。其实,豆子就是现在沽东端之“窦家岗”读音讹变。咸水沽在明朝属于河间府静海县。镇中有一座“老爷庙”( 关帝庙 ),当年供桌上有口铁磬,上面铸有一行楷字:“大明嘉靖五年月河间府静海县咸水沽关圣帝庙”。到了清朝雍正六年或八年,才改属天津。
咸水沽是海河老“湾”畔的一个商业市镇,魁娃是镇上商业会长周景颐最小的儿子,排行第五,在家族大排行里则是第十五,也居末位,本家后辈称为“十五叔”。景颐会长本名梦薪——那一辈起名第一字用“梦”,字幼章,字是和其父的字相连属的,父亲名周铜,字印章。幼章是印章的独生子,但在叔伯兄弟的大排行中名列第五。幼章和八堂侄考取清光绪末科秀才,“景颐”就是专为参加科举考试登录榜名而起的大名。周景颐的生母是周铜原配徐氏,但周汝昌没见过。周汝昌记忆中的奶奶,是徐氏死后周铜的续弦刘氏。这位刘奶奶是富家之女,但长相不佳,周铜不喜欢,夫妻感情冷淡。刘奶奶晚年缠绵病榻,周汝昌偶尔去看望,奶奶很高兴,周汝昌还记得已经说不清话的奶奶摸出一个苹果给自己。
周家是咸水沽的一个大户人家,族人众多,分居易爨,习惯上叫“东院里”、“西院里”、“北院里”……孩子们在院落里穿来穿去,跳跳蹦蹦,洋溢着很旺的人气。
周家是“养大船的”。养大船就是自己家有大木船,一艘,或者两三艘,在渤海作航运,运售东北三省的粮米和木材等物品。拥有海船,当然是财富和地位的一个标志。往上追溯,周家的先人是“担筐荷篓”从外地移民而来。周铜的兄长周锐,早先给镇上东头大户韩家船上做事,后来就挣得自己有了船,发起家来,逐渐成为镇上的“名门”望族。到后来,周家有了当地最大的船,号称“同和周家”。据刘国华《 古镇稗史 》( 中国文学出版社2004年5月出版 )中考述,周家有三艘海船,分别叫“登悠”、“双梯子”和“五百万”;河边也有了自己家的专用码头装卸货物,叫“同和码头”。
咸水沽的中心地带是“三里长街”,街两侧店铺栉比鳞次,商贾繁荣,周家在长街的最西头。周家的来历,从周锐、周铜往前推,已经历史烟云模糊,似乎是从江浙绍兴一带迁来的。周家的子弟,大多“北人南相”,身材容貌,不是北方的粗犷型,而是南方的清秀型,周汝昌的四哥周祜昌就长得极像鲁迅的兄弟周建人,以至得了一个“周建人”的绰号。
周家大概天生有些文学艺术的基因,家里的子弟都能书善画,吹拉弹唱,管弦丝竹,在院落里不绝于耳。自从发家创业,周梦薪就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注到当地的文化事业方面。这里自古是渔盐之地,读书的人不多,当时唯一一所私立小学,就是周梦薪策划经费,担任“校董”。对民间文艺更是热心扶持,逢年过节,高跷、秧歌、龙灯、法鼓,种种活动,都由他主持,出资购买衣装道具,组织表演,热闹非凡。做这些公益事业,既有一种服务乡梓的成就感,也满足了自己的天分爱好,他干得很是起劲。当然,周家的威信也就在乡里渐渐树立了起来。
周梦薪的这些作为,其实是由来有自,有血胤遗传的。周汝昌后来这样忆述自己的祖父周印章( 周铜 ):他命中有那么一个好哥哥( 周锐 ),创了业,任凭他施为,从其所好,买些心爱的艺术品,虽然够不上古玩的级别,但也是房屋里摆得般般样样,琳琅满目,别有奇趣。他喜欢作兴民间歌舞,给各种耍会的买“行头”,买乐器,自己喜欢乐器,好听唱曲,也就支持“穷哥们”耍乐自娱。凡是乡镇这一等级的民间文艺活动,他总是独力支持的赞助者,如西头的“同乐高跷老会”等。他极爱音乐、工艺、书画、园林这些方面的事情。他可不是“文人墨客”,而是一个民间很不俗气的人。
祖、父遗泽,周家一族,辈辈出音乐能手,几乎人人都能拿得起一件乐器。乡下人讲“风水迷信”,有一个说法是:“老周家坟地,祖辈出吹觱捏眼儿的人。”每逢夏日晚凉,西院里周汝昌的八堂兄周紫登( 名懋昌 )常常召集弟兄子侄一群人,笙管笛箫,丝弦钟磬,登楼而合奏起来。
《 古镇稗史 》中说,周景颐五子分别叫震昌( 字伯安 )、祚昌( 字福民 )、泽昌( 字雨仁 )、祜昌( 字屡易未定,后来顾随赠以“受百”、“寿白” )、汝昌,都深受祖父周铜爱好文艺的影响,吹拉弹唱样样精通。二子祚昌是吹箫能手,箫一到他的手里,略一调停,立即妙音如缕,因此得一绰号,就叫“老箫”;三子泽昌,京胡的演奏技艺在沽上远近闻名,1949年后,沽上艺人京剧演员邵汉良回沽省亲,和沽上票友联袂演出京剧《 打渔杀家 》,主要的一个操琴伴奏者就是周泽昌。
咸水沽当地的水质是甜美滋润的,何以名“咸”?有一种传说是,咸水沽其实原名“涵水沽”,因为在海河东南岸,这块地方的河道形成一个大湾,水势颇盛大,涵水最多,故名。因为涵和咸两个字古代读音相同,时间长了,就讹“涵”为“咸”了。也许,临海就有渔盐之利,盐当然也有“咸”意了。
咸水沽这个明清古镇,距今二三十年前,镇上那个明朝嘉靖年间的关帝庙还在,庙前空地不大,四周是店铺,当中是个小小的集市,售卖食品杂物,人们叫“庙前头”。当年咸水沽遍地都是港汊溪流,芦苇草树,街镇南边是居民区,豆棚瓜架横曳竖立,房舍与菜圃稻畦相间为邻,油菜花一片金黄,稻花香里蛙声不断,古柳垂杨萧飒飘曳,号称“小江南”。这样的风物民情,配上周家楼阁上传出的弦管音乐歌唱,弥漫在悠悠古镇的时空中,当真让人恍然有五柳先生陶渊明“无怀氏之民欤?葛天氏之民欤”( 陶潜《 五柳先生传 》)的幻觉。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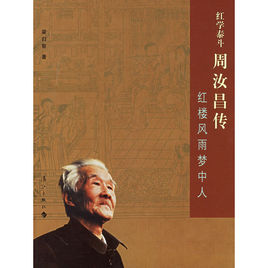 作者:梁归智(现代)
作者:梁归智(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