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1979年,我40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科院近代史所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曾是明代特務機關、北洋政府黎元洪大總統宅第、學術大師胡適的住宅。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機構的任務,我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過去親密無間的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也決不捏造罪名陷害別人。她為此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有點「看破紅塵」的心緒,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她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着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
作此研究,談何容易!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也即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絕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儲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1929年被開除到1942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1929年轉向中國托派及1931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1952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這些資料會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着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落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獲得這批後期歷史資料後,為貫徹資料共用和推動全國陳獨秀全面研究的原則,我們於是聯絡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對陳獨秀有研究的學者收集、研究並最終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共分四卷。安徽學者主編第一卷(1879–1915),即陳獨秀早期資料,陸續收集到《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迄今發現的陳獨秀最早的著作《揚子江形勢略論》、早期創辦的刊物《安徽俗話報》等;北京學者主編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期出版的《廣東群報》,記錄了陳的大量言論和活動;上海學者主編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陳獨秀領導的「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資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時期陳主持的中共特委會會議原始記錄尤其珍貴;近代史所則利用上述資料主編第四卷(1927–1942)。這四卷資料都是綜合性的,包括陳獨秀未發表過的論著、有關各種檔案資料、親友回憶錄和各方評論等,準備交與中央直屬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書籍出版單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質疑,有的直接為其辯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接着又運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最高權威刊物《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1984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然而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1]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被迫結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運用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來說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台。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納會費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1994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錄的是關於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1920年創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進行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史太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1979年,我40歲。在十年「文革」和它的前身「四清」運動中耗費了一生中最寶貴的青春年華後,由一個大學的政治教員,茫然地跨進了一個藏龍臥虎之地——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進行中國革命史研究。中科院近代史所位於北京王府井大街東廠胡同一號,曾是明代特務機關、北洋政府黎元洪大總統宅第、學術大師胡適的住宅。對於自己學識水準能否勝任近代史研究最高機構的任務,我心中一點也沒有數。
然而,我是一個幸運者。近代史所革命史研究室的領導人,是延安「小八路」出身、性格開朗、熱情提攜後人的史洛明女士。「文革」中,她看到那些過去親密無間的戰友,一夜之間翻臉不認人,都被咬得遍體鱗傷,而她自己,非但不承認莫須有的罪名,也決不捏造罪名陷害別人。她為此吃盡了苦頭,傷透了心,有點「看破紅塵」的心緒,故而要求調到研究所來,清靜地研究一點歷史,了卻餘生。巧的是,她的安徽老家,七拐八彎,與陳獨秀還有點遠親關係。幾十年來她在黨內總聽到陳獨秀是「右傾機會主義」、「漢奸」、「叛徒」、「反革命」,但又始終拿不出一條證據來,心中一直疑惑不解,現在想弄弄明白。她說︰「小唐,你就與我一起做陳獨秀的研究吧!先從他的後期着手。」——因為,上述陳獨秀的罪名,都發生在他的後期。
作此研究,談何容易!陳獨秀案是在極其複雜的年代中黨派鬥爭的產物,被中共中央數個決議所鐵定。陳獨秀與托派結合後成立了中共反對派組織,也即中共到目前為止唯一的反對黨。因此,他的後期歷史資料是嚴厲封存的絕密檔案。別說學者,就是高官,沒有特殊的理由和審批手續也是不能查閱的。陳獨秀研究成了禁區,能發表的,只能是批判,批判,再批判⋯⋯老一代史學家中,個別有一點正義感的人如孫思白、丁守和、彭明、林茂生等,在論述「五四」新文化運動時客觀評價過陳在這個運動中的作用,就立即遭到批判、打擊和迫害。
機遇終於出現了。當我們開始收集陳獨秀後期資料時,「文革」剛結束不久,各項工作包括各地的檔案管理還未完全走上正軌。我們花了約一年時間,在北京、上海、南京收集到相當完整的陳獨秀後期和中國托派的系統資料,猶如發現了一座儲藏量豐富的金礦。系統到甚麼程度?可以說:從1929年被開除到1942年去世前,陳與中共中央鬥爭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1929年轉向中國托派及1931年被選為托派中央書記後,陳與國民黨、共產黨及托派內部極左派鬥爭及呼籲聯合抗日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和書信;中國托派從1927年大革命失敗後在莫斯科誕生,到1952年在大陸被取締時的幾乎全部文件、文章、書信。
為甚麼這些資料會如此全面而系統?中國托派產生及陳獨秀加入後,組織和活動中心一直在上海,由此向全國輻射。其活動完全歸結為一張機關報上的宣傳及散發小冊子和傳單,由於地下鬥爭的惡劣環境,這些材料絕大多數是手刻油印件,甚至是用印藍紙手工複印或手寫的原稿。1949年,大陸政權易手,除少數托派領導人把組織轉到境外之外,絕大多數托派分子轉入地下,繼續收藏着這些資料。中共忙於對付國民黨殘餘勢力及整頓經濟,托派分子以為可以繼續活動,因此又活躍了起來。沒料想,其組織與活動完全被中共掌握。1952年12月22日夜,依照毛澤東的命令,全國統一行動,對大陸的托派分子及其同情者實行大逮捕、大抄家。中共繼而在全國掀起肅托運動,把散落在民間及所有圖書館中的有關陳獨秀和托派的資料全部徹底地清查出來,經過整理,加以封存。
獲得這批後期歷史資料後,為貫徹資料共用和推動全國陳獨秀全面研究的原則,我們於是聯絡安徽、上海、北京三地對陳獨秀有研究的學者收集、研究並最終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共分四卷。安徽學者主編第一卷(1879–1915),即陳獨秀早期資料,陸續收集到《江州陳氏義門宗譜》、迄今發現的陳獨秀最早的著作《揚子江形勢略論》、早期創辦的刊物《安徽俗話報》等;北京學者主編第二卷(1915–1920),收集到陳獨秀在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時期出版的《廣東群報》,記錄了陳的大量言論和活動;上海學者主編第三卷(1921–1927),收集到陳獨秀領導的「五卅運動」和「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暴動」資料,其中在上海「三暴」時期陳主持的中共特委會會議原始記錄尤其珍貴;近代史所則利用上述資料主編第四卷(1927–1942)。這四卷資料都是綜合性的,包括陳獨秀未發表過的論著、有關各種檔案資料、親友回憶錄和各方評論等,準備交與中央直屬的,中國最重要的政治書籍出版單位人民出版社出版。
與此同時,不少學者衝破阻力,紛紛發表文章。有的對陳獨秀的誣名提出質疑,有的直接為其辯誣。筆者也在中國革命博物館刊物《黨史研究資料》(1980年第16期)發表了處女作《舊案新考——關於王明、康生誣陷陳獨秀為「漢奸」問題》。接着又運用整理編輯《陳獨秀研究資料》第四卷的材料和心得,寫了三萬多字的論文《試論陳獨秀與托派問題》,發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史學界最高權威刊物《歷史研究》(1981年第6期)上。該文批駁了陳與托派相結合是「走向反革命」的傳統觀點,獲得該雜誌優秀論文獎。
北京的政局如初春的天氣,乍暖還寒。1984年初,《陳獨秀研究資料》四卷初稿陸續編出,第一卷已經被人民出版社審閱通過。然而此前,發生了「清除精神污染」運動,「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不能成立的觀點,被定為學術領域「精神污染」的主要表現。代表中央主管人民出版社的胡喬木親自到社嚴厲訓斥︰「你們好大膽,竟敢出陳獨秀的文集!知道陳獨秀是甚麼人嗎?他是托派頭子!知道托派是甚麼東西嗎?托派是漢奸、反革命。」其實,這都是經過他這個主管大人審批的,現在卻倒打一耙。出版社負責人之一曾彥修是個硬骨頭,不服,向中央告了一狀,結果不了了之。與此同時,中共中央宣傳部發出13號文件,宣稱︰「近年有些刊物發表為陳獨秀錯誤辯護的文章⋯⋯這是很不妥當的。望告各有關刊物,此後嚴肅注意防止再發生同類事情。」並指出「不能為他被開除出黨和進行托派活動翻案」,[1]致使《陳獨秀研究資料》胎死腹中。
此前,我開始撰寫《陳獨秀傳(下冊)——從總書記到反對派》一書(此著為李新主編的革命史叢書之一,該書上冊已由叢書編委會成員之一任建樹先行接手),在「清理精神污染」運動被迫結束以後得以面世。但由於形格勢禁,為了能夠順利出版,該書在觀點上未能有較大突破,資料運用也不能不有所顧忌。儘管如此,此書還是受到歡迎,在上海圖書館的借閱率好幾年名列前茅。而且,由於陳後期檔案資料很快又被查封,並轉移到北京中央檔案館,不讓學者研究使用,這本書成了所有研究陳獨秀後期歷史的學者必閱的「工具書」。
就在「陳傳」下冊出版前夕的1989年3月,我與十幾位來自全國各地的陳研學者,在北京秘密成立「陳獨秀研究會」,決心把對陳的研究與「正名」工作推向前進。「平反」二字對當局來說太敏感,故用「正名」以減少阻力。1992年,我出任該會秘書長(後來改選為執行會長)。次年10月,我為該會創辦並主編會刊《陳獨秀研究動態》,為全國陳研學者提供一個交換新資料、新觀點的平台。由於不斷被宣佈為非法刊物,《陳獨秀研究動態》曾改名《簡報》、《信息與服務》、《陳獨秀與中國》,贈閱交納會費者,曾發送近千份。同時由我們組織,兩年一次,逢陳獨秀生日和忌日輪流在其各個歷史活動地舉行全國性的學術研究討論會,交流學術成果,並推動為陳獨秀正名的運動向縱深發展。我們陸續把「十宗罪」推倒了九宗,只剩下「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由於缺乏有力的資料,無法撼動。
真所謂「山窮水盡疑無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正在這個時候,1994年由俄羅斯科學院現代歷史文獻保管與研究中心同德國柏林大學東亞研究會聯合編輯的大型系列檔案文件集《聯共(布)、共產國際與中國》(1920–1949)由中央黨史研究室組織有關專家陸續翻譯出版。首先出版的6卷,正好收錄的是關於陳獨秀在共產國際幫助下從1920年創建中共,到1927年大革命失敗的幾乎全部絕密文件。從中,人們可以十分清楚和詳細地看到,陳獨秀怎樣在共產國際代表的指導下創建中共,又怎樣被迫加入共產國際成為它的一個支部;怎樣被迫接受國際命令加入國民黨實行黨內合作;怎樣一次又一次地被迫放棄獨立發展中共、獨立進行革命的主張,接受史太林為首的聯共中央和共產國際的訓令向國民黨讓步、屈服,從而成為國民黨進行北伐戰爭的附庸和助手;以及1927年4月至7月,國民黨怎樣把中共打入血泊中,史太林又是怎樣把失敗的罪責推到陳獨秀身上。所有這些,徹底地推翻了「陳獨秀右傾機會主義」。這項罪名,原來是史太林文過飾非,把陳獨秀當替罪羊的產物。
陈独秀全传 在线阅读:
第 1 页第 2 页第 3 页第 4 页第 5 页第 6 页第 7 页第 8 页第 9 页第 10 页第 11 页第 12 页第 13 页第 14 页第 15 页第 16 页第 17 页第 18 页第 19 页第 20 页第 21 页第 22 页第 23 页第 24 页第 25 页第 26 页第 27 页第 28 页第 29 页第 30 页
第 1 页第 2 页第 3 页第 4 页第 5 页第 6 页第 7 页第 8 页第 9 页第 10 页第 11 页第 12 页第 13 页第 14 页第 15 页第 16 页第 17 页第 18 页第 19 页第 20 页第 21 页第 22 页第 23 页第 24 页第 25 页第 26 页第 27 页第 28 页第 29 页第 30 页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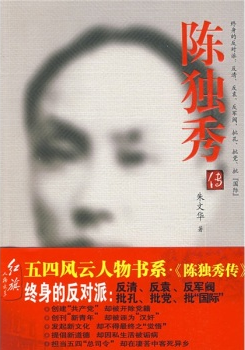 作者:朱文华(近代)
作者:朱文华(近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