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一九〇九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①。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②,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③。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因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④,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⑤。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⑥正象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象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1)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⑦,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一八七三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子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⑧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酉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⑨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⑩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1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12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13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14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土学位。
一八八二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15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16。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17;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I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这套《自传》丛书中有几位作者,他们在自己传记的篇首就担心接受这项任务会遇到极大的困难。我觉得和他们相比,我面临的困难更为艰巨;因为,这类文章我发表过不止一篇,从那些文章题目的性质来看,我个人经历的记述已经超过了通常所需要的,或者在有些情况下必需占有的篇幅。
我第一次介绍精神分析学的进展和内容,是一九〇九年在马萨诸塞州伍斯特市的克拉克大学,当时,我应邀参加了该校二十周年的校庆活动,并在那里作了五次讲演①。就在前不久、美国准备要出一本介绍二十世纪初有关情况的集子②,鉴于该书编者认识到精神分析学的重要性,打算专辟一章予以介绍,我又欣然为他们写了一篇内容相仿的文章。在这两次中间,我还发表过一篇名为《精神分析运动史》的论文,我在这里要讲的基本内容,其实在那篇文章中皆已有所论及。因此,为了避免前后不一,避免完全重复,我必须将主观态度和客观评价、个人生平和历史材料重新有机地结合起来,加以叙述③。
一八五六年五月六日,我出生在摩拉维亚一个名叫弗赖堡的小城镇里,那地方现在属于捷克斯洛伐克。我父母都是犹太人,我也保持着这一血统。我有理由相信,我的祖辈很早就在莱因河畔(科隆)定居生活;由于十四、十五世纪那里对犹太人大肆迫害,他们才背井离乡,向东逃难;到了十九世纪,他们又离开了立陶宛,穿过加西里亚,迁返德奥故地。我四岁时来到了维也纳,在那里完成了全部学业。在中学里④,我在班上连续七年名列前茅,并曾经享受到一些特别优待,几乎所有的课程都免试通过。那时候,家里生活非常拮据,但父亲对我选择职业一事,则始终主张由我自己去决定。无论是那时还是在晚年,我对医生这一职业并无特别的偏好⑤。倒是一种对人而不是对物的好奇心,使我改变了想法;可是,我那时还不懂,观察乃是满足这种好奇心的最好方式之一。我差不多从识字的时候起,便迷上了圣经故事,⑥正象我很晚才发现的那样,这对我的兴趣爱好具有长久的影响。我在学校里有位高年级的好友,后来成了一位颇有名气的政治家,在他强有力的影响下,我曾经萌生过象他那样去学习法律,从事社会活动的想法。那些年头,达尔文的学说是一个很热门的话题,这些理论使人们觉得,人类对世界的认识可望产生一个重大的飞跃,所以它把我深深地吸引住了;然而就在毕业离校前夕,在卡尔·布吕尔教授(Carl Brüh1)给我们上的—堂大课上,我听了他朗诵的歌德描写大自然的优美动人的散文⑦,于是决定攻读医学专业。
一八七三年我刚进大学不久,就觉得有些失望。我先是发现,周围人满以为我会因为自己是犹太人而感到自卑和疏远。我绝对不会这么认为。我从来不知道为什么要对自己的出身或者如人们所说的“种族”感到羞耻。于是,我就在这样不受欢迎的情况下置身子大学这个社圈,并没有感到太多的遗憾;我认为,对于一个积极的进取者来说,再怎么排挤,他还是能在社会的某个角落,寻得一块立身之地。但话又要说回来,在大学里的这些最初感受对我的影响,后来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年纪轻轻便已处于反对派的地位,尝到了被“紧密团结的大多数”⑧压制的命运。这为我以后的独立判断力的形成,多少打下了一些基础。
除此之外,在大学的头几年里,我还发现,自己以前求知心切,曾同时涉足多门学科,但由于天赋中的某些特性和局限,使我难以在其中大部分领域有所作为。这时,我才深深领悟到靡菲斯特告诫的真谛:
你不用为学问东奔酉忙,
每个人只能学习他所能学到的东西。⑨
我终于在思斯特·布吕克⑩的生理实验室里找到了归宿、得到了满足,结识了我所敬慕并引为楷模的师友:伟大的布吕克本人,他的助手西格蒙德·埃克斯纳11和思斯特·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12能与后面这位很有天赋的弗莱施尔·冯·马克索夫结为好友,我感到不胜荣幸。13布吕克把一个神经系统组织学方面的问题交我研究;我出色地完成了这一任务,并且独立地将这项工作推进了一步。从一八七六年到一八八二年间,除了几次短暂的停歇,我始终在生理实验室工作,那时一般都认为,我已被确定替补将空缺的助教位置。14我对医学的各个领域,除了精神病学以外,一概不感兴趣。由于自己放松了医学方面的研究工作,所以直到一八八一年,我才得到了多少有点来迟的医学博土学位。
一八八二年对我来说是个转折点,那—年尊师布吕克见我经济上有困难,认为我父亲不该在我身上破费大量钱财,他极力劝我放弃理论性工作。我听从了他的劝告,离开了生理实验室,来到维也纳总医院15当了一名“临床实习医师”。不久,我又升任住院医师,在各个科室工作,并有半年多时间跟从梅涅特16。对于梅涅特的工作及其人格,我早在大学时代就已有了颇深的印象。
虽然工作变了,但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依然守着自己最初开创的路子。以前布吕克交给我的课题,是研究一种属于最低级鱼类(幼态八目鳗Ammocoetes PetromyZon)的脊髓17;后来我的工作转到人的中枢神经系统方面。就在那时,弗赖西希(Flechsig)发现了神经纤维髓鞘形成的非共生性,这一发现清楚地揭示了髓鞘束产生的复杂过程。我一开始就选择延髓(medulla obIongata)作为一个并且是唯一的研究课题,这正是我工作延续发展的又一标志。在大学的前几年,我搞研究的特点是题大面广,层层铺开,这时已经大为不同了,我开始集中力量专攻一个课题或难点。以后我始终坚持这种方式,为此常常招来以偏概全的指责。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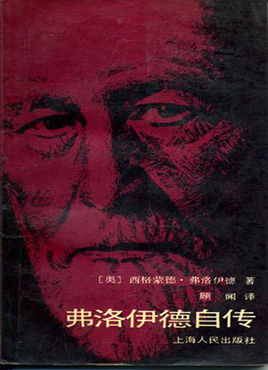 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维也纳)
作者: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维也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