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参加完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银行家例会,搭乘瑞士航空128次航班飞返华盛顿。正当我在座舱内踱步的时候,护送我出行海外的卫士长鲍勃•爱格牛在过道里把我拦下了。鲍勃是前秘密特工,为人友善但话语不多。此刻,他看上去神情严峻。“主席先生,”他低声说道,“机长要在前头见您。两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我一定满脸疑狐,因为他加了句“我不是在开玩笑。”
驾驶舱内,机长神色惶然。他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一桩针对我国的可怕攻击——有几架民航飞机遭到劫持,其中两架撞进世贸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下落不明。他所知道的就这些了,他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道。我们要飞回苏黎士,但他不会向其他乘客广播真实原因。
“我们非返航不可吗?”我问道,“可以降落在加拿大吗?”他说不可以,他接到的命令是折返苏黎士。
我返回座位,机长则发布广播说空中交通管制要求我们飞回苏黎士。座位上的电话立刻就被打爆,我无法和地面取得联系。那个周末和我同在瑞士的美联储同事们,都已经上了别的航班。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态进展,无计可施,只好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东想西想。我望向窗外,随身携带的工作、成堆的备忘录和经济报告,统统被我丢在包中不理:这些袭击会不会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幕呢?
我最先牵挂的是我的妻子安德莉娅,她是NBC电视台驻华盛顿的首席外事记者。令人宽慰的是她人不在纽约(译者注:NBC电视台总部在纽约),而且当天她也没有计划采访五角大楼。我想她应该在华盛顿城中的NBC分台里,正忙碌着报道新闻。所以我不用太担心,我安慰自已……但是,万一她在最后关头,临时前往五角大楼采访某位将军呢?
我担心美联储的同事们,他们和家人都安全吗?美联储职员一定正忙着应对危机。此次袭击——自珍珠港事件以来首次发生在美国本土——将陷国家于混乱,我需要凝神思考的问题是:经济会因此元气大伤吗?
显然,种种经济危机呼之欲出。最坏的情形便是金融系统崩溃,我想这倒不太可能发生。美联储管理的电子支付系统每日调度的资金和证券高达4万亿美元,在美国所有银行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银行间互相转账。
我们向来认为:如果存心破坏美国经济,只要搞掉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了。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资金实物转移,而商业将局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全国经济活动水平将会一落千丈。
在冷战期间,美联储为金融系统赖以运行的通信和计算机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备用系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我们有花样繁多的安全措施,比如,把某个美联储银行的数据备份在数百英里外的另一家美联储银行里,或者某个遥远的地方。万一发生核攻击,我们可以启动备用系统并在无核辐射区迅速运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将在当天启用的正是这样一个备用系统。我相信他和我们同事定会采取必要手段来保证世界美元体系继续运行。
然而,虽有可能,但我并不认为劫机者矢志摧毁金融系统实体。这更有可能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性暴力活动,就象早在8年前世贸中心车库里的炸弹事件一样。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由这类攻击所带来的恐慌——特别是还有攻击将不断袭来的情形之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体里,劳动分工环环相扣,人们必须不停地互相交换产品和服务,没了商品交换,所有家庭都得完蛋。如果人们退出日常经济活动——投资者狂抛股票,商人远离交易,老百姓呆在家里害怕去购物中心遭遇自杀炸弹——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此种心理将导致大众恐慌和经济衰退。象我们正在经受的这种惊骇是可以引起经济活动偃旗息鼓大幅萎缩的。祸不单行,诚非虚言。
飞机远在空中尚未落地,我就已认定世界要发生我还不能说清道明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从冷战后十年来怀揣着的良好自我感觉已然破灭。
我们终于在当时时间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刚刚过午后抵达苏黎士。瑞士银行官员接我下飞机,拥着我进入候机厅的贵宾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播放世贸双塔倒塌以及五角大楼起火的录像,我谢绝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那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揣测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其中一定有我认识的人。我不想看到毁灭,我只想要一部打得通的电话。
我终于在晚上9点钟之前几分钟打通安德莉娅的手机,听到她的声音,我大松一口气。我们彼此确认对方安然无恙之后,她说她得赶紧挂机:她正在值班,马上要接着播报当天事件的最新消息。我说:“快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她当时一只耳朵贴着手机,另一只耳朵里戴着耳塞,身在纽约的特别事件制片人在里面几乎喊起来了:“安德莉娅,汤姆·布洛考要和你连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她只来得及崩出半句“听着!”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开着的手机放在大腿上,对着摄像机开始播报。就在那当儿,我一字不差地听到了全国人民听到的直播新闻——失踪的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我才打通电话,联系上正在美联储的罗杰·弗格森。我们把危机处置预案快速地过了一遍,不出我所料,一切都在他的良好掌控之中。此时,所有飞往美国的民航班机都已停飞,于是,我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德,请求提供返回华盛顿的交通工具。末了,我在私人保镖护卫下,返回酒店睡会儿觉,同时等待指示。
黎明时分,我再次登机,这一回坐到一架美国空军KC-10加油机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往常飞行于大西洋上空给各种飞机加油。舱内气氛凝重。“您怎么也想不到,”机长说,“听!”我把耳朵靠近头戴式耳机,但除了静电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正常情况下,大西洋上空充满无线电通话,”他解释道,“现在的静默极其怪异。”显然,机外什么人也没有。
当我们飞临东海岸进入合众国神圣领空的时候,两架F-16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机长获准飞越曼哈顿南端上空——原先世贸双塔所在地已是烟雾腾腾的废墟。数十年来,我的办公地点离那里不过数个街区而已。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天天眼看着世贸双塔拔地而起。如今,从3万5千英尺俯瞰,它们那冒烟的残骸成了纽约最醒目的地标。
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2001年9月11日下午,我参加完在瑞士举行的国际银行家例会,搭乘瑞士航空128次航班飞返华盛顿。正当我在座舱内踱步的时候,护送我出行海外的卫士长鲍勃•爱格牛在过道里把我拦下了。鲍勃是前秘密特工,为人友善但话语不多。此刻,他看上去神情严峻。“主席先生,”他低声说道,“机长要在前头见您。两架飞机撞了世贸中心。”我一定满脸疑狐,因为他加了句“我不是在开玩笑。”
驾驶舱内,机长神色惶然。他告诉我们刚刚发生一桩针对我国的可怕攻击——有几架民航飞机遭到劫持,其中两架撞进世贸中心,一架撞上五角大楼,还有一架下落不明。他所知道的就这些了,他用略带口音的英语说道。我们要飞回苏黎士,但他不会向其他乘客广播真实原因。
“我们非返航不可吗?”我问道,“可以降落在加拿大吗?”他说不可以,他接到的命令是折返苏黎士。
我返回座位,机长则发布广播说空中交通管制要求我们飞回苏黎士。座位上的电话立刻就被打爆,我无法和地面取得联系。那个周末和我同在瑞士的美联储同事们,都已经上了别的航班。我没有办法了解事态进展,无计可施,只好在接下来的三个半小时里东想西想。我望向窗外,随身携带的工作、成堆的备忘录和经济报告,统统被我丢在包中不理:这些袭击会不会是一个更大阴谋的序幕呢?
我最先牵挂的是我的妻子安德莉娅,她是NBC电视台驻华盛顿的首席外事记者。令人宽慰的是她人不在纽约(译者注:NBC电视台总部在纽约),而且当天她也没有计划采访五角大楼。我想她应该在华盛顿城中的NBC分台里,正忙碌着报道新闻。所以我不用太担心,我安慰自已……但是,万一她在最后关头,临时前往五角大楼采访某位将军呢?
我担心美联储的同事们,他们和家人都安全吗?美联储职员一定正忙着应对危机。此次袭击——自珍珠港事件以来首次发生在美国本土——将陷国家于混乱,我需要凝神思考的问题是:经济会因此元气大伤吗?
显然,种种经济危机呼之欲出。最坏的情形便是金融系统崩溃,我想这倒不太可能发生。美联储管理的电子支付系统每日调度的资金和证券高达4万亿美元,在美国所有银行和世界其它地方的大多数银行间互相转账。
我们向来认为:如果存心破坏美国经济,只要搞掉电子支付系统就可以了。银行将不得不回到低效率的资金实物转移,而商业将局限于物物交换和欠据欠条。全国经济活动水平将会一落千丈。
在冷战期间,美联储为金融系统赖以运行的通信和计算机设施建立了庞大的备用系统,以应对可能发生的核打击。我们有花样繁多的安全措施,比如,把某个美联储银行的数据备份在数百英里外的另一家美联储银行里,或者某个遥远的地方。万一发生核攻击,我们可以启动备用系统并在无核辐射区迅速运行。美联储副主席罗杰•弗格森将在当天启用的正是这样一个备用系统。我相信他和我们同事定会采取必要手段来保证世界美元体系继续运行。
然而,虽有可能,但我并不认为劫机者矢志摧毁金融系统实体。这更有可能是一次反对资本主义美国的象征性暴力活动,就象早在8年前世贸中心车库里的炸弹事件一样。真正令我担心的是由这类攻击所带来的恐慌——特别是还有攻击将不断袭来的情形之下。象我们这样复杂的经济体里,劳动分工环环相扣,人们必须不停地互相交换产品和服务,没了商品交换,所有家庭都得完蛋。如果人们退出日常经济活动——投资者狂抛股票,商人远离交易,老百姓呆在家里害怕去购物中心遭遇自杀炸弹——就会出现滚雪球效应。此种心理将导致大众恐慌和经济衰退。象我们正在经受的这种惊骇是可以引起经济活动偃旗息鼓大幅萎缩的。祸不单行,诚非虚言。
飞机远在空中尚未落地,我就已认定世界要发生我还不能说清道明的变化。我们美国人从冷战后十年来怀揣着的良好自我感觉已然破灭。
我们终于在当时时间晚上8点半——美国时间刚刚过午后抵达苏黎士。瑞士银行官员接我下飞机,拥着我进入候机厅的贵宾室。他们表示可以为我播放世贸双塔倒塌以及五角大楼起火的录像,我谢绝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世贸中心附近工作,那里有我的朋友和熟人。我揣测伤亡人数是惊人的,其中一定有我认识的人。我不想看到毁灭,我只想要一部打得通的电话。
我终于在晚上9点钟之前几分钟打通安德莉娅的手机,听到她的声音,我大松一口气。我们彼此确认对方安然无恙之后,她说她得赶紧挂机:她正在值班,马上要接着播报当天事件的最新消息。我说:“快跟我说说那边的情况吧。”
她当时一只耳朵贴着手机,另一只耳朵里戴着耳塞,身在纽约的特别事件制片人在里面几乎喊起来了:“安德莉娅,汤姆·布洛考要和你连线了!你准备好了吗?”她只来得及崩出半句“听着!”说时迟,那时快,她把开着的手机放在大腿上,对着摄像机开始播报。就在那当儿,我一字不差地听到了全国人民听到的直播新闻——失踪的美国航空93号航班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
然后,我才打通电话,联系上正在美联储的罗杰·弗格森。我们把危机处置预案快速地过了一遍,不出我所料,一切都在他的良好掌控之中。此时,所有飞往美国的民航班机都已停飞,于是,我打电话给白宫办公室主任安迪·卡德,请求提供返回华盛顿的交通工具。末了,我在私人保镖护卫下,返回酒店睡会儿觉,同时等待指示。
黎明时分,我再次登机,这一回坐到一架美国空军KC-10加油机的驾驶舱内。机组人员往常飞行于大西洋上空给各种飞机加油。舱内气氛凝重。“您怎么也想不到,”机长说,“听!”我把耳朵靠近头戴式耳机,但除了静电声外什么也没有听到。“正常情况下,大西洋上空充满无线电通话,”他解释道,“现在的静默极其怪异。”显然,机外什么人也没有。
当我们飞临东海岸进入合众国神圣领空的时候,两架F-16战斗机飞过来为我们护航。机长获准飞越曼哈顿南端上空——原先世贸双塔所在地已是烟雾腾腾的废墟。数十年来,我的办公地点离那里不过数个街区而已。60年代末,70年代初,我一天天眼看着世贸双塔拔地而起。如今,从3万5千英尺俯瞰,它们那冒烟的残骸成了纽约最醒目的地标。
当天下午,我在一名警察护送下,穿过路障重重的街道,驱车直抵美联储,随即投入工作。
电子资金大多流动良好,只是由于民航停飞,老式支票的传输和承兑出现延误。那是个技术问题——一个严重问题,不过,全体职员和各个美联储银行完全有能力给各个商业银行临时追加额外信贷。
接下来的日子里,我大部分时间都在观察和聆听,寻找灾难性经济大衰退的征兆。911之前七个月,经济一直轻度衰退,还未摆脱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影响。不过,情况开始出现转机。此前,我们迅速持续降低利率,市场开始趋于稳定。到了8月底,公众关注点已经从经济转向加州国会议员加里·康迪特,该议员的几则声明闪烁其词,事关年轻女子失踪案,完全占据晚间新闻,安德莉娅没有任何具有全球意义的新闻可供报道。我记得当时头脑里闪过一个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的念头——如果电视新闻大多集中在国内桃色事件上,那么这个世界一定状况良好。而在美联储内部,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到底该降多少。
911之后,来自各个美联储银行源源不断的报告和统计数据,却呈现出另一回事。美联储系统由分布于全国各地的12家银行组成。每一家美联储银行贷款给本地区的各家银行并加以监管。美联储银行也是美国经济的窗口——银行官员和职员与本辖区的银行家及商人保持密切联系,他们收集到的订单和销售信息,胜过每月公布的官方数据。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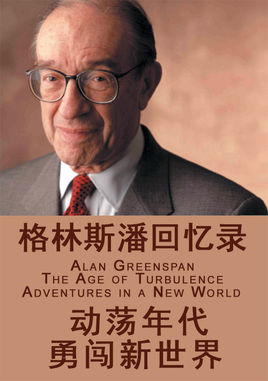 作者:艾伦·格林斯潘(美)
作者:艾伦·格林斯潘(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