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古帝国史的研究,需要涉及太广袤的地域、太漫长的时间段、太多语种的文献资料,而漠北草原深处的游牧政治与文化所留下的详实记载又太过稀少,这就迫使绝大多数学者只好根据自身的兴趣与擅长,而把各自的学术探索聚焦于被进一步分割开来的诸多狭小而专门的分支领域。在这种情况下,一般读者想要通过直接阅读一大堆过分专精深奥、过分细部化的专业性著述,从而求得对这段历史的比较深入通贯的理解,也就变得格外困难了。或许正因为如此,在近代以来的学术界,曾出现过不少大手笔的蒙古史名家;他们力图在创造性地对各种史料及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清理、吸纳和消化的基础上,整体地、准确地展现出蒙古民族历史变迁的宏伟图景。瑞典人多桑的《蒙古史》、英国人霍渥斯的五卷本《蒙古人史》、法国人格鲁塞的《蒙古帝国史》,不但赢得了大量非专业的读者,而且至今仍是从事相关课题的专业工作者必须备置案头的重要参考书籍。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十三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收采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藉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穿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涵意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被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本书作者对此解释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十分贴切的说明。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者勒篾为什么要那样做。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经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
“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作者被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做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帖克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却不能算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别克帖儿并不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
就其总的写作宗旨而言,刻下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书,与上面提到的那几部名著可以说略有相似之处。为了读懂《蒙古秘史》这部用汉字记音方式传承下来的十三世纪的伟大蒙古史诗,作者和他的同事们检阅了“十二种语言的最重要的第一手和第二手”文献资料。本书收采史料的范围,包括俄罗斯的《诺夫哥罗德编年史》、撰写于蒙古征服时代的珍贵的叙利亚编年史《巴尔赫布勒斯》,以及穆斯林世界的伊本阿昔儿《编年史》、术兹札尼书等。虽然还不能说是“上穷碧落下黄泉”,但是作者在发掘史料和广泛参照前人研究成果方面的不倦努力,确实已做到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地步。不过,它不同于多桑、格鲁塞等人著述的地方也很明显。作者念念不忘的,是从自己特定的专业视角出发,对蒙古帝国兴亡的历史进程作出某种带有人类学性质的阐释;他尤其关注的是这样一个问题,即蒙古对欧亚旧大陆的征服,给予紧接着就跨入近现代门槛的人类社会带来了一些什么样的积极影响?如果要用一句话来概括这本书的独特之处,那么我们不妨称之为对蒙古帝国史的文化人类学解读。
现在让我举一个例子,说明作者是如何凭藉着人类学视角的观照来窥穿某些历史事件背后的文化涵意的。在阔亦田击败“古儿汗”札木合所纠结的十一部联盟后,成吉思汗的军队却在接下来追击溃部的战斗中被打散了。他颈脉被创,血流不止,昏迷了半夜才醒过来。这时他只觉得全身的血已经流尽,口里干渴难忍。于是陪伴在他身边的一名勇士者勒篾便只身闯入对面的敌营,去为成吉思汗找寻蒙古人爱喝的马奶子。《蒙古秘史》的汉文旁注在这里写道:“者勒篾帽、靴、衣服自的行都行脱着,独裤有的赤裸,相抗拒着立着敌人里面走着”(按此语大意为:者勒篾脱去自己的帽子、靴子和上下衣服,光身只穿着内裤,朝驻扎在对面的敌方营垒里走去)。他虽然没有找到马奶,可还是从敌营中带回来一桶马酪,使成吉思汗从重伤中获得稍许的恢复。这段故事是每个研习蒙古史的人都熟知的。但是也许此前还没有人认真想过,为什么者勒篾在闯进敌营时需要裸露着自己的身子?本书作者对此解释说:“对蒙古人而言,当众裸体是非常失身份的,但要是有一位泰亦赤兀惕人看到有人夜间裸体穿越营地,他们或许会以为是自己人在起床解手。出于礼貌,担心羞辱到自己的勇士,他们或许会把脸转过去”。看来这确是一个身处险境的陌生人避免别人注视自己的好办法!一个非常真实的细节就这样获得了十分贴切的说明。
也许会有人以为,者勒篾为何赤裸着身子进入敌营,这本身并不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所以原不必如此认真地对它刨根问底。但是他们没有想到,人类以往的历史已一去不复返;想研究历史的人,如果不能够从五花八门的片断资料中找回对过去时代的触摸肌肤般的感知和理解,也就无法真切地“看见”他想追寻的那段历史。“不拘细节”或以“不拘细节”而沾沾自喜的人,起码是不能成为像样的历史学家的!
当然,蒙古帝国时代的历史资料并没有直接提到过者勒篾为什么要那样做。那么作者是从哪里获得这项有关知识的呢?他曾经广泛地游历过古代蒙古人所到之处,用他自己的话说:“我穿越俄罗斯、中国、蒙古、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去追寻蒙古人的足迹。我用了一个夏天的时间沿着突厥部落在古代迁移的道路行走”;“然后,大致遵循马可·波罗的海上航线,我围绕这个古帝国一圈,从华南到越南,穿越马六甲海峡,到达印度及波斯湾的阿拉伯国家,最后抵达威尼斯”。不过,光靠这种走马看花式的旅行考察,断然还无法写得出像现在这样的一本书;尽管连作者自己对此也一度估计不足。1998年,他再次去到蒙古。出乎他本人意料的是,原先是为结束本课题研究而安排的这次“收尾式的短暂旅行”,却变成了另一项长达五年之久的研究。这位文化人类学家如今才真正找回了自己的感觉:这是长期与“一群不断更换的蒙古学生、学者、当地牧民以及养马人”一起生活和工作带给他的最大收益。对于自己的这一大群合作者,他充满敬意地写道:
“他们之间总是非常激烈地进行着争论,试图回答我正在探讨的问题。他们的判断和答案总是比我的好,而且他们经常会提出一些我从未想到过的问题。他们了解牧人的想法,尽管在陌生的地域,也可以很容易地确定他们的祖先将会在哪里扎营,将会按哪个方向行进。他们很容易判别出哪个地方蚊虫多,因而不适合夏季驻宿,哪个地方太过暴露,故不适宜冬季下营。更重要的是,他们乐意验证自己的想法,例如,弄清楚骑着一匹马从一个地点到另一个地点究竟需要多少时间,或对不同地方的土壤和牧草进行比较,弄明白马蹄击地的回声因而会如何不同。他们知道在冻结的江面上,需要多厚的冰层才能让人骑着马走过,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在上面步行,或者必须破冰涉水而过”。
人类学家总是力图从被研究对象自身的经验、思想及其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出发,去寻找对于他们行为的社会和文化解释。所以作者反复强调,《蒙古秘史》的解读,必须建立在“对十三世纪的蒙古文化和地理”具有“深厚知识”的基础上。他说,除非把文献读回到“事件发生的实际地点上去”,现代的人们将难以理解史诗叙事的来龙去脉和它作为一部传记史的意义。散见在本书中的诸多新鲜见解,颇多得益于作者被所全心全意地予以坚持的这一特殊学术取向。
书中另有一个例子也很值得提出来加以讨论。在他的父亲也速该被塔塔尔人毒死、少年成吉思汗(当时叫做铁木真)所在的孛儿只斤家族被他们的近亲泰亦赤兀惕部落驱逐出去以后,铁木真在非常孤立无援的生存环境中与他的同父异母兄弟别克帖儿发生了冲突。结果他残酷地杀害了别克帖儿。《蒙古秘史》在叙及两人不和时,仅提到别克帖儿曾先后夺走过铁木真捕得的一只云雀和一尾咸水鱼。在一个亟须同心协力以应付危机的时候,为一点小事而害死了自己的亲属,铁木真的此种行为确实有些令人难以理解。于是本书作者想起了在古代蒙古人中流行的“收继婚”习俗,即在一家之长死去以后,由其成年的长房长子继承家长地位,后者并有权利将其生母以外的父亲其他庶妻收娶为自己的妻子。作者写道,在也速该被毒死之后,别帖克儿“渐渐地开始行使最长男性成员的特权”。不仅如此,“别克帖儿长大后,诃额仑(按、此即铁木真的母亲)将接受他作为丈夫。因此,无论在哪个方面,别克帖儿都是一家之主。然而,铁木真决不能忍受与别克帖儿共处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铁木真的失常行动由此似乎获得了相当圆满的解释。
不过,作者的这次尝试却不能算是成功的。这里的关键在于,别克帖儿并不具备长房长子的身份!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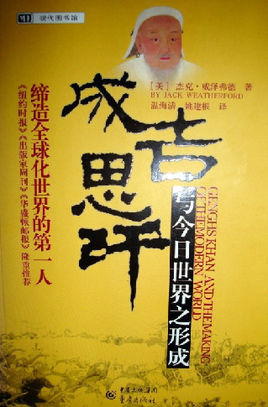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 (美)
作者:杰克·威泽弗德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