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上个周末,我的忘年朋友,也是我的小学和中学的学长周惠民先生,从西雅图打电话来,希望将他多年前就已经翻译完成,而至今未能在大陆出版的《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译稿电子版放到《二闲堂》上,以飨读者。我当然是求之不得。
惠民先生在英译上的造诣和学养我是知道的。大陆“开放”之初,惠民先生就应马海德医生之邀承担国际会议同声传译的工作。这些年来,他陆续出版了多部重要英语著作的译本,长期承担大陆学术杂志的英文审译。
此处首先谈到惠民先生的英译能力,是想说明由惠民先生翻译《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一书是十分恰当的人选。五年前国内一个出版商社,邀请周先生将此书译出,由他来出版。该商社告诉周先生,说曾与当年司徒雷登在华时代的秘书傅泾波先生的女公子,现居美国的傅铎若先生谈论了此事。周先生就开始了工作。
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五日,司徒雷登的回忆录《在华五十年》(My Fifty Years in China—The Memoirs of John Leighton Stuart, Missionary and Ambassador)由美国纽约兰登出版社正式出版。二战以后担任过中国内战国共冲突调停人,并任美国国务卿的乔治·马歇尔和中国的学界祭酒胡适先生分别为该书作序。次日,台湾《大华晚报》即开始边请人翻译,边予以连载,并于同年十二月一日出版了中译本。一九五五年,香港求精出版社再次出版了由阎人峻翻译的司徒雷登回忆录。
然而在那个时代,中美关系,台海关系势同水火。当然更重要的是,毛泽东在解放军挥兵过江,打平天下的关键时刻,写过一篇奠定此后共产党政府与美国外交关系基础的文章,题目就是以司徒雷登的名字为名,叫作《别了,司徒雷登》。在这种情形之下,司徒雷登先生的这本自传丝毫没有可能与大陆的广大读者见面。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自七十年代中期中美关系解冻之后,大陆逐步接受和放宽境外史学文献的有限进入,司徒雷登自传的流入当属自然。然而那个时代,大陆并无版权意识,又有所谓“内部发行”的特殊发行渠道。于是在一九八二年四月,由北京出版社牵头,以内部发行的形式,出版了由程宗家翻译、刘雪芬校对的《在华五十年—司徒雷登回忆录》。值得注意的是,这本传记中仍然还有许多触犯当时政治禁忌的内容,所以在大陆发行的这本《司徒雷登回忆录》只是一部内容经过取舍的删节本,算不得“全本”。对于认真研究当年的历史,并对历史完整性有严格要求的读者来讲,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一九八二年大陆版《司徒雷登回忆录》并没有得到翻译版权的许可。当年或许情有可原,如今就登不得大雅之堂了。
既然惠民先生完全具备翻译《司徒雷登回忆录》的能力,又已经将全书翻译成功,版权也不是问题,那么按说这本众人翘首以望的汉译文本应该很快就可以与读者见面了。
其实不然。正像司徒雷登先生的骨灰迟迟不能安葬燕园一样,这本对于研究那个时代具有重要史料意义的司徒雷登回忆录完整译本至今也不能在国内出版,其中一波三折的故事还是听惠民先生本人来细说从头。
二、
那我就不妨来说说我读司徒雷登以外的故事罢。
最早知道司徒雷登当然是在我读初中的六十年代,这个人物的名字出现在我们的语文课本里面。课文的题目叫作《别了,司徒雷登》,文章的作者是毛泽东。说老实话,如今我已经全然记不得这篇课文的内容,只记得当初我的朦胧印象有二:其一,这个复姓“司徒”的人居然是个美国人;其二,这么好听的名字居然让外国人用掉了,可惜。
如此而已。
再次记起司徒雷登,是许多年之后的一九八六年。我从德国读书归来不久,当初在德国对我关照有加的汉学家韦莎彬太太到中国造访,我陪她到北大燕园会见考古系的教授。或许是考古系办公室面积逼仄,也或许是“外事活动”必须讲究门面,总之那次我们是在“临湖轩”与众教授会面。一杯清茶是那个时代的待客之道,如今记起来的是,考古系的严文明教授特别提到:这里原先是燕京大学时代司徒雷登先生的办公间。
这就让我不免想起与自己多少有些关联的两件事。
一九七二年,我自云南西双版纳回到京城,借住在景山东侧的沙滩后街五十五号大院,当时这里是已经被撤消了的人民教育出版社旧址。我在那里居住凡四年,度过一段闭门读书的时光,一九七六年“落实”了政策才搬走。在此之前,这里是北京大学的校本部和理学院,当然更早之前,这里还是乾隆皇帝的四公主府。顺便说一句,和嘉公主的驸马福隆安是大学士傅恒之子,而这傅家本姓富察,应该和也属富察氏的傅铎若先生还是本家。
自一九五三年院系合并运动以后,燕京大学撤消,北京大学搬去燕京校园,鸠占雀巢,人民教育出版社才从石驸马桥原址搬到这里。后来有父执辈的长者曾经是燕京的校友,每年的“五·四”都会到燕园参加“校庆”活动。事后我不免问问他们的感受。一次听到一位长者的话我记得最真:“咳!大娘的房子让给了二娘,还让大娘养的儿子到上房给二娘做寿,心情能是什么滋味?!”语虽刻薄,道理倒是也还浅显。
由燕园“临湖轩”让我记起的另外一件旧事是我的岳父说给我听的。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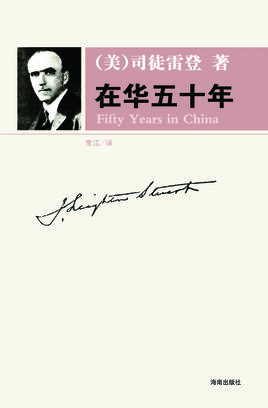 作者:司徒雷登(美)
作者:司徒雷登(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