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另一种生活。清早醒来,又是新的一天,清新拂面。晨光像轻纱,像耳畔的喁喁细语,轻抚着我。其余,只剩回忆。一切都搅成一团。昨天混同于更远的过去,真的混同于假的。剧院的灰尘,像梦醒似的消散了,在严酷的现实面前逃遁了。新出炉的面包,香气直窜三楼,从半开的窗户飘进房间里。很久以来,我忘了楼下有家面包房——忘了大家来这儿买面包。
这天,不同于其他日子。拉窗帘时,很久没遇到绳结而卡住。人容易逃避到习惯里,那里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安静得像乡下房子。今天,习惯变了,变得抽象起来。等着想知道到何处落脚,另找个位置。舍人情易习的习惯,而躲进孤独里——消失在拖长的“孤”字里,消失在听不见的“独”字里。
我虚飘飘的没有重量,怕消失得无影无踪,陶醉在广漠的空间里。怎样才能吸纳一切,变成一种蹦跳激荡的力?怎样才不至于散架,撕成碎片,化身亿万星星点点?隐在一个自由女子的身影里——有种妖术般异样的吸引力。我听到美人鱼迷人的声音召唤我去发现美,去发现伟大。我知道她想断送我,看到她脸上还流着冤死者失色的鲜血。我正想把这一切统统送去见鬼,但马上后悔说出了口,要知道魔鬼在谛听,等着咬我。魔鬼能为我的脆弱、我的怯懦而心软?真相是否已然隐去?我是否能借他人之眼来观看世界?
他是今天早晨走的,大软皮包里只装了几本书。他走下盘旋而下的楼梯。
要说走路的样子谁都没他好。两腿笔直,无可挑剔。为感觉到他的手恨不得他抽我两记耳光,让空气也唉唉叹息。我很想抓住他手,拧他手指,但他却碰不得,从头到脚都强直生硬。水银流泻着毒液。直挺挺死板板,他走下旋转楼梯。
根本没有热面包的香气,今晨也没人到面包房来。今天是礼拜天,迟早会到来的礼拜天,连鼻子窝在被子里也闻得出来。听到钟声四起,想象托盘里托出黄澄澄的新鲜牛角面包,小孩拉着气球跟狗跑差点把热茶打翻,想象速溶咖啡广告里穿长统袜的大腿,想象这是一个尽看电视的礼拜天。一股穿堂风,像条长蛇,钻进我身子。起居室还留着烟味,外套,羊毛衫,翻过来的脏袜子,摊得到处都是,临时凑成一顿菲薄晚餐的剩碗残碟,都罩在蓝灰色的晨雾里,像死人皮肤余温尚存;人要死了就顾不得临终表情,是什么样子就成什么样子。厨房的方砖,冷冰冰的。电话线盘缠一团,像螺丝卷似的。
赤身露体或几近一丝不挂,我记起曾头痛来着,这时直僵僵站着,不知从何开始,是先穿袜子--一碰地板就脏了--,还是烧开水泡茶,或者干脆出门,不刷牙也不梳头就上街,让头发梳齐、衣着考究、心情愉快的行人,领教领教我这副落拓相。我头发都打结了,用手抹抹平,曾看到有个醉汉就用胖手背这么压一压抿一抿的。
我两拳撑到袋底,让长裤完全往下坠,裤脚拖到地上,堆起几叠褶皱,贴边剐着石子路。裤裆下垂,侧影像立体派绘画,走路时摆动胯部,布料在屁股和大腿根都留下白印。裤腿里伸出的大靴子,像画脚没画好而画成大球模样。我从玻璃橱窗里瞄到自己的侧影。后景比较模糊,眼睛像高级相机镜头对光那样前后转动。上街脸不洗头不梳,很得意于自己这副脏模样。我没走远,知道没离开住处附近,很快往左拐进最近一条街,走成一个四边形的最后一边。迎着风,忍着饿,尚未朝食,肚子扁扁的。我要表明,人可以这样不修边幅,不顾惜自己,别人才不放在我眼里哪。身体不足道,饥饿感,女性美,都可置之不理。我要别人知道我这样是因为忙。
其实瞎忙而已,但瞎忙得高明,以致忘了寒冷,故意把脏头发贴在脑门上像条绷带。我要人家以为我病了,来可怜我。我把自己这形象映现在店家的橱窗里,相信至少有人在看我,相信我存在于天地间。饥饿会向人进行小小的讹诈,钳住我不放,使我面临这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生存呢,还是死亡。我愿存活而不食,眼看着消瘦下去,净化自己,冀能自新。
谁都不注意我。我想标榜自己的孤独,可是谁都不信,别人期待着看到一个能吃能喝身强体壮健步疾行的我,一个将身腰一束前额一扬令人人都转过脸来行注目礼的我。
这一企盼,以失败告终。很抱歉,我就是这么平凡不起眼。这时,我正走正方形的最后一条边,拐角就是我楼前的大门,隐在面包房的铺面后面。面包房今天关门。
真觉得饿了。
“他”的名字,可以叫于利安、马锡安或约安,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是眼前实在的生活还是另一种生活,他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也可能是外国人——最好是外国人,来自异域他乡,讲一种我能懂的语言。他是活着,或已呜呼,对我都无所谓,是他就行,只要是他。
我不说实话,因为我喜欢搞得神秘兮兮的,喜欢多少事尽在不言中。只有在沉默时,在独守秘密的房间里,我才感到快慰。这时,我自导自演,肆无忌惮,高兴起来无妨奸恶,工于心计,多情多恋——同时绝顶聪明。我把自己的故事冲淡,搞得模模糊糊的,东一段西一段,打乱时序,移花接木。因为我不相信有始有终,不相信有碰巧的事。即使混乱也有迹可寻,因为时间就是时间,而我一无所求。于是,瘦骨嶙峋还去其骨,一切都已在那里,用不到我去指指点点。让我以自己的方式去发疯,去求真,我只听命于内心的驱驰。这儿有个我不打算说的故事,因为跟千千万万其他故事一样。一切都是故事,一生的每分每秒都在讲述一个故事,一死还有什么回忆可言!我们不得已活出许多故事来,难道能都忘怀,只留下岁月的精华和泡沫?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是他?为什么相爱?为什么相妒?为什么不爱?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作恶,不论大恶小恶?我从这段禅语感到宽慰:“妙中自有更妙。众生皆有佛性,各具智慧与德性,而当局者迷,是误于妄念。”
具体到我,还能碰到什么事呢?日复一日,千篇一律。所以,常百无聊赖,脾气暴躁。我常烦躁,虽然没人说看到我“发脾气”——那是因为我太喜欢嫣然媚人,失望之余,便摆出一副苦相。事实上,我心头很忧伤,总是很忧伤。会唱歌,我就唱blues[忧丧曲],咧着嘴,挂着大颗大颗的眼泪,身子瘦损,拼命抽烟,喝过量的白酒、香槟或伏特加,潦倒粗疏,怨天尤人,陶醉在痛苦的旋涡里。
然而,生活做出了另一种安排。我的模样像十五岁,有个时期显得有点圆乎乎的,现在已不抽烟,睡得也早,酒就喜欢干红。但一直不明白,如此这般,是不是还是一种欺骗?选择,并不一定是折中,求得半拉儿满足,对失去的一切加倍渴望,是这样吧,时不时的?之后,一切又变了。说是要顺应人生,在精神振足的日子,可以提升到智慧、理性、历史的层面来认识。历史,在我看来,写的都是垂范后世的行为,逸出常规的非常事。有人指出,这里是一对模范夫妻,正直,高尚,没有花花事儿,没有斑斑污点。我却为高傲所苦。我那时并不很快活,因为我并不十分内向,并不内向到无需外求,无需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我的能耐。在情爱——真情的爱——与自我表现之间,无所适从。我之成为今日之我,是前因造成的后果:小时候,跟所有孩子一样,相信天主教行善的说法,人都是有罪的,造成别人的不幸我有责,应忏悔。我说谎,是怕神圣的惩罚,就是说,怕最后审判。我学做好人,变得懂事,爱整洁,每晚像洗内裤那样洗刷我的罪过,再也不想到作恶。我脚踏实地,布施穷人,天真得像花海里的鲜花,开在散发春天气息的绿草场里。
这一切有什么用?除非自欺欺人!为什么要这样自己对自己说假话?无非是免得去想自己是个怪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随时可干吃里爬外的事儿。因为一个人讨厌自己,既然讨厌自己,就自暴自弃,就可以使坏作恶。我就作过恶。不是有益世道人心的道德,而是针对某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那人是个勇敢分子,独来独往,屹然挺立,与各种形式的权力作斗争,不怕霸主动雷霆之怒,要惩罚他的胆大妄为。
我曾想去摸摸蝴蝶的翅膀,差点儿把翅膀折断。其实只想知道粉蝶的娇弱。指尖上还感到翅上细毛的抖动,毛上的渗液还沾在我捉昆虫的湿手指上。我屏息静气,让这奇迹过去,让指尖感到的生命之波传入翅膀受伤的肌理,而那蝴蝶的生命已入于麻痹衰竭状态。
一张长桌,长得像耶稣及其门徒所用的那种,上面堆着物品,瓶罐,书籍。有的书已看了开头,反扣在桌上。有的还没打开,叠成老厚一摞,耀目照眼。我喜欢在早晨看书,但很少正襟危坐,一页页翻着看。早晨似乎宜于做别的事,而不是读书。尤其是一天的这一刻,人该按程序起身,出门上班。
我家的人,历来就是这样生活。读书,思考,他们觉得是浪费时间。他们一起身就大声喧哗,以宣告时间已上班,永远重复同样的动作:凡一份人家要关注的事,做过了又重来,一辈子干同样的家务,而且一本正经,好像别无选择。坐着空打发日子的是懒汉,他们抱着做得更好更有用的信念,走进走出,忙得满头大汗,把碗碟洗得一尘不染,放得整整齐齐。没有家务没有采购,他们会闲得发慌。做大量的事,消磨去大量的时间,免得停下来不知所措。他们说话,是免得冷场;冷场,就不自在,像烈酒流过喉咙,烧灼胸口。他们总抱怨说,要做的事太多,事实上是抱怨自己成了逃避无聊的奴隶。他们责怪生活平淡无奇,不让有个人选择的余地,成了折磨他们的超强力量的牺牲品,屈从于重复复重复的死套套。
今天早晨,我就借助于做家务,出一身汗,把套房打扫干净。之所以选这一项,因为确信有够多的事要做。一上午就这样打发过去。从容易的着手,把房间旮旯都打扫到,像从小教我的那样,称得上能干的家庭主妇。我的劳作值得夸奖,而把可以等等的事放到明天去做不迟--如摊得到处都是的书,这不碍事,不像又多又脏的碗碟,因为要用,不能一直脏着。等全干完了,自己也梳洗一番,一身好闻的气味。中午已到。
终于可以坐下来享两小时的清福,坐在自己干净的套房里,自己也一样干净。打开书来,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角逐,在我阅读时消失了。正是靠了书本,对世事看得更分明,而不是靠干家务。不可解的,变得可亲起来。借询问的形式,回答就在询问之中,天主得以显形。礼拜天下午慢慢流逝,太阳已无赫赫之光,犹如少妇的脸色,虽说还年轻,却已无处女的娇美。日华晻暧,照在皮肤上留下淡淡的影子。不知不觉中,白日失去了光彩,黯然消隐。我想起了朱丽叶……
这天,不同于其他日子。拉窗帘时,很久没遇到绳结而卡住。人容易逃避到习惯里,那里四平八稳,波澜不惊,安静得像乡下房子。今天,习惯变了,变得抽象起来。等着想知道到何处落脚,另找个位置。舍人情易习的习惯,而躲进孤独里——消失在拖长的“孤”字里,消失在听不见的“独”字里。
我虚飘飘的没有重量,怕消失得无影无踪,陶醉在广漠的空间里。怎样才能吸纳一切,变成一种蹦跳激荡的力?怎样才不至于散架,撕成碎片,化身亿万星星点点?隐在一个自由女子的身影里——有种妖术般异样的吸引力。我听到美人鱼迷人的声音召唤我去发现美,去发现伟大。我知道她想断送我,看到她脸上还流着冤死者失色的鲜血。我正想把这一切统统送去见鬼,但马上后悔说出了口,要知道魔鬼在谛听,等着咬我。魔鬼能为我的脆弱、我的怯懦而心软?真相是否已然隐去?我是否能借他人之眼来观看世界?
他是今天早晨走的,大软皮包里只装了几本书。他走下盘旋而下的楼梯。
要说走路的样子谁都没他好。两腿笔直,无可挑剔。为感觉到他的手恨不得他抽我两记耳光,让空气也唉唉叹息。我很想抓住他手,拧他手指,但他却碰不得,从头到脚都强直生硬。水银流泻着毒液。直挺挺死板板,他走下旋转楼梯。
根本没有热面包的香气,今晨也没人到面包房来。今天是礼拜天,迟早会到来的礼拜天,连鼻子窝在被子里也闻得出来。听到钟声四起,想象托盘里托出黄澄澄的新鲜牛角面包,小孩拉着气球跟狗跑差点把热茶打翻,想象速溶咖啡广告里穿长统袜的大腿,想象这是一个尽看电视的礼拜天。一股穿堂风,像条长蛇,钻进我身子。起居室还留着烟味,外套,羊毛衫,翻过来的脏袜子,摊得到处都是,临时凑成一顿菲薄晚餐的剩碗残碟,都罩在蓝灰色的晨雾里,像死人皮肤余温尚存;人要死了就顾不得临终表情,是什么样子就成什么样子。厨房的方砖,冷冰冰的。电话线盘缠一团,像螺丝卷似的。
赤身露体或几近一丝不挂,我记起曾头痛来着,这时直僵僵站着,不知从何开始,是先穿袜子--一碰地板就脏了--,还是烧开水泡茶,或者干脆出门,不刷牙也不梳头就上街,让头发梳齐、衣着考究、心情愉快的行人,领教领教我这副落拓相。我头发都打结了,用手抹抹平,曾看到有个醉汉就用胖手背这么压一压抿一抿的。
我两拳撑到袋底,让长裤完全往下坠,裤脚拖到地上,堆起几叠褶皱,贴边剐着石子路。裤裆下垂,侧影像立体派绘画,走路时摆动胯部,布料在屁股和大腿根都留下白印。裤腿里伸出的大靴子,像画脚没画好而画成大球模样。我从玻璃橱窗里瞄到自己的侧影。后景比较模糊,眼睛像高级相机镜头对光那样前后转动。上街脸不洗头不梳,很得意于自己这副脏模样。我没走远,知道没离开住处附近,很快往左拐进最近一条街,走成一个四边形的最后一边。迎着风,忍着饿,尚未朝食,肚子扁扁的。我要表明,人可以这样不修边幅,不顾惜自己,别人才不放在我眼里哪。身体不足道,饥饿感,女性美,都可置之不理。我要别人知道我这样是因为忙。
其实瞎忙而已,但瞎忙得高明,以致忘了寒冷,故意把脏头发贴在脑门上像条绷带。我要人家以为我病了,来可怜我。我把自己这形象映现在店家的橱窗里,相信至少有人在看我,相信我存在于天地间。饥饿会向人进行小小的讹诈,钳住我不放,使我面临这二元对立的矛盾之中:生存呢,还是死亡。我愿存活而不食,眼看着消瘦下去,净化自己,冀能自新。
谁都不注意我。我想标榜自己的孤独,可是谁都不信,别人期待着看到一个能吃能喝身强体壮健步疾行的我,一个将身腰一束前额一扬令人人都转过脸来行注目礼的我。
这一企盼,以失败告终。很抱歉,我就是这么平凡不起眼。这时,我正走正方形的最后一条边,拐角就是我楼前的大门,隐在面包房的铺面后面。面包房今天关门。
真觉得饿了。
“他”的名字,可以叫于利安、马锡安或约安,无论是今天还是以后,是眼前实在的生活还是另一种生活,他能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也可能是外国人——最好是外国人,来自异域他乡,讲一种我能懂的语言。他是活着,或已呜呼,对我都无所谓,是他就行,只要是他。
我不说实话,因为我喜欢搞得神秘兮兮的,喜欢多少事尽在不言中。只有在沉默时,在独守秘密的房间里,我才感到快慰。这时,我自导自演,肆无忌惮,高兴起来无妨奸恶,工于心计,多情多恋——同时绝顶聪明。我把自己的故事冲淡,搞得模模糊糊的,东一段西一段,打乱时序,移花接木。因为我不相信有始有终,不相信有碰巧的事。即使混乱也有迹可寻,因为时间就是时间,而我一无所求。于是,瘦骨嶙峋还去其骨,一切都已在那里,用不到我去指指点点。让我以自己的方式去发疯,去求真,我只听命于内心的驱驰。这儿有个我不打算说的故事,因为跟千千万万其他故事一样。一切都是故事,一生的每分每秒都在讲述一个故事,一死还有什么回忆可言!我们不得已活出许多故事来,难道能都忘怀,只留下岁月的精华和泡沫?谁也不明白,为什么他是他?为什么相爱?为什么相妒?为什么不爱?为什么哭泣?为什么作恶,不论大恶小恶?我从这段禅语感到宽慰:“妙中自有更妙。众生皆有佛性,各具智慧与德性,而当局者迷,是误于妄念。”
具体到我,还能碰到什么事呢?日复一日,千篇一律。所以,常百无聊赖,脾气暴躁。我常烦躁,虽然没人说看到我“发脾气”——那是因为我太喜欢嫣然媚人,失望之余,便摆出一副苦相。事实上,我心头很忧伤,总是很忧伤。会唱歌,我就唱blues[忧丧曲],咧着嘴,挂着大颗大颗的眼泪,身子瘦损,拼命抽烟,喝过量的白酒、香槟或伏特加,潦倒粗疏,怨天尤人,陶醉在痛苦的旋涡里。
然而,生活做出了另一种安排。我的模样像十五岁,有个时期显得有点圆乎乎的,现在已不抽烟,睡得也早,酒就喜欢干红。但一直不明白,如此这般,是不是还是一种欺骗?选择,并不一定是折中,求得半拉儿满足,对失去的一切加倍渴望,是这样吧,时不时的?之后,一切又变了。说是要顺应人生,在精神振足的日子,可以提升到智慧、理性、历史的层面来认识。历史,在我看来,写的都是垂范后世的行为,逸出常规的非常事。有人指出,这里是一对模范夫妻,正直,高尚,没有花花事儿,没有斑斑污点。我却为高傲所苦。我那时并不很快活,因为我并不十分内向,并不内向到无需外求,无需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我的能耐。在情爱——真情的爱——与自我表现之间,无所适从。我之成为今日之我,是前因造成的后果:小时候,跟所有孩子一样,相信天主教行善的说法,人都是有罪的,造成别人的不幸我有责,应忏悔。我说谎,是怕神圣的惩罚,就是说,怕最后审判。我学做好人,变得懂事,爱整洁,每晚像洗内裤那样洗刷我的罪过,再也不想到作恶。我脚踏实地,布施穷人,天真得像花海里的鲜花,开在散发春天气息的绿草场里。
这一切有什么用?除非自欺欺人!为什么要这样自己对自己说假话?无非是免得去想自己是个怪物,什么坏事都做得出来,随时可干吃里爬外的事儿。因为一个人讨厌自己,既然讨厌自己,就自暴自弃,就可以使坏作恶。我就作过恶。不是有益世道人心的道德,而是针对某个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那人是个勇敢分子,独来独往,屹然挺立,与各种形式的权力作斗争,不怕霸主动雷霆之怒,要惩罚他的胆大妄为。
我曾想去摸摸蝴蝶的翅膀,差点儿把翅膀折断。其实只想知道粉蝶的娇弱。指尖上还感到翅上细毛的抖动,毛上的渗液还沾在我捉昆虫的湿手指上。我屏息静气,让这奇迹过去,让指尖感到的生命之波传入翅膀受伤的肌理,而那蝴蝶的生命已入于麻痹衰竭状态。
一张长桌,长得像耶稣及其门徒所用的那种,上面堆着物品,瓶罐,书籍。有的书已看了开头,反扣在桌上。有的还没打开,叠成老厚一摞,耀目照眼。我喜欢在早晨看书,但很少正襟危坐,一页页翻着看。早晨似乎宜于做别的事,而不是读书。尤其是一天的这一刻,人该按程序起身,出门上班。
我家的人,历来就是这样生活。读书,思考,他们觉得是浪费时间。他们一起身就大声喧哗,以宣告时间已上班,永远重复同样的动作:凡一份人家要关注的事,做过了又重来,一辈子干同样的家务,而且一本正经,好像别无选择。坐着空打发日子的是懒汉,他们抱着做得更好更有用的信念,走进走出,忙得满头大汗,把碗碟洗得一尘不染,放得整整齐齐。没有家务没有采购,他们会闲得发慌。做大量的事,消磨去大量的时间,免得停下来不知所措。他们说话,是免得冷场;冷场,就不自在,像烈酒流过喉咙,烧灼胸口。他们总抱怨说,要做的事太多,事实上是抱怨自己成了逃避无聊的奴隶。他们责怪生活平淡无奇,不让有个人选择的余地,成了折磨他们的超强力量的牺牲品,屈从于重复复重复的死套套。
今天早晨,我就借助于做家务,出一身汗,把套房打扫干净。之所以选这一项,因为确信有够多的事要做。一上午就这样打发过去。从容易的着手,把房间旮旯都打扫到,像从小教我的那样,称得上能干的家庭主妇。我的劳作值得夸奖,而把可以等等的事放到明天去做不迟--如摊得到处都是的书,这不碍事,不像又多又脏的碗碟,因为要用,不能一直脏着。等全干完了,自己也梳洗一番,一身好闻的气味。中午已到。
终于可以坐下来享两小时的清福,坐在自己干净的套房里,自己也一样干净。打开书来,争分夺秒、与时间赛跑的角逐,在我阅读时消失了。正是靠了书本,对世事看得更分明,而不是靠干家务。不可解的,变得可亲起来。借询问的形式,回答就在询问之中,天主得以显形。礼拜天下午慢慢流逝,太阳已无赫赫之光,犹如少妇的脸色,虽说还年轻,却已无处女的娇美。日华晻暧,照在皮肤上留下淡淡的影子。不知不觉中,白日失去了光彩,黯然消隐。我想起了朱丽叶……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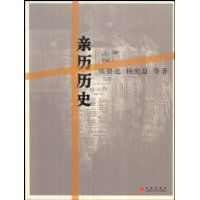 作者:苏菲·玛索 (法)
作者:苏菲·玛索 (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