列侬回忆 第一部分
关于摇滚
扬:你认为摇滚乐的未来是什么?
约翰: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我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摇滚乐搞成狗屎的精英主义,我们就会把它搞成狗屎摇滚精英主义。如果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的摇滚乐,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创造,不要再被革命形象还有长发迷惑了,我们总得超越那个层次,那也是我们剪掉头发的原因150。我们爽快地坦白一些吧,看看到底谁是谁、谁做了哪些事情。
看看谁是真的在做音乐、谁又在胡搞一堆狗屎东西。摇滚乐将会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什么。
扬:为什么你认为它对大家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约翰:摇滚乐吗?因为它够原始,而且完全不用废话——最棒的玩意儿。而且它会“穿透”你。它就是节奏。在丛林里,他们就有这样的节奏,传遍全世界。它就是那么简单。你弄出这个节奏,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动起来。我在Malcolm X151、Eldridge Cleaver152还是谁的书上读到,他说黑人通过摇滚乐让中产阶级的白人回归到他们的身体,把他们的心灵和身体都投了进去,事情就像那样。它打通了一切。对我来说它就是打通了,在我15岁的时候,它是唯一能够穿透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能够抓住我的东西。摇滚乐是真实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而且关于摇滚乐的事,我指的是好的摇滚乐,不管好的定义是什么等等,哈哈,所有那堆狗屎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而且这种真实(realism)会穿透一切抓住你,真实的不只是你自己而已。你会从那里面辨认出某些纯真(true)的东西,就像所有真正的艺术一样,无论艺术的定义是什么,各位读者。这样可以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它是真实的,它通常也很简单;如果它很简单,它就是真实的。说起来就是这样。
洋子:嗯。
约翰:摇滚乐也抓住了你(对洋子说),不是吗?
洋子:是……
约翰:终于。
洋子:古典音乐基本上是4/4拍,后来也走向4/3拍的华尔兹,更多节奏之类的。但它走的离心跳越来越远,心跳是4/4拍,而它呢——(比手势示范)你知道吗?然后它们开始“1-2-3”,像那样,然后……
约翰:越来越变态。
洋子:……节奏的装饰性愈来愈强,而且你知道像勋伯格(Schoenberg)153、韦伯恩(Webern)154,他们的节奏都像是——(比手势示范)你知道,像那样的东西。非常复杂而且很有趣,而我们的心智就像那样,但它们失去了心跳的声音。我一开始去看Beatles录音的时候,心里想:“喔,是这样的啊。”所以我问约翰:“嗯,你们为什么总是用那种节奏呢?都是一样的节奏,为什么你们不用更复杂一点的东西?”
约翰:当时我正在做Bulldog155。
洋子:然后他说了:“喔,她说我们一直在用同样的节奏。”
约翰:非常尴尬。
洋子:然后我突然间了解到,那就是……
扬:是你觉得尴尬,还是洋子?
约翰:是我,因为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些有深度的话,我会说 :“噢,或许吧……”
洋子:他是个很害羞的家伙……
约翰:我是很害羞,如果有人攻击我,我会退缩。
洋子:嗯。
约翰:一直到我有了那个……
洋子:我同样有这种知识分子的臭架子(snobbery)……
约翰:她是个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你看,当我在骂“那些去他妈的知识分子”时,我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用脑袋里那种数学公式般的思考模式去感受事物,他们会说:“这个是那个的结果,而它也造成了这个。”因为这种运算方式在他们小时候就养成了。
洋子:要解释这些,最好的例证就是,我如果没看到乐谱就不会弹钢琴。
约翰:神经错乱!
洋子:我必须先看到才行——所以就是那样。
约翰:那就是精英主义(intellectualism)。
洋子:(笑)
约翰:那就叫音乐修养(musicianship),一整个流派的音乐狗屎——除非能读懂那张纸,不然你别想做音乐,而那张纸跟音乐根本不相干。
扬:现在你30岁,感受到的摇滚乐,跟你15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吗?
约翰:这个嘛,它永远不会再那么新鲜了,对我而言,它不可能再有像以前一样的冲击效果,不过Tutti Frutti跟Long Tall Sally(63)还是相当前卫。几天前我在格林威治村遇到洋子在前卫圈的老朋友,他正在谈论“单一音符”(one note),还说“迪伦难道不是只唱一个音吗?”——好像他才刚发现这件事似的。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你的极限了。我可以用知识分子的方式跟你好好地玩游戏,来(提出)证明为什么某些音乐一直都很重要,不管过去或未来。就像蓝调相对于爵士乐——与白人中产阶级有教养的爵士乐相比,蓝调比较好。
扬:因为它比较简单吗?
约翰: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既不被扭曲,也不是被凭空想像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概念。它就像把椅子——但这把椅子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不是被设计成一把更好的椅子、一把更大的椅子或者设计成钉上皮革的椅子。它就是第一把椅子,它是拿来坐的,不是摆着好看,或者拿来欣赏的。你就“坐在”那个音乐上。
扬:你认为痛苦的概念是什么?
约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扬:God这首歌的开头,你唱“上帝是一个概念 / 我们用来衡量自己的痛苦”(God is a concept by which we measure our pain )17。
约翰: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经受的这些。人是从痛苦中出生的,而痛苦也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的状态。我认为痛苦越是巨大,我们需要的神就越多。
扬:“上帝作为衡量痛苦的概念”这句话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深奥的哲学论述。
约翰:喔,我从来没听过那些东西。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不知道有谁写过那些东西,或者谁说过什么,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真不可思议。
洋子:你只是在感受它而已。
约翰:没错,我感受到了。你看,当我感受它的时候,简直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了。
扬:乔治·马丁跟Phil Spector的制作风格,有什么不同(9)?
约翰:嗯,乔治·马丁——我不知道。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些唱片,像同名双专辑,乔治·马丁并没有担纲制作。我不知道标准在哪,但是他的确没有,我不记得了。假如是早期,我还能想起乔治·马丁做了些什么。
扬:他做了什么?
约翰:他担任“转译”的工作。如果保罗想用小提琴的声音,他会帮忙“转译”成他(保罗)要的形式。像In My Life18,有一段伊丽莎白时代风格的钢琴独奏,他就会做那类事情。我会跟他说:“弹段巴赫之类的东西吧,你可以来个十二小节吗?”他还帮我们发展出一套语言,让我们可以跟其他乐手沟通。因为我非常害羞,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原因,我很少跟专业乐手来往。我不喜欢去跟坐在那里的二十来个家伙解释他们应该做什么,反正他们总是很烂。所以除了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大概都跟那类事情没啥关系,我什么都自己来。
扬:那你现在为什么用Phil取代乔治·马丁?
约翰:这个嘛,我不是找人来替代乔治·马丁,我不会利用任何人。这跟乔治·马丁个人无关,他只是不适合而已——他比较接近保罗的风格,而不是我的。
扬:Phil是否带进来什么特别的东西?
约翰:Phil——有,有。你到处都听得到Spector,不是哪个特别的地方,你就是听得出他。我相信Phil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就像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非常神经质。不过我们一起做了不少曲子,我跟洋子一起弄,录音的时候,她会在控制室里鼓励我,但我们依旧陷入困境。然后Phil搬进来住,在我们越陷越深的时候,他让整件事情获得新生。我们完成了一些东西,对录音的恐惧也磨掉了一些。
扬:你对专辑整体的评价如何?
约翰:我想这是我做过最棒的事,我认为它很写实,对我来说也是真诚的,这些年来的In My Life、I’m a Loser 19、Help! 20、Strawberry Fields 21一直是如此,它们都是很个人的唱片。我一直以来都是写关于自己的事,我不喜欢写第三人称的歌,写那些住在水泥公寓里的人的生活,我喜欢第一人称的音乐。不过因为焦虑,还有很多原因,以前我偶尔才会特别写些关于自己的事,但现在我所写的完完全全是我自己,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不是别人。所以我喜欢它。
扬:有一份诚实在里面……
约翰:它很真,你知道的。它说的是“我”,而我也确实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东西了。以前我诚实写下的歌曲只有Help!和Straw-berry Fields。我还能再举出几首,只是没办法马上想起来,这些都是我自认为最好的歌。它们真的都是我依照个人经验写成的,而不是把自己投射到某种情境,然后写出一个漂亮的故事,我一直都觉得那样很假。但我偶尔还是必须想像情境才写得出来,因为以前我非得写出那么多歌不可,或者因为我已经焦虑到根本没办法思考自己的事。
扬:在这张专辑里,其实完全没有想像的成分……
约翰:对,因为我脑袋里完全没有那样的东西,完全没有幻想。
扬:也没有“报纸计程车”(newspaper taxi)22……
约翰:对。那时候我是有意识地在写诗,那都是刻意的诗。但现在这张专辑里的东西,比我过去写的任何东西都要更好,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刻意为之的作品,我写这些歌遇到的障碍,是有史以来最少的。
扬:完全不用废话。
约翰:对,完全不用废话。
扬:音乐非常简单,非常节约……
约翰:没错,我一直都喜欢简单的摇滚乐。现在英国就有一首很棒的歌叫I Hear You Knocking(10),几个月前的。Spirit in the Sky(11)我也很喜欢。我一直都很喜欢简单的摇滚乐,没别的。我曾经嗑过药,走过迷幻的路子,就跟这整代人一样。但说真的,我很喜欢老摇滚。老摇滚最能表达我自己,我有很多的点子,想在Mother这首歌里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光用钢琴就已经把一切都搞定了,剩下的可以用你的心去体会出来。我想(这张唱片)衬乐的复杂程度,就跟你听过的任何唱片一样,如果你耳朵够尖,就会听出来。任何乐手都会告诉你,只要在钢琴上弹一个音,都会有很多的泛音在里面,所以就朝这样的方向去做了。去他的,这张唱片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扬:你是怎么把God里面的一连串“祷文”(1itany)组合起来的?
约翰:什么祷文?
扬:就是“我不相信魔法(I don’t believe in magic)”那段,是怎么开始的23?
约翰:这个嘛,就像很多歌词一样,它们就这么从我口中冒出来,就是那样开始的。God几乎是用三首歌组合而成的,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上帝是一个概念,我们用来测量自己的痛苦”,有了这样一个句子之后,你就会坐下来把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旋律唱出来。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唱):“God is the concept……蹦蹦蹦蹦”,因为我喜欢那种音乐。然后我就这样进行下去了(唱):“I don’t believe in magic……”它就一直在我脑中盘旋,还有《易经》(I Ching)和《圣经》(Bible),前面三四个词是这样跑出来的,随口就唱出来了。
扬:你什么时候想到要一路写到“我不相信Beatles(I don’t believe in Beatles)”这一句?
约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才理解到我把所有我不相信的东西都写进去了,我其实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就像列一份寄圣诞卡的名单……我该在哪里结束?丘吉尔吗?还漏掉了谁?就像那样,于是我觉得该停下来了……我本来想留下一段空白,然后说,你就填上那些自己不相信的名字吧,随便都写得出来。不过Beatles放在最后,是因为我不再相信神话(myth),而Beatles就是一桩神话,我不相信这套,美梦已经结束了。我不单指Beatles已经结束了,我说的是整个时代的事。美梦结束了,而我个人必须回归到所谓的“现实”。
扬:God后来成为电台最常播放的歌曲,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约翰:呃,我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一开始挑的是Look at Me,因为它很容易入耳,他们或许以为这是Beatles的东西吧。所以我不清楚,如果那是大家要的,那就这样吧。整张唱片最有想法、最有感觉的歌,或许是God和Working Class Hero。
扬:在God里面,提到迪伦时,为什么你宁可用Zimmerman,而不是用迪伦24?
约翰:因为迪伦是狗屎,Zimmerman才是他真正的姓。我不相信迪伦……同样的道理,我也不相信汤姆·琼斯(Tom Jones)。Zimmerman是他的姓,我的名字不叫约翰·披头(John Beatle),我叫约翰·列侬,就是那样。
关于摇滚
扬:你认为摇滚乐的未来是什么?
约翰:不管是什么玩意儿,就是我们做出来的东西。我是说,如果我们要把摇滚乐搞成狗屎的精英主义,我们就会把它搞成狗屎摇滚精英主义。如果我们要的是货真价实的摇滚乐,那就看我们怎么去创造,不要再被革命形象还有长发迷惑了,我们总得超越那个层次,那也是我们剪掉头发的原因150。我们爽快地坦白一些吧,看看到底谁是谁、谁做了哪些事情。
看看谁是真的在做音乐、谁又在胡搞一堆狗屎东西。摇滚乐将会是我们做出来的这些东西,无论是什么。
扬:为什么你认为它对大家有这么重要的意义?
约翰:摇滚乐吗?因为它够原始,而且完全不用废话——最棒的玩意儿。而且它会“穿透”你。它就是节奏。在丛林里,他们就有这样的节奏,传遍全世界。它就是那么简单。你弄出这个节奏,所有的人都会跟着动起来。我在Malcolm X151、Eldridge Cleaver152还是谁的书上读到,他说黑人通过摇滚乐让中产阶级的白人回归到他们的身体,把他们的心灵和身体都投了进去,事情就像那样。它打通了一切。对我来说它就是打通了,在我15岁的时候,它是唯一能够穿透当时发生的所有事情、能够抓住我的东西。摇滚乐是真实的,其他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而且关于摇滚乐的事,我指的是好的摇滚乐,不管好的定义是什么等等,哈哈,所有那堆狗屎东西,都是货真价实的。而且这种真实(realism)会穿透一切抓住你,真实的不只是你自己而已。你会从那里面辨认出某些纯真(true)的东西,就像所有真正的艺术一样,无论艺术的定义是什么,各位读者。这样可以吗?就是这么回事。如果它是真实的,它通常也很简单;如果它很简单,它就是真实的。说起来就是这样。
洋子:嗯。
约翰:摇滚乐也抓住了你(对洋子说),不是吗?
洋子:是……
约翰:终于。
洋子:古典音乐基本上是4/4拍,后来也走向4/3拍的华尔兹,更多节奏之类的。但它走的离心跳越来越远,心跳是4/4拍,而它呢——(比手势示范)你知道吗?然后它们开始“1-2-3”,像那样,然后……
约翰:越来越变态。
洋子:……节奏的装饰性愈来愈强,而且你知道像勋伯格(Schoenberg)153、韦伯恩(Webern)154,他们的节奏都像是——(比手势示范)你知道,像那样的东西。非常复杂而且很有趣,而我们的心智就像那样,但它们失去了心跳的声音。我一开始去看Beatles录音的时候,心里想:“喔,是这样的啊。”所以我问约翰:“嗯,你们为什么总是用那种节奏呢?都是一样的节奏,为什么你们不用更复杂一点的东西?”
约翰:当时我正在做Bulldog155。
洋子:然后他说了:“喔,她说我们一直在用同样的节奏。”
约翰:非常尴尬。
洋子:然后我突然间了解到,那就是……
扬:是你觉得尴尬,还是洋子?
约翰:是我,因为如果有人在我面前说些有深度的话,我会说 :“噢,或许吧……”
洋子:他是个很害羞的家伙……
约翰:我是很害羞,如果有人攻击我,我会退缩。
洋子:嗯。
约翰:一直到我有了那个……
洋子:我同样有这种知识分子的臭架子(snobbery)……
约翰:她是个知识分子,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你看,当我在骂“那些去他妈的知识分子”时,我确实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他们用脑袋里那种数学公式般的思考模式去感受事物,他们会说:“这个是那个的结果,而它也造成了这个。”因为这种运算方式在他们小时候就养成了。
洋子:要解释这些,最好的例证就是,我如果没看到乐谱就不会弹钢琴。
约翰:神经错乱!
洋子:我必须先看到才行——所以就是那样。
约翰:那就是精英主义(intellectualism)。
洋子:(笑)
约翰:那就叫音乐修养(musicianship),一整个流派的音乐狗屎——除非能读懂那张纸,不然你别想做音乐,而那张纸跟音乐根本不相干。
扬:现在你30岁,感受到的摇滚乐,跟你15岁的时候还是一样吗?
约翰:这个嘛,它永远不会再那么新鲜了,对我而言,它不可能再有像以前一样的冲击效果,不过Tutti Frutti跟Long Tall Sally(63)还是相当前卫。几天前我在格林威治村遇到洋子在前卫圈的老朋友,他正在谈论“单一音符”(one note),还说“迪伦难道不是只唱一个音吗?”——好像他才刚发现这件事似的。我觉得那应该就是你的极限了。我可以用知识分子的方式跟你好好地玩游戏,来(提出)证明为什么某些音乐一直都很重要,不管过去或未来。就像蓝调相对于爵士乐——与白人中产阶级有教养的爵士乐相比,蓝调比较好。
扬:因为它比较简单吗?
约翰:因为它是“真实”的。它既不被扭曲,也不是被凭空想像出来的——它不是一种概念。它就像把椅子——但这把椅子并不是被设计出来的,不是被设计成一把更好的椅子、一把更大的椅子或者设计成钉上皮革的椅子。它就是第一把椅子,它是拿来坐的,不是摆着好看,或者拿来欣赏的。你就“坐在”那个音乐上。
扬:你认为痛苦的概念是什么?
约翰:我不明白你的意思。
扬:God这首歌的开头,你唱“上帝是一个概念 / 我们用来衡量自己的痛苦”(God is a concept by which we measure our pain )17。
约翰:我们的痛苦,就是我们一直以来经受的这些。人是从痛苦中出生的,而痛苦也是我们大多数时候的状态。我认为痛苦越是巨大,我们需要的神就越多。
扬:“上帝作为衡量痛苦的概念”这句话背后,其实有一整套深奥的哲学论述。
约翰:喔,我从来没听过那些东西。这只是我个人的理解,我不知道有谁写过那些东西,或者谁说过什么,这只是我自己的理解,真不可思议。
洋子:你只是在感受它而已。
约翰:没错,我感受到了。你看,当我感受它的时候,简直就像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现在我知道他们讲的是什么意思了。
扬:乔治·马丁跟Phil Spector的制作风格,有什么不同(9)?
约翰:嗯,乔治·马丁——我不知道。你可以看得出来,我们有些唱片,像同名双专辑,乔治·马丁并没有担纲制作。我不知道标准在哪,但是他的确没有,我不记得了。假如是早期,我还能想起乔治·马丁做了些什么。
扬:他做了什么?
约翰:他担任“转译”的工作。如果保罗想用小提琴的声音,他会帮忙“转译”成他(保罗)要的形式。像In My Life18,有一段伊丽莎白时代风格的钢琴独奏,他就会做那类事情。我会跟他说:“弹段巴赫之类的东西吧,你可以来个十二小节吗?”他还帮我们发展出一套语言,让我们可以跟其他乐手沟通。因为我非常害羞,还有许多许多其他的原因,我很少跟专业乐手来往。我不喜欢去跟坐在那里的二十来个家伙解释他们应该做什么,反正他们总是很烂。所以除了最开始的那段时间,我大概都跟那类事情没啥关系,我什么都自己来。
扬:那你现在为什么用Phil取代乔治·马丁?
约翰:这个嘛,我不是找人来替代乔治·马丁,我不会利用任何人。这跟乔治·马丁个人无关,他只是不适合而已——他比较接近保罗的风格,而不是我的。
扬:Phil是否带进来什么特别的东西?
约翰:Phil——有,有。你到处都听得到Spector,不是哪个特别的地方,你就是听得出他。我相信Phil是个伟大的艺术家,但就像许多伟大的艺术家一样,他非常神经质。不过我们一起做了不少曲子,我跟洋子一起弄,录音的时候,她会在控制室里鼓励我,但我们依旧陷入困境。然后Phil搬进来住,在我们越陷越深的时候,他让整件事情获得新生。我们完成了一些东西,对录音的恐惧也磨掉了一些。
扬:你对专辑整体的评价如何?
约翰:我想这是我做过最棒的事,我认为它很写实,对我来说也是真诚的,这些年来的In My Life、I’m a Loser 19、Help! 20、Strawberry Fields 21一直是如此,它们都是很个人的唱片。我一直以来都是写关于自己的事,我不喜欢写第三人称的歌,写那些住在水泥公寓里的人的生活,我喜欢第一人称的音乐。不过因为焦虑,还有很多原因,以前我偶尔才会特别写些关于自己的事,但现在我所写的完完全全是我自己,这就是我喜欢它的原因。这就是我,不是别人。所以我喜欢它。
扬:有一份诚实在里面……
约翰:它很真,你知道的。它说的是“我”,而我也确实不知道任何其他的东西了。以前我诚实写下的歌曲只有Help!和Straw-berry Fields。我还能再举出几首,只是没办法马上想起来,这些都是我自认为最好的歌。它们真的都是我依照个人经验写成的,而不是把自己投射到某种情境,然后写出一个漂亮的故事,我一直都觉得那样很假。但我偶尔还是必须想像情境才写得出来,因为以前我非得写出那么多歌不可,或者因为我已经焦虑到根本没办法思考自己的事。
扬:在这张专辑里,其实完全没有想像的成分……
约翰:对,因为我脑袋里完全没有那样的东西,完全没有幻想。
扬:也没有“报纸计程车”(newspaper taxi)22……
约翰:对。那时候我是有意识地在写诗,那都是刻意的诗。但现在这张专辑里的东西,比我过去写的任何东西都要更好,因为它并不是那种刻意为之的作品,我写这些歌遇到的障碍,是有史以来最少的。
扬:完全不用废话。
约翰:对,完全不用废话。
扬:音乐非常简单,非常节约……
约翰:没错,我一直都喜欢简单的摇滚乐。现在英国就有一首很棒的歌叫I Hear You Knocking(10),几个月前的。Spirit in the Sky(11)我也很喜欢。我一直都很喜欢简单的摇滚乐,没别的。我曾经嗑过药,走过迷幻的路子,就跟这整代人一样。但说真的,我很喜欢老摇滚。老摇滚最能表达我自己,我有很多的点子,想在Mother这首歌里做这个做那个,但是光用钢琴就已经把一切都搞定了,剩下的可以用你的心去体会出来。我想(这张唱片)衬乐的复杂程度,就跟你听过的任何唱片一样,如果你耳朵够尖,就会听出来。任何乐手都会告诉你,只要在钢琴上弹一个音,都会有很多的泛音在里面,所以就朝这样的方向去做了。去他的,这张唱片根本不需要其他的东西。
扬:你是怎么把God里面的一连串“祷文”(1itany)组合起来的?
约翰:什么祷文?
扬:就是“我不相信魔法(I don’t believe in magic)”那段,是怎么开始的23?
约翰:这个嘛,就像很多歌词一样,它们就这么从我口中冒出来,就是那样开始的。God几乎是用三首歌组合而成的,我有这么一个想法:“上帝是一个概念,我们用来测量自己的痛苦”,有了这样一个句子之后,你就会坐下来把脑中浮现的第一个旋律唱出来。这首歌的旋律很简单(唱):“God is the concept……蹦蹦蹦蹦”,因为我喜欢那种音乐。然后我就这样进行下去了(唱):“I don’t believe in magic……”它就一直在我脑中盘旋,还有《易经》(I Ching)和《圣经》(Bible),前面三四个词是这样跑出来的,随口就唱出来了。
扬:你什么时候想到要一路写到“我不相信Beatles(I don’t believe in Beatles)”这一句?
约翰: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才理解到我把所有我不相信的东西都写进去了,我其实还可以继续写下去的,就像列一份寄圣诞卡的名单……我该在哪里结束?丘吉尔吗?还漏掉了谁?就像那样,于是我觉得该停下来了……我本来想留下一段空白,然后说,你就填上那些自己不相信的名字吧,随便都写得出来。不过Beatles放在最后,是因为我不再相信神话(myth),而Beatles就是一桩神话,我不相信这套,美梦已经结束了。我不单指Beatles已经结束了,我说的是整个时代的事。美梦结束了,而我个人必须回归到所谓的“现实”。
扬:God后来成为电台最常播放的歌曲,这件事你是什么时候才知道的?
约翰:呃,我不知道这件事。他们一开始挑的是Look at Me,因为它很容易入耳,他们或许以为这是Beatles的东西吧。所以我不清楚,如果那是大家要的,那就这样吧。整张唱片最有想法、最有感觉的歌,或许是God和Working Class Hero。
扬:在God里面,提到迪伦时,为什么你宁可用Zimmerman,而不是用迪伦24?
约翰:因为迪伦是狗屎,Zimmerman才是他真正的姓。我不相信迪伦……同样的道理,我也不相信汤姆·琼斯(Tom Jones)。Zimmerman是他的姓,我的名字不叫约翰·披头(John Beatle),我叫约翰·列侬,就是那样。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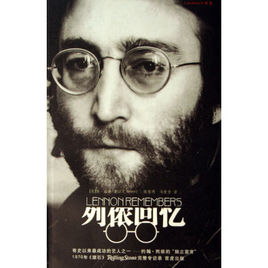 作者:扬·温纳 (美)
作者:扬·温纳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