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唐波夫省北部有一个乡村名叫“杨树林”。老人们说,过去这里的确有过一片密林。可是在我的童年时期,人们就早已把那片林子忘记了。
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延伸得很远很远,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却被许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边的农舍简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驰着许多饥饿的野狼。我小的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处处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还有远处狼的号叫声。有时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时只是过于紧张的儿童的听觉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围一切都焕然一新了。草原上开着野花,油绿的嫩草覆盖着大地。处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
我们的村子很大,居民约有5000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贫兹,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挣钱。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
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员,他没受过教育,但却知书识字,甚至可以说是博学多识。他喜好读书,在和人辩论的时候,也常常引经据典。僻如,有一次他对和他交谈的人说: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的说明,和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上过3年当地的乡村小学。1910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记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
两层楼房的中学校舍,使我很惊讶,在我们杨树林村没有这么高大的房子。我紧握着父亲的手,随他走进了学校的前厅,羞答答地停了脚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宽大的门、石地、有栏杆的宽敞的楼梯。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家长同来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们简直比那新鲜的、在我看来是富丽的陈设更使我不安。基尔山诺夫是一座商业的县城,在这些和我同样来投考的女孩子中间,农家的孩子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红胖的,用鲜蓝色绸带系着长长的发辫。她鄙视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我靠紧了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似乎在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我们上楼去了,有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招呼进一间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长案后边坐着3位考试委员。我还记得,我回答了一切试题,最后,我就忘记害怕,大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
今后我们将给瑞典人一点颜色看,在这里建起雄城,气死傲慢的邻人……爸爸在楼下等着我。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马上就上楼梯来迎接我,脸色是那么愉快……中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的温暖、感谢的回忆。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在我们学校里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我们也随着她微笑。她是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坐在讲桌后面,沉思地看着我们,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
“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我们能一直不倦地听着她讲。她一面仔细地讲给我们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讲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听着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的讲解,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当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虽然一向没有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知道她是爱我们的。根据她看我们的眼神,根据她有时候亲切地把手放在我们的肩上根据她在我们任何人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地伤心,我们就能理解到她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样也爱慕她的一切:爱她的青春、美丽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个性和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爱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后,抚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时常回忆我所敬爱的阿法娜谢夫娜先生,并且在困难的时候,常会设想:如果她在这里,她可能告诉我怎样做。
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很爱好绘画,美术教员也发现了我有绘画的才能,但是我对自己不敢抱有成为画家的希望。
有一次,美术教员谢尔杰·谢民诺维奇·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他和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一样,也很爱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我们上了他的课,了解了什么是颜色、线条、比例、远近画法等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怎样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来。谢尔杰·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创作,他有一大本画册,粘着很精致的复制名画。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参观的念头……但是,无论自己怎样希望继续学习,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需要我帮助父母。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村子周围,种着黑麦、燕麦和黍子的农田延伸得很远很远,可是靠近村子的地面却被许多深谷割裂得零零散散。深谷逐年扩大,陡峻的高坡上,那些村边的农舍简直就像要跌落到谷底去了。一到冬季,深谷里往返奔驰着许多饥饿的野狼。我小的时候很怕在冬天的夜晚走出屋外:冷,死气沉沉,处处是雪,无边无际的雪,还有远处狼的号叫声。有时真的听到了狼叫,也有时只是过于紧张的儿童的听觉在作怪。……可是一到春季,周围一切都焕然一新了。草原上开着野花,油绿的嫩草覆盖着大地。处处是红的、蓝的、金黄的野花,像火星似的怒放着。雏菊、铃铛花、矢车菊,可以满怀地抱回家去。
我们的村子很大,居民约有5000人。差不多每户都有人到唐波夫、贫兹,甚至也到莫斯科去作工挣钱。可怜的一小块土地是不够养活一家贫苦农民的。
我生在一个和睦的大家庭里。父亲齐莫菲·西门诺维奇·秋里阔夫,在村公所当文书员,他没受过教育,但却知书识字,甚至可以说是博学多识。他喜好读书,在和人辩论的时候,也常常引经据典。僻如,有一次他对和他交谈的人说:
“我记得,我读过一本书,里面关于天体的说明,和您的说法完全不同……”
我上过3年当地的乡村小学。1910年秋季,父亲把我领到基尔山诺夫城去投考一个女子中学。从那时候到现在,差不多40年了,可是一切大小事情我全记得很清楚,就仿佛是昨天的事一样。
两层楼房的中学校舍,使我很惊讶,在我们杨树林村没有这么高大的房子。我紧握着父亲的手,随他走进了学校的前厅,羞答答地停了脚步。一切都是新奇而生疏的:宽大的门、石地、有栏杆的宽敞的楼梯。这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和家长同来的女孩子。最使我不好意思的就是,她们简直比那新鲜的、在我看来是富丽的陈设更使我不安。基尔山诺夫是一座商业的县城,在这些和我同样来投考的女孩子中间,农家的孩子很少。我记得有一个女孩子,看外表是地道商人的女儿,面孔红胖的,用鲜蓝色绸带系着长长的发辫。她鄙视地打量了我一番,就咬着嘴唇转过身子去。我靠紧了父亲,父亲抚摸着我的头,似乎在说:“孩子,不要怕,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随后我们上楼去了,有人把我们一个一个地招呼进一间大屋子去,在屋里的长案后边坐着3位考试委员。我还记得,我回答了一切试题,最后,我就忘记害怕,大声朗诵了以下的诗句:
今后我们将给瑞典人一点颜色看,在这里建起雄城,气死傲慢的邻人……爸爸在楼下等着我。我高兴极了,不顾一切地向他跑去,他马上就上楼梯来迎接我,脸色是那么愉快……中学时期就这样开始了。我至今还保持着对这一时期的温暖、感谢的回忆。阿尔喀基·别洛乌索夫在我们学校里讲授数学,讲得明白有趣。他的夫人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讲授俄文和文学。
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总是微笑着走进教室,我们也随着她微笑。她是那样活泼、年轻、和蔼可亲,她坐在讲桌后面,沉思地看着我们,不用任何开场白,开始就念道:
“树林脱下紫色的衣裳……”
我们能一直不倦地听着她讲。她一面仔细地讲给我们听,一面她本人也陶醉于她所讲述的美景之中。她努力给我们讲解俄罗斯文学的动人力量,它那鼓舞人的思想和情感,以及它的深刻的人道性。
听着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的讲解,我明白了:教师工作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当一个真正的好教师,必须具有活泼的心灵,清晰的头脑,当然,还必须非常喜爱儿童。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虽然一向没有说过爱我们,可是我们无需任何解释就知道她是爱我们的。根据她看我们的眼神,根据她有时候亲切地把手放在我们的肩上根据她在我们任何人遭到失败的时候怎样地伤心,我们就能理解到她对我们的爱。我们同样也爱慕她的一切:爱她的青春、美丽而沉思的面貌,愉快仁慈的个性和她对于自己的工作的爱好。一直到我成年之后,抚育着自己的孩子的时候,我仍时常回忆我所敬爱的阿法娜谢夫娜先生,并且在困难的时候,常会设想:如果她在这里,她可能告诉我怎样做。
另外还有一些很使我怀念基尔山诺夫中学的事情:我很爱好绘画,美术教员也发现了我有绘画的才能,但是我对自己不敢抱有成为画家的希望。
有一次,美术教员谢尔杰·谢民诺维奇·波马佐夫对我说:“您需要学习,一定要学习,您有很大的绘画天才。”
他和耶里萨维塔·阿法娜谢夫娜一样,也很爱好他自己所教的那门学科。我们上了他的课,了解了什么是颜色、线条、比例、远近画法等等以外,也了解了构成美术精神的东西,是在于对生活的热爱和怎样学会随时随地了解生活,看出它在各方面的表现来。谢尔杰·谢民诺维奇给我们介绍了列宾、苏里柯夫、列维唐等大画家的创作,他有一大本画册,粘着很精致的复制名画。那时候在我心里就引起了到莫斯科去,到特列佳柯夫画馆参观参观的念头……但是,无论自己怎样希望继续学习,我知道那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家里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需要我帮助父母。中学毕业后我就回到杨树林来了。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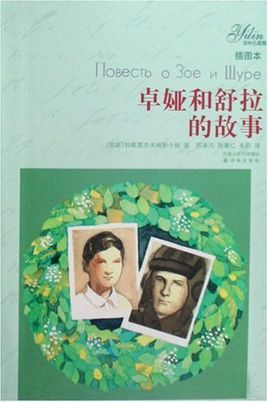 作者:柳·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苏联)
作者:柳·科斯莫杰米杨斯卡娅(苏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