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幸运地走进了北京外国语大学,但不幸的是,一进北外,就“被迫改行”(原本报考的是英语系),拿起了法语课本。但不幸之中毕竟还有万幸:就在同一年,在巴黎,一位法国人异想天开,推出了一场长达6个小时的世界影视广告通宵展映活动,这也就是后来让我痴迷至今的“饕餮之夜”。
法语外教
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法语外教梅涛小姐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法国有许多人喜欢看广告,广告是一个公众话题,人们谈论广告和谈论天气一样平常,而且津津有味。这让我听得目瞪口呆,笑掉大牙:资本主义竟然已经没落无聊到如此地步。
梅涛小姐是个地道的法国人,但给人的感觉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她不苟言笑,工作起来像头牛,连在黑板上写字也都像运足了气一样,弄得粉笔头“啪啪”飞落。常常是一堂课还未过半,她的鼻尖儿上就已经沁满了汗珠。她是我们的语言老师,也是一位法兰西文化的模范传播者。她说的有关法国的一切,我们都信,或者努力去信,唯独她这段有关广告的插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无论如何信马由缰,无论如何壮着胆子浪漫,我们也想不出法国人究竟哪里出了毛病。那时,广告在人们的眼里就像苍蝇一样,人们厌恶它,鄙视它,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它。不过,梅涛小姐在向我们提及广告的时候,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她永远紧绷的脸上却露出了少有的轻松,兴奋得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相信梅涛小姐说的是真话,但又无法相信法国人竟然会傻到如此地步。
从本科到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再借调到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一切都顺理成章,不紧不慢。我也满足于校园的单纯清净,与世无争,平时与学生混得不错,再做些翻译上的学问,北外1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10年间,除了梅涛小姐的那几句广告闲谈外,广告与我似乎毫不相干。
1991年初,我出国进修。原本去法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法国之行泡汤,我“被贬”来到瑞士洛桑大学的现代法语学校,一边进修法语,一边在语言实验室担任助教,辅导来自各个国家的法语学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不幸”,让我体验了一次激情的力量,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瑞士闪念
在瑞士,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活生生的西方广告。洛桑和日内瓦一样,都属于瑞士的法语区,收看法国电视台的节目非常方便,我很快就明白了梅涛小姐当年有关法国人喜欢看广告的奇谈。另外,刚到瑞士,有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也让我见识到了广告或者说广告文化的特殊之处。
一次是在一个有关语言的研讨会上,一位语言学家对瑞士和法国的广告语(广告口号)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侃侃而谈,竟然从广告语里挖出瑞士人是如何保守、如何自高自大而又含而不露,法国人如何懂得诱惑与被诱惑、如何胸怀世界而又缩手缩脚等等。真厉害。
另一次是在大学公寓的前厅里,两个大学生坐在电视机前看广告,一边看,一边争先恐后地抢着猜广告卖的是什么产品。整个广告时间成了他们两个的益智游戏,而且是前仰后合,旁若无人。当然,他们看的是法国电视台的广告。广告一结束,两个人才算是恢复到正常状态,变得没精打采了。
虽然觉得那里的广告很新鲜,但瑞士的山川更新鲜,更诱人,世外桃源一般。因此,我对满世界的广告很快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
除了学业外,打工、旅游成了我在瑞士生活的第二职业,有时打工和旅游两不误,更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有一次,为一家培训机构派发培训小广告,一天就要跑好几个城市。一会儿是人来人往的闹市,一会儿是幽静的莱芒湖畔,一会儿又是爬半个小时才有一户人家的美丽山地。虽然腿脚受累,却真正领略了瑞士的如画风光。
一年的进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一天,我收拾行李到深夜,感觉有点疲劳,又有点心神不定,就来到公寓的前厅,打开电视,准备休息片刻。夜静极了,只听到不远处莱芒湖水有节奏的拍岸声响。公寓的学生都已经入睡,我把电视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信手选了一个频道。广告,广告,广告,还是广告……没有停顿,一连串的广告。鬼使神差,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换频道,而是呆呆地看了下去。我什么也听不见,耳边只有湖水悠缓低沉的撞击声,一浪接着一浪。广告,广告,广告……没完没了,过瘾之极!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饕餮之夜”,更不知道这是法国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转播“饕餮之夜”,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散发着魔力的广告世界。
窗外渐渐亮了起来,街面上也开始有了动静。终于,公寓的清洁女工来了,她看上去无精打采,而我也是一脸疲惫,但一浪接一浪的广告狂潮让我的大脑始终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女工见我这么早就起来看电视,很惊讶。互道早安后,为了不妨碍她的清洁工作,我只好起身回房间了。就在我关电视的一刹那,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一个压抑不住的念头像浪潮一样不停地向我撞来:去法国,学广告!
法语外教
大二的时候,有一天,法语外教梅涛小姐在课堂上告诉我们,法国有许多人喜欢看广告,广告是一个公众话题,人们谈论广告和谈论天气一样平常,而且津津有味。这让我听得目瞪口呆,笑掉大牙:资本主义竟然已经没落无聊到如此地步。
梅涛小姐是个地道的法国人,但给人的感觉却像一个不折不扣的德国人。她不苟言笑,工作起来像头牛,连在黑板上写字也都像运足了气一样,弄得粉笔头“啪啪”飞落。常常是一堂课还未过半,她的鼻尖儿上就已经沁满了汗珠。她是我们的语言老师,也是一位法兰西文化的模范传播者。她说的有关法国的一切,我们都信,或者努力去信,唯独她这段有关广告的插曲,大大超出了我们的想像力。无论如何信马由缰,无论如何壮着胆子浪漫,我们也想不出法国人究竟哪里出了毛病。那时,广告在人们的眼里就像苍蝇一样,人们厌恶它,鄙视它,恨不得一巴掌拍死它。不过,梅涛小姐在向我们提及广告的时候,虽然只是三言两语,但她永远紧绷的脸上却露出了少有的轻松,兴奋得像是变了一个人。我相信梅涛小姐说的是真话,但又无法相信法国人竟然会傻到如此地步。
从本科到研究生,后来又留校任教,再借调到国家教委国际合作司,一切都顺理成章,不紧不慢。我也满足于校园的单纯清净,与世无争,平时与学生混得不错,再做些翻译上的学问,北外10年一眨眼就过去了。10年间,除了梅涛小姐的那几句广告闲谈外,广告与我似乎毫不相干。
1991年初,我出国进修。原本去法国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但由于特殊的历史原因,法国之行泡汤,我“被贬”来到瑞士洛桑大学的现代法语学校,一边进修法语,一边在语言实验室担任助教,辅导来自各个国家的法语学生。没有想到,正是这一次“不幸”,让我体验了一次激情的力量,也彻底改变了我的生活轨迹。
瑞士闪念
在瑞士,我第一次接触到了活生生的西方广告。洛桑和日内瓦一样,都属于瑞士的法语区,收看法国电视台的节目非常方便,我很快就明白了梅涛小姐当年有关法国人喜欢看广告的奇谈。另外,刚到瑞士,有两件不起眼的小事也让我见识到了广告或者说广告文化的特殊之处。
一次是在一个有关语言的研讨会上,一位语言学家对瑞士和法国的广告语(广告口号)进行了比较分析。他侃侃而谈,竟然从广告语里挖出瑞士人是如何保守、如何自高自大而又含而不露,法国人如何懂得诱惑与被诱惑、如何胸怀世界而又缩手缩脚等等。真厉害。
另一次是在大学公寓的前厅里,两个大学生坐在电视机前看广告,一边看,一边争先恐后地抢着猜广告卖的是什么产品。整个广告时间成了他们两个的益智游戏,而且是前仰后合,旁若无人。当然,他们看的是法国电视台的广告。广告一结束,两个人才算是恢复到正常状态,变得没精打采了。
虽然觉得那里的广告很新鲜,但瑞士的山川更新鲜,更诱人,世外桃源一般。因此,我对满世界的广告很快就习以为常,视而不见了。
除了学业外,打工、旅游成了我在瑞士生活的第二职业,有时打工和旅游两不误,更让我体验到了一种乐不思蜀的感觉。有一次,为一家培训机构派发培训小广告,一天就要跑好几个城市。一会儿是人来人往的闹市,一会儿是幽静的莱芒湖畔,一会儿又是爬半个小时才有一户人家的美丽山地。虽然腿脚受累,却真正领略了瑞士的如画风光。
一年的进修时间很快就要结束了,我开始打点行装,准备回国。一天,我收拾行李到深夜,感觉有点疲劳,又有点心神不定,就来到公寓的前厅,打开电视,准备休息片刻。夜静极了,只听到不远处莱芒湖水有节奏的拍岸声响。公寓的学生都已经入睡,我把电视的音量调到了最低,信手选了一个频道。广告,广告,广告,还是广告……没有停顿,一连串的广告。鬼使神差,不知道为什么,我竟然没有换频道,而是呆呆地看了下去。我什么也听不见,耳边只有湖水悠缓低沉的撞击声,一浪接着一浪。广告,广告,广告……没完没了,过瘾之极!我当时不知道这是什么节目,也不知道世界上还有什么“饕餮之夜”,更不知道这是法国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转播“饕餮之夜”,但我的眼睛再也没有离开过这个散发着魔力的广告世界。
窗外渐渐亮了起来,街面上也开始有了动静。终于,公寓的清洁女工来了,她看上去无精打采,而我也是一脸疲惫,但一浪接一浪的广告狂潮让我的大脑始终处于极度的亢奋状态。女工见我这么早就起来看电视,很惊讶。互道早安后,为了不妨碍她的清洁工作,我只好起身回房间了。就在我关电视的一刹那,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一个压抑不住的念头像浪潮一样不停地向我撞来:去法国,学广告!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更多>>
本栏下载排行
│- 229494次因为痛,所以叫青春
- 153619次人性的弱点
- 92588次追寻生命的意义
- 91890次谁的青春不迷茫
- 91051次男人:如何洞悉女人...
- 88504次高效人生的12个关键点
- 73846次心理学与生活
- 71076次不抱怨的世界
- 68204次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 67839次拖延心理学
更多>>
随机推荐
│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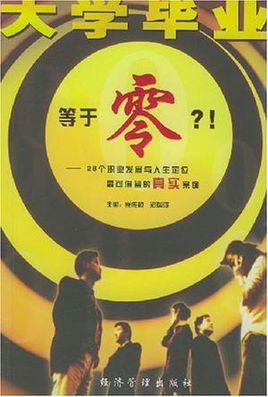 作者:崔传桢(当代)
作者:崔传桢(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