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苏联神经科学家卢瑞亚,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目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师的同时,也成为了着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谭普·格兰丁。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去年的一部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 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更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四十四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是萨克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因为写这篇序的缘故,仔细阅读了奥利弗·萨克斯的生平,发现其实我早就与他有些联系。萨克斯的研究理念,可以说师承苏联神经科学家卢瑞亚,而这位前辈,曾经因为在大脑皮层功能研究领域的探索性研究,被我三年前的博士论文多次引用。
四五十年前,关于神经系统可塑性的研究,还远没有现在这么深入,大脑内“神经线路”的联系,一旦固定还能否改变,还没有一个笃定的结论。卢瑞亚和萨克斯认定大脑有“卓越的可塑性、惊人的适应能力”,而且这些“不仅仅是在神经或感知障碍的这种特殊(而且经常是令人绝望的)环境下才会出现”,他们主张不单单要面对来问诊的病人,更要看到处在日常生活环境中的病人。这些见地,在当时的情境下,可谓先锋。
萨克斯和卢瑞亚的交情,始于1974年前后的一段通信。那年萨克斯在挪威的一个边远山区,遭遇了一头愤怒的公牛,情急之下他急转逃生,一脚踩空,左腿肌腱断裂,神经损伤,造成了严重的残疾。他慢慢发现这条腿仿佛不再是自己身体的一部分,奇异的遭遇让他以一个病人的视角审视自己的身体和心理。他将之称为“医学的机缘”。正是因为这个机缘,他和卢瑞亚讨论起人体的整体机能,关于个体和环境的联系。卢瑞亚鼓励说“你正在揭示一个全新的领域”,这样的信件给了他极大的支持。
萨克斯的这段遭遇,后来被写成《单腿站立》一书,于1984年出版。事实上,从1973年起,他就开始以亲身的医患经历,写作了一系列的“医疗轶事”,《觉醒》、《错把妻子当帽子》,这些都成为世界范围的畅销书。他将病患案例文学化,将虚构与真实融为一体,饱含同情,着力描写患者的各种身心体验,给读者打开一道通往奇异世界之门。这一系列的书,获得了极大成功,被翻译成多国语言。萨克斯目前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作为顶尖医师的同时,也成为了着名的畅销书作家,被称为“脑神经文学家”,被《纽约时报》誉为“医学桂冠诗人”。
萨克斯的书中描写了很多例“病感失认症”,这也是我最感兴趣的话题。由于中风或其他原因,病人可能无法辨认自己身体的一部分,甚至觉得那是别人的。他们会在火车上指着自己的手对邻座说:“对不起,先生,您把手放在我膝盖上了。”即便被旁人提醒,这些可怜的病人都很难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对自己身体的错误感知,有时会发展到匪夷所思的地步。记得英国《卫报》曾有个记者写到自己的遭遇,他有天早晨起来,感觉“自己跟电视机遥控器一样高”,“脚陷进了地毯里”。此后,他时不时被猛然抛进童话世界:手指变得有半里长,走到街上,路旁的车看起来像威尔士矮脚狗那么大。有时办公的时候,身体突然缩小,椅子变得好大,感觉自己就好像走进了仙境的爱丽丝。还记得阿兰·德波顿描写过一个家伙,他把自己当做一个煎蛋,始终不敢坐在椅子上,后来有个朋友出了个招,在椅子上放了块面包。如此,他终于肯把自己像三明治一样放在椅子上了。
萨克斯将神经病学的理论和案例深入浅出地写进书里,既轻盈又沉厚。本来,神经病患,在普通人看来是一类与自己很少发生关联的遥远而陌生的群体。萨克斯以客观平等的态度看待他们,与他们交流,在书中展现了他们的心灵世界。那是另外一个伟大而奇异的境界。每一个患者,其实都有自己独特的、值得尊重的人格世界,有着我们未必能够达到的宁静和辽远,甚至是通透。
每一本萨克斯医生的书都可当做非常精彩的医学传奇集。《错把妻子当帽子》展现了24个脑神经失序的患者,这本书大多数讲述的是“白痴天才(或称白痴学者)”的事迹。这些故事以前所未有的高度告诉我们,“病”这种东西,未必是生命中不可承受之重。缺陷、不适与疾病,会产生出另一些发展、进化与生命的形态,激发出我们远不能预料的创造力。普通读者能通过阅读这些故事感受到人类心智活动的繁复和奇妙,更能以新的眼光重新发现日常与人生。《火星上的人类学家》描写的则是另一种“变形记”。书名同题文写的则是一位自闭症患者、杰出的动物行为科学家谭普·格兰丁。一方面,她有韧性、真诚、坦率、非常敏锐,然而,另一方面,由于病症带来的情感缺陷,使得她在感知情绪时会有障碍,在社交中常感困惑。文中也提到阿斯伯格综合征——因为去年的一部动画片《玛丽与麦克斯》 而让影迷们熟知的病症。阿斯伯格综合征和自闭症的关系,学界尚不是很清楚,两者有类似的症状,例如人际交往障碍、刻板、重复的兴趣、自我中心。然而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更不易被发现,他们在外在表现上很难与正常人区分开。影片中的麦克斯就是一个四十四岁的肥胖古怪的阿斯伯格综合征患者,不擅长交际却又渴望温情。我们自认为是正常的地球人,将这些病人视为“火星人”,其实我们又何尝不被他们当做是“外星人”呢?又何尝不处处表现出怪异的举动呢?这正是萨克斯想告诉读者的。
萨克斯的“小说”谈的不仅仅是猎奇的故事,他探讨的是人性的无限可能性,人与人之间微妙的超越我们现有认知的关系,他希望“火星人”与地球人相互了解,相互表达。这是萨克斯文学的珍贵之处,也是中信出版社这套书的珍贵之处。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更多>>
本栏下载排行
│- 240574次因为痛,所以叫青春
- 161355次人性的弱点
- 99172次追寻生命的意义
- 96539次男人:如何洞悉女人...
- 93648次谁的青春不迷茫
- 91787次高效人生的12个关键点
- 79142次心理学与生活
- 72946次高效能人士的七个习惯
- 72214次不抱怨的世界
- 71202次拖延心理学
更多>>
随机推荐
│
更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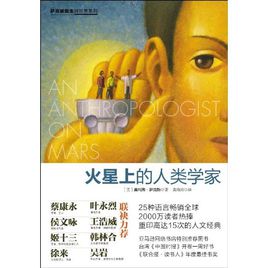 作者:奥利弗·萨克斯(美)
作者:奥利弗·萨克斯(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