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孩子被缠绕在腰间的蜷曲的蛇弄醒了。有那么一会儿他很害怕,它压迫着他的呼吸,让他做恶梦,但是当他彻底醒来,他认出了它是谁,他把两只手伸进它的圈套,它改变了姿势,缠在他背上的力量收紧了,又渐渐变弱,蛇头从肩膀滑过他的脖子,然后他感觉到那嘶嘶作响的舌头紧贴着他的耳朵。
描画着玩保龄球和看斗鸡的男孩子们的老式夜灯,闪动着黯淡的火苗,他睡着的时候黄昏已经过去,冷冷的月光从高高的窗子里射进来,在黄色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痕迹。他掀开毯子看那条蛇,顺便确定它是哪一条。他的母亲曾告诉他,有条背上的花纹好像织物的花蛇,最好别去碰它。但是还好,这是那条淡棕色灰腹蛇,它的鳞片像珐琅般光滑
大概是一年前,当他满四岁的时候,他得到一张五尺长的男孩用的床,腿很短以防他从上面跌下来。蛇很容易就能爬上来。房间里的所有其他人都很快进入了梦乡,他的妹妹克里欧佩特拉睡在斯巴达保姆身边的摇篮里,不远处,一张更精致的刻花梨木床上,是他自己的保姆赫拉尼克,现在一定是午夜了,但是他还是能听到大厅里男人们的嘈杂声音,虽然模糊不清,但是他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这条蛇是个秘密,他自己的夜晚的秘密,即便是睡的那么近的赫拉妮克也没有发现它沉默的致意。她在打呼噜,因为把这声音比作石匠的锯声,他挨过一巴掌。赫拉妮克不是普通的保姆,而是一位具有王室血统的夫人,她老是对他说,她不会这么照料任何一个他父亲的儿子之外的孩子
鼾声和远处传来的歌声,都沉落在寂静里,只有他和那条蛇醒着,哨兵在通道里来回巡逻,他经过门口的时候能听到他的盔甲锵锵作响
孩子翻了个身,抚摸着那条蛇,用手指感觉着它光滑有力的躯体,它把它扁平的头放在他的胸口,一开始很凉,把他弄醒了,现在它从他身上得到了温暖,慵懒起来,要睡觉了,也许就这么一直待到早晨。如果赫拉妮克发现了它会说什么?他忍着笑想着,起码会吓个半死然后跑开。他从来没见它这么远从他母亲的房间跑过来。
他倾听着她是否派遣使女出来找它,它的名字是格劳克斯,但是他只听见两个男人在大厅里对骂,和他父亲的大嗓门,叫他们两个都闭嘴。
他在头脑里描绘着她的样子,穿着带黄色宽边白色羊毛长袍,她沐浴后总是穿成这样,油灯在她的左手里闪动着红光,她轻柔地唤着:“格劳克斯,”也许她会用她的小骨笛吹起蛇曲。使女们会到处寻找,从梳妆台底下,化妆盒,到里面散发着肉桂气味的铜皮包裹的衣柜。他曾见过她们为了找一只丢失的耳环如此大动干戈,她们会又害怕又笨拙,而她会很生气,大厅里又传来喧哗声,他想起他父亲不喜欢格劳克斯,它走丢了他会很高兴的。
他会把它带回给她,他自己。
他一定要这么做,孩子站在黄色的地板上那道月光中,蛇缠在他身上,它肯定不喜欢被衣服打扰,但是他拿起他的斗篷,把他们俩裹起来好保持暖和
他停下来想了想,他得避开两个士兵,就算他们都很友好,在这个时间他们也会拦住他。他听到他们中的一个就在门外。他要穿过走廊,拐角处有个储存室,哨兵同时看管着这两道门。
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把门打开一条缝,向外张望并盘算着他的计划。墙角有一尊青铜的阿波罗,安放在绿色大理石底座上。他的个子小的足以躲在后面,等到哨兵走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就跑开,剩下的很简单,他只要跑到那个有着通往国王卧室的楼梯的院子里就行了。
楼梯两边的墙上画着树和鸟,卧室门前有一块空地,闪亮的大门的门环衘在狮子嘴里,大理石地面光洁如新,在阿格劳斯国王*的时代,这里不过是个泻湖边的小港口,现在却是拥有庙宇和巨大宫殿的城市了,阿格劳斯国王在这里盖起他著名的,对全希腊来说都是个奇迹的宫殿。它太著名了以至于不必作任何改变,虽然过了五十年还是尽善尽美,朱克斯花了多年时间来为它画壁画
[*阿格劳斯国王413BC-399BC,在位期间把首都迁往派拉,大力发展希腊文化,欧里匹得斯写过一出悲剧献给他]
楼梯脚下站着第二名哨兵,王家卫士阿格斯,他靠在他的长矛上悠闲地站着,孩子在黑暗的走廊里窥探并等待着。
阿格斯大约二十岁,是位宗室领主的儿子,他全副武装等待着国王,他的头盔上飘拂着着红白交织的马鬃,护颊上装饰着狮子浮雕,他的盾牌上画着一只昂首阔步的公山猪,盾牌挂在他的肩膀上,在国王安全归寝之前是不能放下来的,当然在这之前也不能放下武器,他的右手里有一只七尺长矛。
孩子开心地张望着,他感到那条蛇在斗篷底下柔软地扭动着,他认识这个年轻人,他应该怪叫着跳出来,让他在惊慌中扔开盾牌,把长矛举得像那束马鬃那么高。但是阿格斯在值班,将会是他敲来那扇门把格劳克斯交给使女们,然后把他送回赫拉尼克那里。他从前试过夜里溜进来,虽然从未这么晚,他们总是告诉他除了国王谁也不可以进入。
通道的地面是用黑白相间的拼成图案的卵石铺成的,他的脚被硌疼了,夜晚越来越冷,阿格斯要去视察楼梯,想绕过他可比绕过那一个哨兵难多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考虑应该走出来,和阿格斯聊几句,然后回去。但是靠在他胸口的蛇提醒他他是来看他母亲的。因此,他该怎么办?
人们一心一意想要办成什么事的话,机会自然出现。格劳克斯是条有魔力的蛇,他举起它细小的蛇头,无声地念诵着“Agathodaimon, Sabazeus-Zagreus,让他离开,来吧,来吧,”他加上了一条曾听他母亲念诵过的咒语,虽然他不明白它的意义,只是值得一试。
阿格斯穿过楼梯,向与走廊相反的方向走去。不远处有尊雕像,是只蹲着的狮子,阿格斯把他的长矛和盾牌靠在上面,绕到后面。按照当地的标准,他还算没大醉,但是他值班前喝了不少,很难坚持到下一个哨兵接班。所有的士兵都去狮子雕像后面解决,天亮前奴隶们就会清理干净。
他正抬步走向那边,在他放下武器之前,孩子发现机会来了,开始向前跑,他悄无声息地跑过冰冷光滑的楼梯。
阿格斯躲在狮子后面也没有忘记他的职责,当看门狗叫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回头看去,但是这声音来自另一个方向,继而停止了,他弄平他的衣服,拿起武器,楼梯空荡荡的
孩子躲过了他的眼睛,悄悄打开沉重的大门,然后去系上门闩。门闩很光滑,涂满了油,他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转身进屋。
只有一盏油灯在高高的装饰着镀金葡萄藤和鹿脚的青铜灯柱上闪烁着,房间里很暖和,笼罩着私密的气息,边缘刺绣的深蓝色羊毛窗帘,画在墙上的人像,都在幽暗中浮动,油灯的火苗摇曳着,男人的吵闹声隔着厚厚的门听上去只是一阵低语。
这里有一股沐浴油膏的香气,香料和麝香,还有青铜壁炉旁边篮子里散发着松香味的灰烬,和他母亲那些从雅典运来的装满油彩和油膏的小瓶子的香气,她为了展示魔法而焚烧的什么辛辣的东西,她的头发和身体的气味,床上伸展着一条带着象牙镯子的腿,她睡着了,她的头发散落早亚麻枕套上,他从未见过她沉睡的样子。
她看上其根本没发现格劳克斯走丢了,睡的很沉,他停在那儿,享受着这偷偷摸摸的不受打扰的占有。她橄榄木的桌子上,瓶瓶罐罐整齐地摆放着,一个镀金的水仙像托着她的银镜子,藏红色的寝袍叠好放在矮凳上。房间的一角传来她的使女微弱的鼾声。他的目光移向壁炉边的一块松动的石头,底下藏着禁忌之物,他有时很希望自己也能拥有魔法。
但是格劳克斯会溜走,他现在就得叫醒她。
他轻轻走了国去,像个看不见的守卫,或是她的梦乡的国王。镶着鲜红镶边,环饰着扣子的貂皮轻柔地盖在她身上,随着她的呼吸起伏。她淡淡的眉毛下方是光洁的眼睑,几乎能透过它们看到她的灰眼睛,她的睫毛又黑又浓,她的嘴紧闭着,颜色像掺了水的酒,她的鼻子挺直,发出轻微的呼吸声,她刚刚21岁。
貂皮被子从她的胸口滑落下去一点,不久前,克里欧佩特拉还时常把头靠在那里,她最近才被送到斯巴达保姆那里,现在这怀抱又属于他了。
一绺头发落在他脸上,深红色,硬硬的,在油灯的火光中闪闪发亮。他拉过一绺他自己的头发,把它们放在一起,他的头发就像未融炼的黄金,闪亮沉重,莱尼克过节的时候抱怨说,恐怕它们永远不会变成卷发了。她的头发就像波浪一样,克里欧佩特拉的斯巴达保姆说她的也一样,显然不像父亲,他会因此讨厌她。也许她会死掉,婴儿们很容易死去。
他看着里面墙上的巨大的壁画,特洛伊的毁灭,是朱克斯为 阿格劳斯国王画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人大小。背景里是巨大的木马,前面希腊人用剑屠杀着特洛伊人,向他们投掷长矛,或是把大张着嘴尖叫着的妇女扛在肩头,在最醒目的地方是老普莱阿姆和年幼的阿斯提阿那克斯倒在他们的血泊里。他很喜欢那色彩,他就出生在这屋子里,这幅画对他而言一点不新奇。
缠着他的腰,在他的斗篷底下,格劳克斯正在蠕动,毫无疑问是为回到老巢感到高兴,孩子又看了看他母亲的脸,然后甩开他唯一的那件衣服,掀起被子那精致的镶边,身上还缠着那条蛇躺在她身边。
她的胳膊环绕着他,她轻声嘟囔着,把她的鼻子和嘴唇埋在他的头发里,她的呼吸声更低沉了,他把头抵在她的下巴底下,她柔软的胸脯拥着他,他能感觉到他的皮肤擦过她的,蛇夹在他们之间太紧了,使劲地蠕动着爬走了。
他感到她醒了过来。他向上看的时候遇到了她的灰眼睛。她吻了他,抚摸他,问他是谁放他进来的。
她还半睡半醒,他已经准备好这个问题的答案。阿格斯没好好履行职责,士兵们会因为这个受罚,半年前他从窗口看到一个士兵在操场上被其他卫兵处死,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他已经忘了那罪名,如果他当时就知道的话。但是他还记着远处那具被绑在木桩上的躯体,举着标枪的人围成一圈,随着一声令下,一声惨叫响起,那头颅耷拉下拉,地面上一大滩鲜血。
“我告诉哨兵你想见我,”不需要提及名字,作为一个爱讲话的孩子,他已经知道如何管好自己的舌头。
她的脸颊动了动,贴在他头上,他很少听到她对父亲说话的时候不撒谎的,他想这也许也是她的魔术之一,就像用骨笛吹奏蛇曲。
描画着玩保龄球和看斗鸡的男孩子们的老式夜灯,闪动着黯淡的火苗,他睡着的时候黄昏已经过去,冷冷的月光从高高的窗子里射进来,在黄色大理石地板上留下一道深色的痕迹。他掀开毯子看那条蛇,顺便确定它是哪一条。他的母亲曾告诉他,有条背上的花纹好像织物的花蛇,最好别去碰它。但是还好,这是那条淡棕色灰腹蛇,它的鳞片像珐琅般光滑
大概是一年前,当他满四岁的时候,他得到一张五尺长的男孩用的床,腿很短以防他从上面跌下来。蛇很容易就能爬上来。房间里的所有其他人都很快进入了梦乡,他的妹妹克里欧佩特拉睡在斯巴达保姆身边的摇篮里,不远处,一张更精致的刻花梨木床上,是他自己的保姆赫拉尼克,现在一定是午夜了,但是他还是能听到大厅里男人们的嘈杂声音,虽然模糊不清,但是他明白他们在干什么。
这条蛇是个秘密,他自己的夜晚的秘密,即便是睡的那么近的赫拉妮克也没有发现它沉默的致意。她在打呼噜,因为把这声音比作石匠的锯声,他挨过一巴掌。赫拉妮克不是普通的保姆,而是一位具有王室血统的夫人,她老是对他说,她不会这么照料任何一个他父亲的儿子之外的孩子
鼾声和远处传来的歌声,都沉落在寂静里,只有他和那条蛇醒着,哨兵在通道里来回巡逻,他经过门口的时候能听到他的盔甲锵锵作响
孩子翻了个身,抚摸着那条蛇,用手指感觉着它光滑有力的躯体,它把它扁平的头放在他的胸口,一开始很凉,把他弄醒了,现在它从他身上得到了温暖,慵懒起来,要睡觉了,也许就这么一直待到早晨。如果赫拉妮克发现了它会说什么?他忍着笑想着,起码会吓个半死然后跑开。他从来没见它这么远从他母亲的房间跑过来。
他倾听着她是否派遣使女出来找它,它的名字是格劳克斯,但是他只听见两个男人在大厅里对骂,和他父亲的大嗓门,叫他们两个都闭嘴。
他在头脑里描绘着她的样子,穿着带黄色宽边白色羊毛长袍,她沐浴后总是穿成这样,油灯在她的左手里闪动着红光,她轻柔地唤着:“格劳克斯,”也许她会用她的小骨笛吹起蛇曲。使女们会到处寻找,从梳妆台底下,化妆盒,到里面散发着肉桂气味的铜皮包裹的衣柜。他曾见过她们为了找一只丢失的耳环如此大动干戈,她们会又害怕又笨拙,而她会很生气,大厅里又传来喧哗声,他想起他父亲不喜欢格劳克斯,它走丢了他会很高兴的。
他会把它带回给她,他自己。
他一定要这么做,孩子站在黄色的地板上那道月光中,蛇缠在他身上,它肯定不喜欢被衣服打扰,但是他拿起他的斗篷,把他们俩裹起来好保持暖和
他停下来想了想,他得避开两个士兵,就算他们都很友好,在这个时间他们也会拦住他。他听到他们中的一个就在门外。他要穿过走廊,拐角处有个储存室,哨兵同时看管着这两道门。
脚步声渐渐远去,他把门打开一条缝,向外张望并盘算着他的计划。墙角有一尊青铜的阿波罗,安放在绿色大理石底座上。他的个子小的足以躲在后面,等到哨兵走向另一边的时候他就跑开,剩下的很简单,他只要跑到那个有着通往国王卧室的楼梯的院子里就行了。
楼梯两边的墙上画着树和鸟,卧室门前有一块空地,闪亮的大门的门环衘在狮子嘴里,大理石地面光洁如新,在阿格劳斯国王*的时代,这里不过是个泻湖边的小港口,现在却是拥有庙宇和巨大宫殿的城市了,阿格劳斯国王在这里盖起他著名的,对全希腊来说都是个奇迹的宫殿。它太著名了以至于不必作任何改变,虽然过了五十年还是尽善尽美,朱克斯花了多年时间来为它画壁画
[*阿格劳斯国王413BC-399BC,在位期间把首都迁往派拉,大力发展希腊文化,欧里匹得斯写过一出悲剧献给他]
楼梯脚下站着第二名哨兵,王家卫士阿格斯,他靠在他的长矛上悠闲地站着,孩子在黑暗的走廊里窥探并等待着。
阿格斯大约二十岁,是位宗室领主的儿子,他全副武装等待着国王,他的头盔上飘拂着着红白交织的马鬃,护颊上装饰着狮子浮雕,他的盾牌上画着一只昂首阔步的公山猪,盾牌挂在他的肩膀上,在国王安全归寝之前是不能放下来的,当然在这之前也不能放下武器,他的右手里有一只七尺长矛。
孩子开心地张望着,他感到那条蛇在斗篷底下柔软地扭动着,他认识这个年轻人,他应该怪叫着跳出来,让他在惊慌中扔开盾牌,把长矛举得像那束马鬃那么高。但是阿格斯在值班,将会是他敲来那扇门把格劳克斯交给使女们,然后把他送回赫拉尼克那里。他从前试过夜里溜进来,虽然从未这么晚,他们总是告诉他除了国王谁也不可以进入。
通道的地面是用黑白相间的拼成图案的卵石铺成的,他的脚被硌疼了,夜晚越来越冷,阿格斯要去视察楼梯,想绕过他可比绕过那一个哨兵难多了。
有那么一会儿他考虑应该走出来,和阿格斯聊几句,然后回去。但是靠在他胸口的蛇提醒他他是来看他母亲的。因此,他该怎么办?
人们一心一意想要办成什么事的话,机会自然出现。格劳克斯是条有魔力的蛇,他举起它细小的蛇头,无声地念诵着“Agathodaimon, Sabazeus-Zagreus,让他离开,来吧,来吧,”他加上了一条曾听他母亲念诵过的咒语,虽然他不明白它的意义,只是值得一试。
阿格斯穿过楼梯,向与走廊相反的方向走去。不远处有尊雕像,是只蹲着的狮子,阿格斯把他的长矛和盾牌靠在上面,绕到后面。按照当地的标准,他还算没大醉,但是他值班前喝了不少,很难坚持到下一个哨兵接班。所有的士兵都去狮子雕像后面解决,天亮前奴隶们就会清理干净。
他正抬步走向那边,在他放下武器之前,孩子发现机会来了,开始向前跑,他悄无声息地跑过冰冷光滑的楼梯。
阿格斯躲在狮子后面也没有忘记他的职责,当看门狗叫起来的时候,他马上回头看去,但是这声音来自另一个方向,继而停止了,他弄平他的衣服,拿起武器,楼梯空荡荡的
孩子躲过了他的眼睛,悄悄打开沉重的大门,然后去系上门闩。门闩很光滑,涂满了油,他毫不费力地完成了,转身进屋。
只有一盏油灯在高高的装饰着镀金葡萄藤和鹿脚的青铜灯柱上闪烁着,房间里很暖和,笼罩着私密的气息,边缘刺绣的深蓝色羊毛窗帘,画在墙上的人像,都在幽暗中浮动,油灯的火苗摇曳着,男人的吵闹声隔着厚厚的门听上去只是一阵低语。
这里有一股沐浴油膏的香气,香料和麝香,还有青铜壁炉旁边篮子里散发着松香味的灰烬,和他母亲那些从雅典运来的装满油彩和油膏的小瓶子的香气,她为了展示魔法而焚烧的什么辛辣的东西,她的头发和身体的气味,床上伸展着一条带着象牙镯子的腿,她睡着了,她的头发散落早亚麻枕套上,他从未见过她沉睡的样子。
她看上其根本没发现格劳克斯走丢了,睡的很沉,他停在那儿,享受着这偷偷摸摸的不受打扰的占有。她橄榄木的桌子上,瓶瓶罐罐整齐地摆放着,一个镀金的水仙像托着她的银镜子,藏红色的寝袍叠好放在矮凳上。房间的一角传来她的使女微弱的鼾声。他的目光移向壁炉边的一块松动的石头,底下藏着禁忌之物,他有时很希望自己也能拥有魔法。
但是格劳克斯会溜走,他现在就得叫醒她。
他轻轻走了国去,像个看不见的守卫,或是她的梦乡的国王。镶着鲜红镶边,环饰着扣子的貂皮轻柔地盖在她身上,随着她的呼吸起伏。她淡淡的眉毛下方是光洁的眼睑,几乎能透过它们看到她的灰眼睛,她的睫毛又黑又浓,她的嘴紧闭着,颜色像掺了水的酒,她的鼻子挺直,发出轻微的呼吸声,她刚刚21岁。
貂皮被子从她的胸口滑落下去一点,不久前,克里欧佩特拉还时常把头靠在那里,她最近才被送到斯巴达保姆那里,现在这怀抱又属于他了。
一绺头发落在他脸上,深红色,硬硬的,在油灯的火光中闪闪发亮。他拉过一绺他自己的头发,把它们放在一起,他的头发就像未融炼的黄金,闪亮沉重,莱尼克过节的时候抱怨说,恐怕它们永远不会变成卷发了。她的头发就像波浪一样,克里欧佩特拉的斯巴达保姆说她的也一样,显然不像父亲,他会因此讨厌她。也许她会死掉,婴儿们很容易死去。
他看着里面墙上的巨大的壁画,特洛伊的毁灭,是朱克斯为 阿格劳斯国王画的,里面的东西都是真人大小。背景里是巨大的木马,前面希腊人用剑屠杀着特洛伊人,向他们投掷长矛,或是把大张着嘴尖叫着的妇女扛在肩头,在最醒目的地方是老普莱阿姆和年幼的阿斯提阿那克斯倒在他们的血泊里。他很喜欢那色彩,他就出生在这屋子里,这幅画对他而言一点不新奇。
缠着他的腰,在他的斗篷底下,格劳克斯正在蠕动,毫无疑问是为回到老巢感到高兴,孩子又看了看他母亲的脸,然后甩开他唯一的那件衣服,掀起被子那精致的镶边,身上还缠着那条蛇躺在她身边。
她的胳膊环绕着他,她轻声嘟囔着,把她的鼻子和嘴唇埋在他的头发里,她的呼吸声更低沉了,他把头抵在她的下巴底下,她柔软的胸脯拥着他,他能感觉到他的皮肤擦过她的,蛇夹在他们之间太紧了,使劲地蠕动着爬走了。
他感到她醒了过来。他向上看的时候遇到了她的灰眼睛。她吻了他,抚摸他,问他是谁放他进来的。
她还半睡半醒,他已经准备好这个问题的答案。阿格斯没好好履行职责,士兵们会因为这个受罚,半年前他从窗口看到一个士兵在操场上被其他卫兵处死,过了这么久的时间,他已经忘了那罪名,如果他当时就知道的话。但是他还记着远处那具被绑在木桩上的躯体,举着标枪的人围成一圈,随着一声令下,一声惨叫响起,那头颅耷拉下拉,地面上一大滩鲜血。
“我告诉哨兵你想见我,”不需要提及名字,作为一个爱讲话的孩子,他已经知道如何管好自己的舌头。
她的脸颊动了动,贴在他头上,他很少听到她对父亲说话的时候不撒谎的,他想这也许也是她的魔术之一,就像用骨笛吹奏蛇曲。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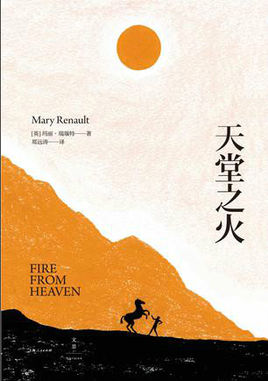 作者:玛丽·瑞瑙特(英)
作者:玛丽·瑞瑙特(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