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言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这本书谈战国五子,按照活动年代的顺序排列是:墨子、孟子、庄子、荀子、韩非子。
正如许多西方学者所说,中华帝国是孔夫子和秦始皇缔造的。而上述五位活动的年代,恰好是孔子去世之后,始皇帝统一之前。他们是大变革时代的革命党与保守派,是那个社会背景下的先锋与公知。
而所谓“公知”是“公共知识分子”的简称,在这个词还没有像现在这么火爆并充满贬义之前,它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摘抄余英时先生的解释:
今天西方人常常称知识分子为“社会的良心”,认为他们是人类的基本价值(如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这里所用的“知识分子”一词在西方是具有特殊涵义的,并不是泛指一切有“知识”的人。这种特殊涵义的“知识分子”首先也必须是以某种知识技能为专业的人:他可以是教师、新闻工作者、律师、艺术家、文学家、工程师、科学家或任何其他行业的脑力劳动者。但是如果他的全部兴趣始终限于职业范围之内,那么他仍然没有具备“知识分子”的充足条件。根据西方学术界的一般理解,所谓“知识分子”,除了献身于专业工作以外,同时还必须深切地关怀着国家、社会,以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之事。而且这种关怀又必须是超越于个人(包括个人所属的小团体)的私利之上的。(《士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地位》)
余先生又说:“熟悉中国文化史的人不难看出,西方学人所刻画的‘知识分子’的基本性格竟和中国的‘士’极为相似。”
确实,以专业知识而论,谁要是夸说诸子今天还如何了得,只能推断为别有用心。但不可否认,那时的许多问题,还是今天的问题。
以韩非子为例。
先秦,中国思想史的黄金时代。在最有名的七子里面,按年代排,韩非是殿军。韩非看前面六位都不太顺眼;相应的,在怎么跟领导人谈心的问题上,韩非一副进退失据、左右为难的小媳妇相,在那六位那里,大概也很难引起共鸣。
而这六位亦是各有各的个性。
《老子》这书,自说自话。一个老爷子面无表情地在念叨,语音语调从头到尾没有抑扬顿挫,爱听不听,不听拉倒。
孔子是低调的,主张跟领导说话要客气,但原则问题不让步。他认为国家领导人听不进不同意见就该亡国,跟你说不通我就自己辞职走人。并且,看《论语》的记录,孔子评价起国君或官员们来,态度常常也并不像他主张的那样谦恭。
墨子很自恋,觉得就他最牛。即使全世界都在反驳他,在他看来也不过是集中天下的鸡蛋砸石头。《墨子》书里记录他和别人的辩论,都透着这股子气势,和国君说话,也不例外。
孟子也嚣张。“道高于君”是他的基本立场,“说大人,则藐之,毋视其巍巍然也”是他的基本态度,“帝王师”是他的基本定位。所以人家问他,咱们大王对您很客气,您对他就不能尊敬点吗?他的回答竟是:“我经常把尧舜之道讲给他听,不就是对他最大的尊敬吗?”
庄子更不必说。庄子稀罕跟国家领导人说话吗?答案当然是否定的。既然如此,那领导不爱听,他当回事吗?
韩非的老师荀子,讲究“尊王”,倒也是特别强调要突出领导权威的。但他一张嘴仍然会说,你们这些国君拿齐桓公、晋文公当奋斗目标,但我们孔门弟子,就算只是个小孩子,都觉得谈这个丢人。
总之,“凡说之难,在知所说之心,可以吾说当之”这个韩非看来最大的难题,在这六位心目当中,根本就不存在。
道理也很简单。这老六位就算各有各的毛病,起码有一点是共通的。他们都怀揣理想,拿自己当人,希望按照自己的主张来塑造国君。自居奴才,为讨主子欢心而变着花样说话,他们不但做不出,甚至根本想不到。
有意思的是,那些一心干禄,比韩非还要以国君的是非为是非的纵横家和法家实践派,也没把游说看得这么难。
苏秦、张仪不必说了,各国国君一路忽悠过来,一点都不怯。
韩非的同门李斯,胆色也一样可观。《谏逐客书》开门见山,“臣闻吏议逐客,窃以为过矣”,批评新国策不对,一点没绕弯子。这篇的行文,也正是韩非说的“顺比滑泽,洋洋洒洒”,尤其是后半篇,“华而不实”的嫌疑着实不小。但人家也成功了。
韩非和这帮子人的巨大差异,也许可以从出身上来解释。
韩非是“韩之诸公子”。韩国是一个不强大,但还算是大国的国家;“诸公子”的意思,是一个不算高贵,但还说得过去的贵族。
章太炎骂老子,有句名言叫“怯懦者多阴谋”,拿到韩非身上更合适。没行动力,各种阴谋诡计只能一遍遍过脑子,所以韩非这方面的研究特别有水平。真的耍流氓,韩非在秦始皇面前一和李斯、姚贾交锋,三招两式就败了,皇帝也不再把他当回事。
太史公为韩非立传,没写几句话,倒全文引录《说难》。因为他亦有同感。
那是汉武帝的时代。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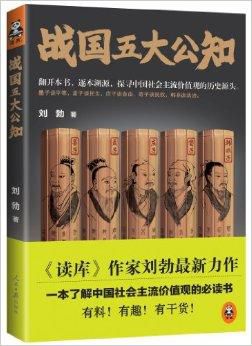 作者:刘勃(战国)
作者:刘勃(战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