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辑缘起
孔子“修”《春秋》,创造“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是中国历史篡改史的开端。宗周内乱,周室典籍被人携出后杳无下落,是古代典籍之又一大劫。秦始皇并六国,焚书坑儒,是古代典籍之又一大劫。此三劫过后,兵燹,水淹,火焚……天灾比不上人祸,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们,或出于政治合法性的延续,或出于对末日的莫名恐惧,纷纷操纵刀笔之吏,模仿“先圣”,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居然使秉笔直书的“董狐笔”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所谓“史”,乃客观记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竟不可得;所谓“史官”,本应独立的职业,竟成为朝廷豢养的宠物,或危险运命的渊薮。
因此鲁迅先生说中国史是“瞒和骗”的历史;一部二十四史,无非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因此学者和政客们才斗胆敢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中国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长于健忘,轻易地抹去血痕,陷入历史循环论的泥沼。
但是—正如阉割尚有不净,罗网尚有漏鱼,百密难免一疏,“官方净化”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漏洞,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此之谓“历史的后门”。
加盟的作者,或构建体系,或符号学分析;或考据,或文本细读;即或轻薄为文,嬉笑怒骂,亦有一种“史见”在里面,读者或可明鉴。
是为缘起。
第一章 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张生(名珙,字君瑞,西洛人氏),第一代流氓才子的集大成者,《西厢记》的横空出世,遂成竖子之名。西厢花下,朗月当头,浪子张生揭竿而起,吹起了向古典爱情总攻的号角。有关爱情的虚无主义理想在张生明确的功利思想的凌厉攻势之下,顿如美国双子世贸大楼一样土崩瓦解。立在唐宋传奇和元杂剧深处的张生绣口轻吐,一下就淹没了盛唐。因此,与其说《西厢记》是浪漫爱情的礼赞,毋宁说它是浪漫爱情的挽歌。
又一个起点
我必须充满惭愧地承认,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长久地为《西厢记》的诲淫诲盗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虚伪光辉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觉。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诲淫诲盗和皆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两极,而两极的连接处却是我们的盲点。《西厢记》高度符号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为另一面的能指被我们忘却了。
第二章 一群苍蝇在莺莺身边飞
张生
张生的作派在《西厢记》里妩媚而阴柔。刚出场的张生像历代的书生一样,无疑是病弱的,他无比自怜地这样自我评价:“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文章与飘零的张力在张生身上难堪地对峙着,并要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之前,可怜而可爱的张生只能是“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飘零的价值最终会找到归宿;而在此之前,对张生飘零的第一个奖励在普救寺里露出了端倪—如同上苍注定,张君瑞命带桃花,普救寺中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向张生展示了意外的美丽和妖艳。也就是在此时,张生的满腹文章悄悄派上了用场。流氓需要才气,才气成就着流氓。张生的文化流氓底色得以彻底显影并最后定影,等待他的就是如何冲洗和复制放大并上光了。
普救寺的惊艳直接催生了一首好诗:
月色溶溶夜
花木寂寂春
如何临浩魄
不见月中人
该诗可谓孤篇压全唐,足见张生的“学成满腹文章”绝非空穴来风。张生以月亮—这人世间阴柔的代表起兴,最后直抒胸臆,向着近在咫尺的月中人发出召魂令,瞬间建立起了多情的形象。你听,张生像一个流浪歌手一样唱道:寺庙的夜色多沉静,那花儿寂寞地开在春风中,我静立月下多饥渴啊,为何没有美眉来调情?张生大胆而浮夸地将煽情进行到底,其实践精神当是空前绝后。若干年前,张生的老师也咏过月亮,他说:明月照到我床前,我当是霜花和食盐,抬头我把月亮看,才知它没故乡的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比张生,老师就显得不着边际。若干年后,张生的学生就不再咏月亮了,他们只说星星,发誓要给情人“一扇朝北的窗,让他看到星斗”,有张生的诗意,但显得过于吝啬。至于郁达夫之流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怕为情多累美人”则显得自怜而变态,及至发展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里的那种欲擒故纵,那种小家子气,那种小妾般的懦弱,足见流氓才子已呈现难以挽回的退化。
孔子“修”《春秋》,创造“春秋笔法”,使乱臣贼子惧,是中国历史篡改史的开端。宗周内乱,周室典籍被人携出后杳无下落,是古代典籍之又一大劫。秦始皇并六国,焚书坑儒,是古代典籍之又一大劫。此三劫过后,兵燹,水淹,火焚……天灾比不上人祸,历朝历代的独裁者们,或出于政治合法性的延续,或出于对末日的莫名恐惧,纷纷操纵刀笔之吏,模仿“先圣”,肆无忌惮地篡改历史,居然使秉笔直书的“董狐笔”成为一个著名的典故。所谓“史”,乃客观记事的题中应有之义,在中国竟不可得;所谓“史官”,本应独立的职业,竟成为朝廷豢养的宠物,或危险运命的渊薮。
因此鲁迅先生说中国史是“瞒和骗”的历史;一部二十四史,无非是帝王将相的家谱。因此学者和政客们才斗胆敢说:历史是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因此中国才“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长于健忘,轻易地抹去血痕,陷入历史循环论的泥沼。
但是—正如阉割尚有不净,罗网尚有漏鱼,百密难免一疏,“官方净化”总会有形形色色的漏洞,刀笔吏的指缝间也常常泄露出有趣的消息。此之谓“历史的后门”。
加盟的作者,或构建体系,或符号学分析;或考据,或文本细读;即或轻薄为文,嬉笑怒骂,亦有一种“史见”在里面,读者或可明鉴。
是为缘起。
第一章 一个起点
一个起点
张生(名珙,字君瑞,西洛人氏),第一代流氓才子的集大成者,《西厢记》的横空出世,遂成竖子之名。西厢花下,朗月当头,浪子张生揭竿而起,吹起了向古典爱情总攻的号角。有关爱情的虚无主义理想在张生明确的功利思想的凌厉攻势之下,顿如美国双子世贸大楼一样土崩瓦解。立在唐宋传奇和元杂剧深处的张生绣口轻吐,一下就淹没了盛唐。因此,与其说《西厢记》是浪漫爱情的礼赞,毋宁说它是浪漫爱情的挽歌。
又一个起点
我必须充满惭愧地承认,少不更事的我曾经长久地为《西厢记》的诲淫诲盗深深陶醉,及至弱冠,《西厢记》中的“有情人皆成眷属”的虚伪光辉亦令我生出仰慕的感觉。而今年近四十,始知诲淫诲盗和皆成眷属是《西厢记》的两极,而两极的连接处却是我们的盲点。《西厢记》高度符号化的人物的所指是其一面,而作为另一面的能指被我们忘却了。
第二章 一群苍蝇在莺莺身边飞
张生
张生的作派在《西厢记》里妩媚而阴柔。刚出场的张生像历代的书生一样,无疑是病弱的,他无比自怜地这样自我评价:“学成满腹文章,尚在湖海飘零。”文章与飘零的张力在张生身上难堪地对峙着,并要最终寻找到自己的出口。在没有找到出口之前,可怜而可爱的张生只能是“万金宝剑藏秋水,满马春愁压绣鞍”。
飘零的价值最终会找到归宿;而在此之前,对张生飘零的第一个奖励在普救寺里露出了端倪—如同上苍注定,张君瑞命带桃花,普救寺中五百年前风流业冤向张生展示了意外的美丽和妖艳。也就是在此时,张生的满腹文章悄悄派上了用场。流氓需要才气,才气成就着流氓。张生的文化流氓底色得以彻底显影并最后定影,等待他的就是如何冲洗和复制放大并上光了。
普救寺的惊艳直接催生了一首好诗:
月色溶溶夜
花木寂寂春
如何临浩魄
不见月中人
该诗可谓孤篇压全唐,足见张生的“学成满腹文章”绝非空穴来风。张生以月亮—这人世间阴柔的代表起兴,最后直抒胸臆,向着近在咫尺的月中人发出召魂令,瞬间建立起了多情的形象。你听,张生像一个流浪歌手一样唱道:寺庙的夜色多沉静,那花儿寂寞地开在春风中,我静立月下多饥渴啊,为何没有美眉来调情?张生大胆而浮夸地将煽情进行到底,其实践精神当是空前绝后。若干年前,张生的老师也咏过月亮,他说:明月照到我床前,我当是霜花和食盐,抬头我把月亮看,才知它没故乡的圆(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相比张生,老师就显得不着边际。若干年后,张生的学生就不再咏月亮了,他们只说星星,发誓要给情人“一扇朝北的窗,让他看到星斗”,有张生的诗意,但显得过于吝啬。至于郁达夫之流的“曾因酒醉鞭名马,怕为情多累美人”则显得自怜而变态,及至发展到“轻轻地我走了/正如我轻轻地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里的那种欲擒故纵,那种小家子气,那种小妾般的懦弱,足见流氓才子已呈现难以挽回的退化。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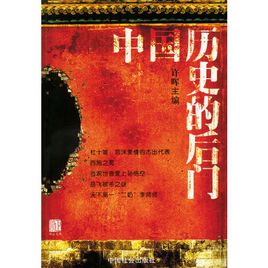 作者:许晖 (现代)
作者:许晖 (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