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 张贤亮
缘起
2004年11月8日夜十点多钟,我的手机突然响起。从7日早上我就感到不太舒服,有点感冒症状,关节酸疼,流鼻涕,慵懒,所以8号这天我很早就躺下了。这时一边懊恼没有关手机,一边又不得不起床到衣架上取出外衣里的手机。一听,出乎意料是小林的声音,她说《收获》策划了一个新的纪实性专栏,总的题目和希拉里的那本书名一样,叫“亲历历史”,约我写一篇。我说写“反右”行不行?小林说还是写“文革”吧。我说,“文革”的1965年到1968年我正在劳改农场,劳改队里不搞“文革”,我好像无从写起。小林说,“文革”有十年的历史哩!哦,“文革”竟闹了十年,连我自己都忘了!
关了机,我一夜难眠,第二天精神却好起来。
“文革”闹了十年,我准备只写一天。这篇文章我一开始就写上写作缘由的准确时间,是因为事件发生那天的准确时间我也忘了。我们常说我们是个健忘的民族,却很少责备自己个人也健忘。但这一天所发生的事是千真万确的,有近万人目睹,场面宏大。事实如同沉在河底的卵石,虽然河面上的波光浪影每一瞬间都不相同,但卵石是水流冲刷不去的,模糊的日期涂抹不掉事实。我曾将此事写进小说《习惯死亡》,这书译成了二十多种文字,但所有的读者都把它当虚构的故事。我写这篇文章也是要告诉读者,那不是故事,没有一点虚构的成分。
一开始就写下准确日子还因为,我感到身体不适的这天正是11月7日。这一天,绝大多数中国人大约也忘却了。11月7日对中国人来说曾是一个伟大的日子——“苏联十月革命节”,所谓攻打冬宫的“一声炮响,给我们带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很多年中,每年的这一天在中国是仅次于“十一”国庆节的节日,全国人民都要采取规模不等而形式相同的仪式来纪念它。我们不再纪念它已有二三十年了,可是这个节日总让我念念不忘。每到日历翻到这一天,我耳边似乎就会响起阿芙洛尔巡洋舰的隆隆炮声。这个节日是因我年轻时每年都过而至今印象深刻,那么我述说的这个真实故事的主人公,今天会是怎样的呢?她年幼时就“亲历”过那样的“历史”,我很难想象她能身心正常地活下来,更不知道如果她还活着并偶然看到我这篇文章,是否会触及她的隐痛,给她新的刺激。但我想到假如是后一种情况,她一定是和我一样坚强的人,甚至比我更坚强。她看了这篇文章,一定会亲自站出来说话,她的述说当然比我的文章更有力。
我希望是这样!
上
我在马克思《资本论》的注释中读到,“一个人不能以同一个罪行判处两次”,可是那是资产阶级法律,无产阶级法律好像不是这样,不但可以将人的同一罪行判处两次,还可以因政治的需要在后面一次的判处中将人罪加一等。在1965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我的罪名从“右派分子”升成“反革命分子”,判刑三年,在临近春节时,被一辆吉普车从南梁农场又押回西湖农场劳动改造。其实,对这样的判处我还是很庆幸的。因为1958年在西湖农场第一次劳改三年,至1961年释放到南梁农场就业以后,我仍是以一个被管制的“右派分子”身份和普通农工一起劳动的。像一只羊和一群狼、至少是一群狗一起在荒原上觅食一样,时时刻刻的提心吊胆可想而知。在劳改队里面,大家都是羊或大家都是狼或狗,谁也别说谁。你是羊我也是羊,你是狼我也是狼,你是狗我也是狗,我有一种用别人对我的态度来对待别人的本能,因而送我进劳改队我倒仿佛有一种回家的感觉,能应付自如了。是的,劳改队已成了我的家,或说是我天生就应该生活在劳改队里面,就像蜗牛就应该生活在它的壳里。
我记得1966年夏天,劳改队外的社会上文化大革命闹得很凶的时候,一天,我正在稻田里薅草,劳改队长在田埂上慢慢踱到我身边说:“你在这里真走运!你知不知道银川的‘文化大革命成就展’里还贴着你的《大风歌》哩。你要是在外面的话,非把你拉出去挂大牌子游街不可!”我立起腰心存感激地朝他嘻嘻笑。我确实感到很幸运。后来我才知道那次的所谓“文化大革命成就展”是宁夏“走资派”举办的,展出我的《大风歌》,为的是企图证明“文化革命”在宁夏已经进行过并取得“成就”了,以此来抵制这次由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文化大革命”。当时倘若我在社会上,肯定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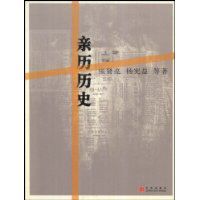 作者:张贤亮、杨宪益 (现代)
作者:张贤亮、杨宪益 (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