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介
通过简洁而令人信服的叙事,施蒂默尔深入探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讲述了德意志如何从一个新国家急速崛起成为欧洲大陆超级大国的动人心魄的历史:
为何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获得了难得的胜利;
统一进程、工业化、殖民运动和军事扩张等因素,如何综合起来促进了帝国的崛起;
德意志如何成为彻底打破欧洲均势的重要势力,并永远留在了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中心。
在历史进程之中,除了从普法战争到凡尔赛和约的这段时期,没有任何一段能够如此彻底地形成并改变德国。无视德意志帝国在这段历史时期的精彩演出,深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不可能。
作者简介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在德国马尔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的教育。1973年以来,长期担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索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上世纪80年代,出任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顾问。
施蒂默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提出了从地理角度解释德国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德国处于欧洲中心的这种不稳定地理形势是德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并辩称,为了应对这一形势,德国历届统治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进行威权统治。
1
壮观的凡尔赛宫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接待如此众多显赫的贵宾了。人群中有几个神情肃穆的贵族身着庄重的礼服,更多的则是带着胜利者姿态的军官——他们穿着挂满勋章的军队制服,左手扶在剑柄上,右手托着插着羽毛的头盔。这些德意志贵族统治阶级的精英,加上北德三个自由市的议员以及几个德意志帝国国会成员,一起见证了1871年1月18日的欧洲最后一个帝国——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人群中熟悉罗马历史的人必然会想起那个残酷却颠扑不破的真理:”武力成就帝国。“事实上,凡尔赛正是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盟军的主战场,在打败拿破仑三世的信念驱使下,这支盟军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了一起。他们此时所在的凡尔赛宫镜廊在几个星期前还可能是遍布着普鲁士伤兵残将的临时医院病房。此时,战争还未结束,盟军还要继续对抗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后崛起的共和国,然而和平已然到来。这种和平对法国注定是痛苦的,她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向长久以来一直充当自己外交筹码和战场的德意志赔偿50亿金法郎。和平对德意志来说也不是那么轻松:俾斯麦马上就认识到”法国是难以对付的“——有一个充满敌意的法国,欧洲不可能建立一个欧洲秩序;没有法国,欧洲秩序也无法建立。
为了遏制已经称霸德意志的普鲁士进一步在欧洲称霸,急于报复的法国不顾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意愿在1870年6月加入战争。”为萨多瓦复仇“成了法国媒体一种近乎疯狂的战争呼声。萨多瓦(Sadova),亦称柯尼格拉茨(Koniggratz),曾是普奥战争(1866年)中普鲁士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点。法国并未参加普奥战争,而且还曾经于1859年在意大利大败于奥地利,但是巴黎的议会和媒体却一致认为,自从弗朗索瓦一世[1]起,只有法国才有资格称霸欧洲。拿破仑三世深知,如果他不能阻止普鲁士主导的德国攫取法国传承的霸权,他将失去王位。于是法国参战了。然而在小城市色当被围困几个星期后,拿破仑三世还是输掉了战争,也失去了王位以及大量军队。
德意志帝国皇帝在离家如此远的地方登基似乎非常不合常理,而在象征着法国光荣与辉煌的凡尔赛王宫举行登基大典无疑让战败的法国人感到更加屈辱。但是,如果在柏林登基,这会显得普鲁士在自己的德意志兄弟面前炫耀军事独裁,也会提醒德国人,普鲁士国王曾经仅仅是作为”帝国七支柱“之一的普鲁士邦国的首领,是个选帝侯而已。法兰克福也不是举行登基典礼的理想地点。法兰克福与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神圣第一帝国皇帝的加冕礼就是在法兰克福的哥特大教堂举行的。它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也与帝国颇有联系: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柏林、巴登、奥地利、萨克森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等地的群众革命撼动了整个德意志地区几乎所有邦国国王的宝座,而今天的德意志皇帝,也就是当时的普鲁士王子,被迫假借外交借口经由法兰克福前往英国。还有,就在四年前,曾经作为”神圣罗马帝国金库“的法兰克福在1866年战争中支持奥地利,战败后作为惩罚,普鲁士剥夺了它作为自由市的地位。没有人忘记法兰克福及其他南方富裕的兄弟们如何嘲笑普鲁士的权力中心勃兰登堡只是”神圣帝国的吸墨粉盒“(一种将沙覆在字迹上吸收多于墨水的装置,因普鲁士境内多沙土),而如今它们将要臣服在曾经的普鲁士国王脚下,尊他为皇帝。为了避免国内各个邦国可能会感到的尴尬,在法国凡尔赛举行登基大典无疑是明智的选择。1871年1月18日这一天还有深刻的含义:170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701年1月18日,选帝侯腓特烈三世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自我加冕为”普鲁士国王“。
通过简洁而令人信服的叙事,施蒂默尔深入探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因素,讲述了德意志如何从一个新国家急速崛起成为欧洲大陆超级大国的动人心魄的历史:
为何在普法战争中普鲁士获得了难得的胜利;
统一进程、工业化、殖民运动和军事扩张等因素,如何综合起来促进了帝国的崛起;
德意志如何成为彻底打破欧洲均势的重要势力,并永远留在了欧洲历史舞台上的中心。
在历史进程之中,除了从普法战争到凡尔赛和约的这段时期,没有任何一段能够如此彻底地形成并改变德国。无视德意志帝国在这段历史时期的精彩演出,深刻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根源是不可能。
作者简介
米夏埃尔·施蒂默尔,德国新保守主义学者,在德国马尔堡大学、柏林自由大学和伦敦经济学院接受了历史、哲学和语言学的教育。1973年以来,长期担任埃尔兰根—纽伦堡大学历史系教授,曾任索邦大学、美国哈佛大学、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访问学者,上世纪80年代,出任了联邦德国总理科尔的顾问。
施蒂默尔最为人所知的是他提出了从地理角度解释德国历史的观点。他认为,德国处于欧洲中心的这种不稳定地理形势是德国历史进程中具有决定性影响的因素,并辩称,为了应对这一形势,德国历届统治者没有其它选择只能进行威权统治。
1
壮观的凡尔赛宫已经有五十多年没有接待如此众多显赫的贵宾了。人群中有几个神情肃穆的贵族身着庄重的礼服,更多的则是带着胜利者姿态的军官——他们穿着挂满勋章的军队制服,左手扶在剑柄上,右手托着插着羽毛的头盔。这些德意志贵族统治阶级的精英,加上北德三个自由市的议员以及几个德意志帝国国会成员,一起见证了1871年1月18日的欧洲最后一个帝国——德意志帝国的诞生。
人群中熟悉罗马历史的人必然会想起那个残酷却颠扑不破的真理:”武力成就帝国。“事实上,凡尔赛正是普法战争期间德国盟军的主战场,在打败拿破仑三世的信念驱使下,这支盟军前所未有地团结到了一起。他们此时所在的凡尔赛宫镜廊在几个星期前还可能是遍布着普鲁士伤兵残将的临时医院病房。此时,战争还未结束,盟军还要继续对抗法兰西第二帝国之后崛起的共和国,然而和平已然到来。这种和平对法国注定是痛苦的,她失去了阿尔萨斯和洛林,还要向长久以来一直充当自己外交筹码和战场的德意志赔偿50亿金法郎。和平对德意志来说也不是那么轻松:俾斯麦马上就认识到”法国是难以对付的“——有一个充满敌意的法国,欧洲不可能建立一个欧洲秩序;没有法国,欧洲秩序也无法建立。
为了遏制已经称霸德意志的普鲁士进一步在欧洲称霸,急于报复的法国不顾皇帝拿破仑三世的意愿在1870年6月加入战争。”为萨多瓦复仇“成了法国媒体一种近乎疯狂的战争呼声。萨多瓦(Sadova),亦称柯尼格拉茨(Koniggratz),曾是普奥战争(1866年)中普鲁士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地点。法国并未参加普奥战争,而且还曾经于1859年在意大利大败于奥地利,但是巴黎的议会和媒体却一致认为,自从弗朗索瓦一世[1]起,只有法国才有资格称霸欧洲。拿破仑三世深知,如果他不能阻止普鲁士主导的德国攫取法国传承的霸权,他将失去王位。于是法国参战了。然而在小城市色当被围困几个星期后,拿破仑三世还是输掉了战争,也失去了王位以及大量军队。
德意志帝国皇帝在离家如此远的地方登基似乎非常不合常理,而在象征着法国光荣与辉煌的凡尔赛王宫举行登基大典无疑让战败的法国人感到更加屈辱。但是,如果在柏林登基,这会显得普鲁士在自己的德意志兄弟面前炫耀军事独裁,也会提醒德国人,普鲁士国王曾经仅仅是作为”帝国七支柱“之一的普鲁士邦国的首领,是个选帝侯而已。法兰克福也不是举行登基典礼的理想地点。法兰克福与中世纪的神圣罗马帝国之间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因为神圣第一帝国皇帝的加冕礼就是在法兰克福的哥特大教堂举行的。它在1848年欧洲革命时期也与帝国颇有联系:在那疯狂的革命年代,柏林、巴登、奥地利、萨克森和巴列丁奈特(palatinate)等地的群众革命撼动了整个德意志地区几乎所有邦国国王的宝座,而今天的德意志皇帝,也就是当时的普鲁士王子,被迫假借外交借口经由法兰克福前往英国。还有,就在四年前,曾经作为”神圣罗马帝国金库“的法兰克福在1866年战争中支持奥地利,战败后作为惩罚,普鲁士剥夺了它作为自由市的地位。没有人忘记法兰克福及其他南方富裕的兄弟们如何嘲笑普鲁士的权力中心勃兰登堡只是”神圣帝国的吸墨粉盒“(一种将沙覆在字迹上吸收多于墨水的装置,因普鲁士境内多沙土),而如今它们将要臣服在曾经的普鲁士国王脚下,尊他为皇帝。为了避免国内各个邦国可能会感到的尴尬,在法国凡尔赛举行登基大典无疑是明智的选择。1871年1月18日这一天还有深刻的含义:170年前的这一天,也就是1701年1月18日,选帝侯腓特烈三世脱离了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统治,自我加冕为”普鲁士国王“。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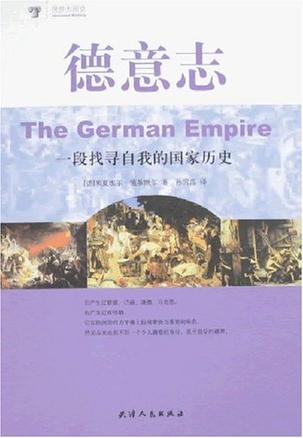 作者: 孙雪晶(现代)
作者: 孙雪晶(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