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多样的猿
每种宗教的核心都包含着创世的神话,它们大多都能回答孩子们这样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用简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洁明了的方式,对人的存在和人生存的环境做出解释。尽管这些神话试图解释人的起源,但是它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环顾世界各地,为什么人们在文化、体形、相贸、肤色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我们从何而来栖息于广袤的大地之上? 希罗多德是约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翔实的希腊-波斯战争的史料,而且他最早以古朴的笔调描述了人类的多样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黝黑神秘的利比亚人、俄罗斯北部野蛮的食人族、模样像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人等。希罗多德充满想象地讲述了“狮身鹰首兽”守护着亚洲群山中的藏宝洞,那个从蚂蚁洞里收集黄金的北部印度人的充满异域色彩的故事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总之,他的作品可称为西方第一部人种志,尽管缺陷明显,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部珍贵遗产。
我们假设自己是当代的希罗多德,是生活在某个地区的土著居民,现在我们要平生首次进行环赤道的世界旅行,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多样性会令我们惊叹不已。设想你乘坐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笛卡尔球体”的正中心——经度0、纬度0,在非洲的中西部,距离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约1000公里。让我们继续想象飞机向东飞去,想象我们像在科幻小说中那样在高空之上俯瞰地面,我们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
我们首先会遇到非洲人——说班图语的中非人。他们的肤色很黑,大多居住在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庄里。再向东走,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黑肤色的人,但与前者相比有所不同:这些又高又瘦的东非尼罗河人,差不多是地球上最高的人,他们生活在绿色的大草原上,以放牛为生。散居在这两族人之间的是哈德兹人,尽管相距不远,但他们与班图人和尼罗河人都有区别。
继续向东,我们遇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无边无际的河面看似永远不可逾越,仿佛它就是世界的终点。现在我们踏上了马尔代夫群岛,这里的人与我们在非洲遇到的有很大的区别,语言也不同。和那些非洲人一样,他们的肤色也是黑的,但面部与他们有所区别,包括鼻子的形状、头发和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尽管看上去有明显的区别,但很明显,他们和非洲人具有某种联系。
在那条宽广的河流之上继续我们的行程,这时,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前方徐徐升起,这就是苏门答腊。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种人,他们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人矮小,面部特征也不同:头发很直,肤色较浅,眼皮较厚。再向东,经过无数岛屿,我们再次遇到了肤色很黑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除了肤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肤色是进化过程中适应这一地区气候环境的结果?或者是表明他们与非洲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接着我们要遇到玻利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百里开阔海域的小环状珊瑚岛上,他们的相貌与我们先前见到的苏门答腊人有些相像,但是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相像但并不相同。最大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区?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到达西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它的首都基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活在这里的人各不相同,主要的有两种,一种与马尔代夫人有些相似,但肤色较浅;另一种很像苏门答腊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因为此前我们所到之地,在一地所见的都是同一种类的人,因此这种现象似乎很奇特。为什么在厄瓜多尔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在美洲继续向东,到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混合人群,我们再次遇到了非洲人,但却是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美洲!经历了这样的旅程,回到起点,对行程中的所见,面对这样一幅色彩斑斓的多样性的“织锦”,我们会陷入沉思,会试着对这一幅多彩多样的图案做出解释。
我们只是在想象之中进行了这次旅行,但我们在想象之中的行程,正是我们的前辈几百年前在欧洲“发现航海”旅程中的真实经历。假设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提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常识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知识。这是一次有趣的思想体验,因为直到近年,除了为什么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同生活在美洲之外,对我们所见到的这幅多彩图画,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
一个物种 1860年6月30日,愤怒的萨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登上了牛津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台。他准备好了要进行一场战斗——不仅是为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他坚定的信仰和世界观。威尔伯福斯深深感到他在为教会的未来战斗。那次聚会所辩论的题目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那是在19世纪中期,直到近代,只有哲学家和教会才会相互争论这个问题,它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于科学家和教会之间。这位优秀的主教忠实地引用圣经原文,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这个日期是根据《圣经》中所描述的宗谱推算出来的。他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在当时深入人心的问题:你难道能够想象你是由猴子变来的吗?这简直荒谬至极!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对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观点是极有说服力的。那一天,他在图书馆成功地捍卫了他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可避免地完全失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人在自然世界处于何种地位,随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变化,预示着人类历史上的“屠龙者”不再是哲学家和神职人员,而是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约瑟夫?霍克和托马斯?享利?赫胥黎,这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赫胥黎当时是伦敦矿业学院生物学讲师,他以“达尔文的斗牛狗”而著名。霍克是皇家植物园的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副主任。当威尔伯福斯的演讲结束后,他们站起来反驳他充满激情的观点,他们的声音无异于为古老的人类起源观敲响了丧钟,寓示者是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威尔伯福斯和霍克、赫胥黎的论战,不仅促进了公众对进化论的接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已经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了,而且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做无所不能的神的创造,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我们比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都要优越,我们是主人、征服者、上帝的宠儿,总之,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达尔文的真知灼见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消化不良、隐士般的人,寥寥数笔便把人由神的创造还原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有趣的是,他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他的祖父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父亲是一名富有的医生,而达尔文每天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经营他的商业投资),当他于1831年开始环球航海时,并无意于动摇《圣经》中的古老信念。剑桥大学毕业后,在那个时代他顺理成章地选择做一名牧师,但他渴望冒险,渴望新奇的航海生活为一成不变、刻板的乡村牧师生活注入活力。当然,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每种宗教的核心都包含着创世的神话,它们大多都能回答孩子们这样的问题:人是从哪里来的?用简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洁明了的方式,对人的存在和人生存的环境做出解释。尽管这些神话试图解释人的起源,但是它们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明确的答案:环顾世界各地,为什么人们在文化、体形、相贸、肤色等方面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为什么我们彼此是如此不同?我们从何而来栖息于广袤的大地之上? 希罗多德是约公元前500年古希腊的历史学家,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翔实的希腊-波斯战争的史料,而且他最早以古朴的笔调描述了人类的多样性,为我们留下了许多传说故事:黝黑神秘的利比亚人、俄罗斯北部野蛮的食人族、模样像土耳其人和蒙古人的人等。希罗多德充满想象地讲述了“狮身鹰首兽”守护着亚洲群山中的藏宝洞,那个从蚂蚁洞里收集黄金的北部印度人的充满异域色彩的故事至今读起来依然津津有味。总之,他的作品可称为西方第一部人种志,尽管缺陷明显,仍不失为那个时代的一部珍贵遗产。
我们假设自己是当代的希罗多德,是生活在某个地区的土著居民,现在我们要平生首次进行环赤道的世界旅行,那么,我们所见到的人类多样性会令我们惊叹不已。设想你乘坐的飞机正在大西洋上空、“笛卡尔球体”的正中心——经度0、纬度0,在非洲的中西部,距离加蓬首都利伯维尔约1000公里。让我们继续想象飞机向东飞去,想象我们像在科幻小说中那样在高空之上俯瞰地面,我们将得到一幅人类多样性的图谱。
我们首先会遇到非洲人——说班图语的中非人。他们的肤色很黑,大多居住在森林中开辟出的小村庄里。再向东走,我们看到的依然是黑肤色的人,但与前者相比有所不同:这些又高又瘦的东非尼罗河人,差不多是地球上最高的人,他们生活在绿色的大草原上,以放牛为生。散居在这两族人之间的是哈德兹人,尽管相距不远,但他们与班图人和尼罗河人都有区别。
继续向东,我们遇到了一条宽阔的大河,无边无际的河面看似永远不可逾越,仿佛它就是世界的终点。现在我们踏上了马尔代夫群岛,这里的人与我们在非洲遇到的有很大的区别,语言也不同。和那些非洲人一样,他们的肤色也是黑的,但面部与他们有所区别,包括鼻子的形状、头发和其他一些细微的差别。尽管看上去有明显的区别,但很明显,他们和非洲人具有某种联系。
在那条宽广的河流之上继续我们的行程,这时,一座巨大的岛屿在前方徐徐升起,这就是苏门答腊。在这里我们遇到了另一种人,他们比非洲人和马尔代夫人矮小,面部特征也不同:头发很直,肤色较浅,眼皮较厚。再向东,经过无数岛屿,我们再次遇到了肤色很黑的人,他们是美拉尼西亚人。除了肤色,他们在很多方面都不像非洲人,他们的肤色是进化过程中适应这一地区气候环境的结果?或者是表明他们与非洲人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 接着我们要遇到玻利尼西亚人,他们生活在散布于数百里开阔海域的小环状珊瑚岛上,他们的相貌与我们先前见到的苏门答腊人有些相像,但是每一次都是同样的结果:相像但并不相同。最大的疑问是:他们为什么生活在如此偏远的地区?他们是如何到达这里的? 继续我们的行程,我们会到达西南美洲的厄瓜多尔海岸。在它的首都基多,我们看到了一种奇特的现象:生活在这里的人各不相同,主要的有两种,一种与马尔代夫人有些相似,但肤色较浅;另一种很像苏门答腊人和玻利尼西亚人。因为此前我们所到之地,在一地所见的都是同一种类的人,因此这种现象似乎很奇特。为什么在厄瓜多尔情况发生了变化呢?在美洲继续向东,到巴西的东北海岸,我们发现了一个更复杂的混合人群,我们再次遇到了非洲人,但却是在距离非洲如此遥远的美洲!经历了这样的旅程,回到起点,对行程中的所见,面对这样一幅色彩斑斓的多样性的“织锦”,我们会陷入沉思,会试着对这一幅多彩多样的图案做出解释。
我们只是在想象之中进行了这次旅行,但我们在想象之中的行程,正是我们的前辈几百年前在欧洲“发现航海”旅程中的真实经历。假设我们一无所知,我们可以提出对今天的人们来说已经是常识的问题,但正是这些问题,使我们获得了历史的知识。这是一次有趣的思想体验,因为直到近年,除了为什么非洲人和欧洲人共同生活在美洲之外,对我们所见到的这幅多彩图画,一直没有一个系统的解释。
一个物种 1860年6月30日,愤怒的萨缪尔?威尔伯福斯主教登上了牛津大学博物馆图书馆的讲台。他准备好了要进行一场战斗——不仅是为他自己,更重要的是为他坚定的信仰和世界观。威尔伯福斯深深感到他在为教会的未来战斗。那次聚会所辩论的题目是关于人在自然中的地位。那是在19世纪中期,直到近代,只有哲学家和教会才会相互争论这个问题,它永远不可能再出现于科学家和教会之间。这位优秀的主教忠实地引用圣经原文,坚信这个世界是公元前4004年10月23日经上帝之手创造的,距今约有6000年的历史。这个日期是根据《圣经》中所描述的宗谱推算出来的。他在演讲中向听众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一个在当时深入人心的问题:你难道能够想象你是由猴子变来的吗?这简直荒谬至极! 威尔伯福斯是一个出色的演讲家,对大多数听众来说,他的观点是极有说服力的。那一天,他在图书馆成功地捍卫了他的信仰,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无可避免地完全失败了。具有深远意义的是,人在自然世界处于何种地位,随着我们在这一问题上观点的变化,预示着人类历史上的“屠龙者”不再是哲学家和神职人员,而是专业的科学工作者。约瑟夫?霍克和托马斯?享利?赫胥黎,这两位维多利亚时代的杰出人物,是达尔文自然选择进化理论的坚定支持者。赫胥黎当时是伦敦矿业学院生物学讲师,他以“达尔文的斗牛狗”而著名。霍克是皇家植物园的有成就的植物学家、副主任。当威尔伯福斯的演讲结束后,他们站起来反驳他充满激情的观点,他们的声音无异于为古老的人类起源观敲响了丧钟,寓示者是科学引导我们进入了一个勇敢的新世界。
威尔伯福斯和霍克、赫胥黎的论战,不仅促进了公众对进化论的接受——大多数受过教育的人已经用进化论的眼光看待世界了,而且使人们重新认识了人在自然界的地位。如果我们把自己看做无所不能的神的创造,我们很容易就能证明我们比地球上的其他一切生命都要优越,我们是主人、征服者、上帝的宠儿,总之,我们是独一无二的存在。
达尔文的真知灼见彻底改变了这一切。这个消化不良、隐士般的人,寥寥数笔便把人由神的创造还原为生物进化的产物。有趣的是,他本人也没有料想到他会提出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维多利亚时代贵族家庭的后代(他的祖父是约西亚?韦奇伍德,父亲是一名富有的医生,而达尔文每天要抽出半天的时间经营他的商业投资),当他于1831年开始环球航海时,并无意于动摇《圣经》中的古老信念。剑桥大学毕业后,在那个时代他顺理成章地选择做一名牧师,但他渴望冒险,渴望新奇的航海生活为一成不变、刻板的乡村牧师生活注入活力。当然,这并不是他的全部目的。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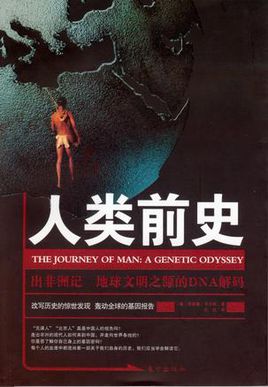 作者:斯宾塞・韦尔斯 (美)
作者:斯宾塞・韦尔斯 (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