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月光下的行军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仲仲、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莽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牵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 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
十月的阳光洒满了洁白的病房。院外阔叶成荫的樟树下传来阵阵喧闹,口令声、军号声响成一片,跑步扬起的尘土弥漫在平静的空气中。屋内躺着的是一个面容憔悴的病人,左腿上打着石膏。这时他正伸着脖子想看看外面的动静,显然发生了什么情况,红军要采取新的行动了。但还没有人告诉他。一个护士从他的门前走过,他喊住她:“出了什么事?”
“我不知道,首长。”护士往院外看了一眼说,“没有人告诉我们。”
这个病人就是有名的陈毅。他无奈地骂了一声,又躺下了。他自六个星期前因臀部枪伤久久不愈而从兴国前线被抬到这里以来,已咒骂了上百次。伤口中不断发现碎骨片,而当陈毅要求给予爱克斯光检查时,医生却以种种借口拒绝了:爱克斯光机出了故障啦,没有电源啦,电池太弱啦。
陈毅,四川人,当时三十三岁,已是红军的一位高级指挥员。他性格开朗,富有幽默感,是个乐天派。然而今天他却一反常态,变得忧心仲仲、烦躁不安。外边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他却搞不清楚。他在病床上辗转反侧,严重的伤情使他一筹莫展。
几分钟后,那位护士又来了。“首长,有人要见你。”她一边说,一边匆忙地拍松他的枕头,整理一下床单。陈毅的目光越过她的肩头向窗外望去,看到向病房走来的正是自己的老朋友和老同志周恩来。后来,陈毅永远也忘不了周恩来看望他的这一天,那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九日——阴历狗(甲戌)年的九月初二。就在这一天,陈毅才知道了后来成为长征的消息。
于都是赣南于都河畔一座寂静的小县城,人口不到一万。它不过是一个渡口,一个集市,这个小镇从来没有发生过什么重大的事件。一九三四年十月,这里是一派安宁富足的景象:天气很好,白天暖和,夜间凉爽,很少下雨。大多数庄稼都已收割完毕,地里只剩下晚稻、莽麦和红薯。青瓦屋顶上晾晒着豆秸和其它东西,有的牵拉在屋檐下。靠院墙放着的红陶罐里装着豆瓣酱。院角堆着绿皮红籽的苦瓜,桔黄色的南瓜和一串串鲜红的干辣椒。农民们都知道,他们的粮食足够吃到下一季庄稼收获时节了。但这时的于都却有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氛:红军在夏天就征购了大批稻米,而且一直在进行不同寻常的扩红(招募新兵)。收成相当好,人们一年到头地忙着播种、收割、耙地、插秧,这时本来可以喘口气了,但又担心似乎要出什么事。到底是什么事,谁也搞不清楚。中秋节已过,家家户户门框上贴着的大红对联和凶恶吓人的门神已经有点破旧了。人们希望这些东西能继续保护他们免遭厄运。
刘英已在于都搞了好几个星期的扩红工作了。她只不过是从事这项工作的许多年轻妇女中的一个。刘英今年二十六岁,还不到五英尺高,娇小得就象小孩子玩的布娃娃。海伦·斯诺曾经说她无法想象刘英在长征途中是怎么没被大风刮走的?后来,当刘英和党的高级领导人洛甫结婚时,她自己也这样说过。刘英的个子虽小,但她具有钢丝一般坚韧的精神,毛泽东也一直关照着她。一天,毛带着一名警卫员来到于都的共青团办事处。他悄悄地要这位小扩红队员马上离开于都,去瑞金赣南中央苏区总部报到,接受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
“我对他说我离不开,”刘英五十年后回忆道,“我还没有完成任务,我还没有完成自己的扩红定额哩!”
但是毛泽东的态度很坚决,他命令刘英必须回去。刘英虽然困惑不解,但还是遵命回到了瑞金。四十英里的路,她走了两天,当然,与她不久之后将要踏上的路程相比,这不过是小小的散步而已。
江西省会南昌市中湖畔,矗立着一座高大森严的楼房,楼里有一个身体消瘦、穿着考究的光头男人。这时他正坐在精美的红木写字台后面,手拿当地国民党报纸《民国日报》,他那薄薄的嘴唇上接着一丝得意的微笑。他的目光掠过当日的主要消息,这是有关承建某座铁路桥合同的事,掠过春药、妇科良药和珠宝等杂 乱无章的广告,然后集中在当日的主要社论上。这是一九三四年的十月十日,双十节,国民党政权成立的纪念日。社论的主题是当前面临的问题。它警告人们:天灾将至,第二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共匪趁机作乱,人们应崇尚仁义道德,戒酒禁舞,为祖国与中华之生存而努力奋斗。社论又要人们相信,乱世中之大幸,江西的局势正迅速改观,共匪一年之内即可肃清,他们已四面楚歌,不得不用绳索把士兵拴在一起,以防逃跑,“共匪士崩瓦解已指日可待”,云云。
看报的人轻轻舔了一下嘴唇,对报上的言词感到满意。其实,这些话都是在他亲自授意下写的。他,就是蒋介石,四十八岁,此刻他亲临南昌指挥对“赤匪”的“围剿”。形势不错,两三天后,他调来自己的专机,准备速赴陕西、宁夏和四川进行视察。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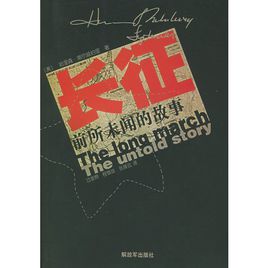 作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美)
作者:哈里森·埃文斯·索尔兹伯里(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