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斋四笔序
始予作《容斋随笔》,首尾十八年,《二笔》十三年,《三笔》五年,而《四笔》之成,不费一岁。身益老而著书益速,盖有其说。嚷自越府归,谢绝外事,独弄笔纪述之习,不可扫除。故搜采异闻,但绪《夷坚志》,于议论雌黄,不复关抱。而稚子櫰,每见《夷坚》满纸,辄曰:“《随笔》、《夷坚》,皆大人素所游戏。今《随笔》不加益,不应厚于彼而薄于此也。”日日立案旁;必俟草一则乃退。重逆其意,则衷所忆而书之。櫰嗜读书,虽就寝犹置一编枕畔,旦则与之俱兴。而天啬其付,年且弱冠,聪明殊未开,以彼其勤,殆必有日。丈夫爱怜少子,此乎见之。于是占抒为序,并奖其志云。庆元三年九月二十四日序。
容斋四笔卷第一(十九则)
孔庙位次自唐以来,相传以孔门高弟颜渊至子夏为十哲,故坐祀于庙堂上。其后升颜子配享,则进曾子于堂,居子夏之次以补其阙。然颜子之父路、曾子之父点,乃在庑下从把之列,子处父上,神灵有知,何以自安?所谓子虽齐圣,不先父食,正谓是也。又孟子配食与颜子并,而其师子思、子思之师曾子亦在下。此两者于礼、于义,实为未然,特相承既久,莫之敢议耳。
周三公不特置周成王董正治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而云:“官不必备,惟其人。”以书传考之,皆兼领六卿,未尝特置也。周公既为师,然犹位冢宰,《尚书》所载召公以太保领家宰,芮伯为司徒,彤伯为宗伯,毕公以太师领司马,卫侯为司寇,毛公以太傅领司空是已。其所次第惟以六卿为先后,而师傅之尊乃居太保下也。
周公作金滕《尚书》孔氏所传五十九篇皆有序,其出于史官者不言某人作,如《虞书》五篇,纪一时君臣吁咈都俞及识其政事,如《说命》、《武成》、《顾命》、《康王之浩》、《召浩》自“惟二月既望”至“越自乃御事”、《洛诰》自“戊辰王在新邑”至篇终、《蔡仲之命》自“惟周公位冢宰”至“邦之蔡”皆然。如指言某人所作,则伊尹作《伊训》、《太甲》、《咸有一德》,《盘庚》三篇,周公作《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多士》、《无逸》、《君爽》、《多方》、《立政》是也。惟《金滕》之篇,首尾皆叙事,而直以为周公作。按此篇除册祝三王外,余皆《周史》之词,如“公乃自以为功”、“公归纳册”、“公将不利于孺子”、“公乃为诗以贻王”、“王亦未敢消公”、“公命我勿敢言”、“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公勤劳王家”之语,“出郊”、“反风”之异,决非周公所自为,今不复可质究矣。
云梦泽云梦,楚泽蔽也,列于《周礼·职方氏》。郑氏曰:“在华容。”《汉志》有云梦官。然其实云也、梦也,各为一处。《禹贡》所书:“云土梦作义。”注云:“在江南。”惟《左传》得其详,如■夫人弃子文于梦中。注云,“梦,泽名,在江夏安陆县城东南。”楚子田江南之梦。注云:“楚之云、”梦,跨江南北。”楚子济江入于云中。注:“入云泽中,所谓江南之梦。”然则,云在江之北,梦在其南也。《上林赋》:“楚有七泽,尝见其一,名曰云梦,特其小小者耳,方九百里。”此乃司马长卿夸言。今为县,隶德安,询诸彼人,已不能的指疆域。《职方氏》以“梦”为“瞢”,《前汉·叙传》:子文投于梦中,音皆同。
关雎不同《关雎》为《国风》首,毛氏列之于三百篇之前。《大序》云:“后妃之德也。”而《鲁诗》云:“后夫人鸡鸣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诗人叹而伤之。”《后汉·皇后纪序》:“康王晏朝,《关雎》作讽。”盖用此也。显宗水平八年诏云:“昔应门失守,《关雎》刺世。”注引《春秋说题辞》曰:“人主不正,应门失守,故歌《关雎》以感之。”宋均云:“应门,听政之处也。言不以政事为务,则有宣淫之心。《关雎》乐而不淫,思得贤人与之共化,修应门之政者也。”薛氏《韩诗章句》曰:“诗人言雎鸠贞洁敬匹,以声相求,隐蔽于无人之处。故人君退朝,入于利宫,后妃御见有度,应门击析,鼓人上堂,退反燕处,体安志明。今时大人内倾于色,贤人见其萌,故咏《关睢》之说淑女正容仪以刺时。”三说不同如此。《黍离》之诗列于王国风之首,周大夫所作也,而《齐诗》以为卫宣公之子寿,闵其兄伋之且见害,作忧思之诗,《黍离》之诗是也。此说尤为可议。
迷痴厥拨柔词谄笑,专取容悦,世俗谓之“迷痴”,亦曰“迷嬉”。中心有愧见诸颜面者,谓之“缅靦”。举措脱落,触事乖件者,谓之“厥拨”。虽为俚言,然其说皆有所本。《列子》云:“墨杘、单至、啴咺、憋憋,四人相与游于世。”又云:“眠娗、諈诿、勇敢、怯疑,四人亦相与游。”张湛注云:“墨音眉,杘敕夷反,《方言》:江淮之间谓之无赖;眠音缅,娗音珍,《方言》:欺谩之语也。郭璞云:谓以言相轻嗤弄也。”所释虽不同,然大略具是矣。《曲礼》:“衣毋拨,足毋蹶。”郑氏注云:“拨,发扬貌。蹶,行遽貌。”大抵亦指其荒率也。
三馆秘阁国朝儒馆仍唐制,有四:曰昭文馆,曰史馆,曰集贤院,曰秘阁。率以上相领昭文大学士,其次监修国史,其次领集贤。若只两相,则首厅兼国史。唯秘阁最低,故但以两制判之。四局各置直官,均谓之馆职,皆称学士。其下则为校理、检讨、校勘,地望清切,非名流不得处。范景仁为馆阁校勘,当迁校理,宰相庞籍言:“范镇有异才,恬于进取。”乃除直秘阁。司马公作诗贺之曰:“延阁屹中天,积书云汉连。神宗重其选,谓大宗也。国士比为仙。玉槛钩陈上,丹梯北斗边。帝容瞻日角,宸翰照星躔。职秩曾无贵,光华在得贤。”其重如此。自熙宁以来,或颇用赏劳。元丰官制行,不置昭文、集贤,以史馆入著作局,而直秘阁只为贴职。至崇宁、政、宣以处大臣子弟姻戚,其滥及于钱谷文俗吏,士大夫不复贵重。然除此职者必诣馆下拜阁,乃具盛筵,邀见在三馆者宴集,秋日暴书宴,皆得预席,若余日则不许至,《随笔》有《馆职名存》一则云。
亭谢立名立亭榭名最易蹈袭,既不可近俗,而务为奇涩亦非是。东坡见一客云近看晋书,问之曰:“曾寻得好亭子名否?”盖谓其难也。秦楚材在宣城,于城外并江作亭,目之曰“知有”。用杜诗“已知出郭少尘事,更有澄江消客愁”之句也。王仲衡在会稽,于后山作亭,目之曰“白凉”。亦用杜诗“越女天下白,鉴湖五月凉”之句。二者可谓甚新,然要为未当。庐山一寺中有亭颇幽胜,或标之曰:“不更归”,取韩诗末句,亦可笑也。
十十钱市肆间交易论钱陌者,云十十钱。言其足数满百无跷减也。其语至俗,然亦有所本。《后汉书·襄楷传》引宫崇所献神书,其《太平经·兴帝王篇》云:“开其玉户,施种于中,比若春种于地也,十十相应和而生。其施不以其时,比若十月种物于地也,十十尽死,固无生音。”其书不传于今,唐章怀太子注释之时,尚犹存也。此所谓十十,盖言十种十生无一失耳,其尽死之义亦然,与钱陌之事殊,然其字则同也。
犀舟张衡《应间》云:“犀舟劲揖。”《后汉》注引《前书》“羌戎弓矛之兵,器不犀利。”《音义》曰:“今俗谓刀兵利为犀。犀,坚也。”“犀舟”,甚新奇,然为文者,未尝用,亦虑予所见之不博也。
毕仲游二书元祐初,司马温公当国,尽改王荆公所行政事,士大夫言利害者以千百数,闻朝廷更化,莫不欢然相贺,唯毕仲游一书,究尽本末。其略云:“昔安石以兴作之说动先帝,而患财之不足也,故凡政之可以得民财者无不用。盖散青苗、置市易、敛役钱、变盐法者,事也,而欲兴作患不足者,情也。苟未能杜其兴作之情,而徒欲禁其散敛变置之事,是以百说而百不行。今遂欲废青苗、罢市易,蠲役钱、去盐法,凡号为财利而伤民者,一扫而更之,则向来用事于新法者,必不喜矣。不喜之人,必不但曰青苗不可废,市易不可罢,役钱不可蠲,盐法不可去,必探不足之情,言不足之事,以动上意,虽致石人而使听之,犹将动也。如是则废者可复散,罢者可复置,蠲者可复敛,去者可复存矣。则不足之情可不预治哉!为今之策,当大举天下之计,深明出入之数,以诸路所积之钱粟,一归地官,使经费可支二十年之用。数年之间,又将十倍于今日。使天子晓然知天下之余于财也,则不足之论不得陈于前,然后所谓新法者,始可永罢而不复行矣,昔安石之居位也,中外莫非其人,故其法能行。今欲救前日之敝,而左右侍从职司使者,十有七八皆安石之徒,虽起二三旧臣,用六七君子,然累百之中存其十数,乌在其势之可为也!势未可为而欲为之,则青苗虽废将复散,况未废乎?市易虽罢且复置,况未罢乎?役钱、盐法亦莫不然。以此救前日之敝,如人久病而少间,其父兄子弟喜见颜色,而未敢贺者,意其病之在也。”
先是东坡公在馆阁,颇因言语文章,规切时政,仲游忧其及祸,贻书戒之曰:“孟轲不得已而后辩,孔子欲无言。古人所以精谋极虑,固功业而养寿命者,未尝不出乎此。君自立朝以来,祸福利害系身者未尝言,顾直惜其言尔。夫言语之累,不特出口者为言,其形于诗歌、赞于赋颂、托于碑铭、著于序记者,亦言也。今知畏干口而未畏于文,是其所是,则见是者喜,非其所非,则蒙非者怨。喜者未能济君之谋,而怨者或已败君之事矣!天下论君之文,如孙膑之用兵、扁鹊之医疾,固所指名者矣,虽无是非之言,犹有是非之疑。又况其有耶?官非谏臣,职非御史,而非人所未非,是人所未是,危身触讳以游其间,殆由抱石而救溺也。”
二公得书耸然,竟如其虑。予顷修史时,因得其集,读二书思欲为之表见,故官虽不显,亦为之立传云。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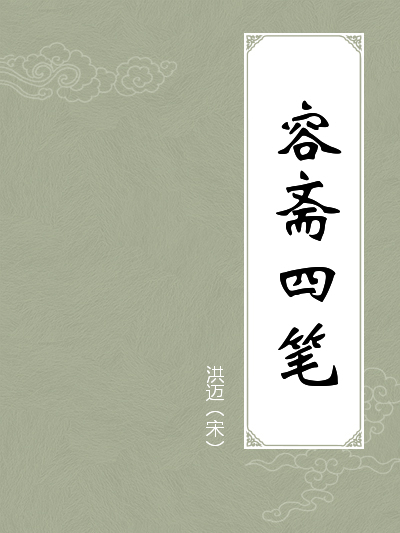 作者:洪迈(宋)
作者:洪迈(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