血浓于水
——《南京大屠杀》再版自序
这本书第一次同读者见面,是一九八七年十二月即“南京大屠杀”五十周年的祭日。在南京举行首发式时,读者蜂拥争购,九千册书一天脱销。出版当月,就发行了十五万册!当时,众多新闻媒介发表评论文章,称它是“中国作家写的第一部全面、真实、生动而深刻地反映‘南京大屠杀’历史的悲剧长卷。”又说这是“民族苦难的缩影,史书式的报告文学”。
从那以后的五六年间,这本书在大陆的书店一直脱销,而香港、台湾、日本及美国的出版社以及报刊,仍然不断地出版、转载,还发表了不少评介文章。
创作这本书的起因和动机是偶然和简单的,自然,也没有想到会在海内外引起不小的反响。最切触发我灵感的,是一九八五年盛夏的一个星期天,《南京日报》发表消息说,为了纪念抗日战争胜利四十周年,南京市在侵华日军集体屠杀南京市民的遗址上,建立了十三块纪念碑。当天我路过北极阁,许多人围在路边,面对扇形的黑底金字的纪念碑,肃立着、凝望着、沉思着。我被这场面震惊了:这里,曾是一片花草繁茂的绿地,它的昨天,怎么会是鲜血飞迸的屠场呢?我当时就有了冲动,我想写一首诗或者一篇散文,题目也想好了:《石头城,站起来十三个石头人》。
五分钟的狂热激情过去了,诗和散文都没有写出来。几天后一些朋友们吹牛聊天,他们说:“李延国写了《中国农民大趋势》,钱钢在写《唐山大地震》,你也来个大的吧!”
“我能写什么呢?”我故作谦虚状。
“南京大屠杀!”一位朋友大声地说。
像电光石火,一句话又点燃了纪念碑前的激情。
我立即翻阅史料。很遗憾,我没有找到“南京大屠杀”的详细记载,一些史书上只是几百字的条目。问了好些人,都吱吱唔唔,或一知半解,没有人能说清这场历史悲剧的缘由、经过及事件中的人物和情节。我觉得,这是一页不应忘的历史。
正因为此,我开始了茫茫人海和茫茫书海的探寻。
快半个世纪了,当年二十岁左右的亲历者如今已是古稀老人了,他们在哪里?
感谢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和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等单位的运行和帮助,凭借他们提供的线索和史料,我奔走于南京的四郊和大街小巷,我要寻访九死一生的幸存者和历史的见证人。
采访是困难的。一辆自行车伴随我早出晚归,辛苦是自然的。艰难的是找到了幸存者们,重提刻骨铭心的创伤和埋在心中的仇恨又会刺痛这些老人。特别是受侵华日军欺凌的那些妇女,她们如今已儿孙成群,回忆那些隐秘的伤痛,她们感到耻辱,感到恐惧,感到害怕!
我得迂回曲折,我得循循善诱,我得晓以民族大义,继而又作出保护隐私的承诺。就是这样,也得再三再四地耐心他说服。这是我们的中国特色,中国人都爱面子。
不管怎么说,我仍然感谢所有接受我采访的人们,三个多月的时间里,近百位幸存者向我诉说了他们人生历程中的厄运,诉说了史料中绝对找不到的故事情节,这不仅给我提供了大量丰富而生动的素材,更使我接近了真实——灾难中人的真实的内心世界和“南京大屠杀”悲剧历史的真实。
那段时间,我沉浸在创作的激动和亢奋中。因为每采访一位老人,都有使我悲愤、使我惊喜的故事。生活就是如此复杂而丰富,这种复杂而丰富的故事是任何作家都想象不出来的!好几次我曾暗暗发誓:这本书一定要写好。写不好,我将愧对这些老人,我将愧对历史,我将扔掉这支笔!
铺开稿纸,如何下笔呢?我再三思量,决定突出一个字:真。我要把侵华日军的暴行和三十万人的冤恨留给历史,留给后人。只有真实,才称得上是历史。只有真实,才能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只有真实,才对得起先人和故人!
对作家来说,讲真话是一种人格,一种良知,也是一种责任。
作为纪实文学,它是事实的再现,它是活的历史。
感谢生活为我提供大量真实生动的素材,感谢当今这个开放的时代给了我一个说真话的机会。
于是,我放开手脚,秉笔直书。我要突破时间和空间的局限:五十年,一百年后,还可能有人读这本书。白皮肤、黑皮肤和黄皮肤的人,都能从这本书中找到共同的话题。
于是,我举起了正义和人道的旗帜。正义和人道是全人类的旗帜。
面对二十万言的这本书,我感到问心无愧。因为,我努力按照历史的真实还原给了历史。书中所记之事,所写之人,都有史可查,有据可依,连接受我采访的幸存者们的姓名、年龄、职业,甚至门牌号码都提供给了读者。我觉得,纪实文学的审美意义在于“真实”这两个字。对于有责任感的作家来说,“真实”这两个字,不仅仅是一种职业的道德,它还是一种人格——对历史的尊重和对读者的尊重的文人的品格。
读者是上帝。这本血泪铸成的痛史第一次印刷的五万册立即销完,当月又加印十万册,十万册也很快脱销。部队、工厂、学校组织的读书活动常把《南京大屠杀》列入必读书目,北京和上海的中学生还把它作为课外读物。不久,香港、台湾、美国、日本等地纷纷出版转载,海内外报刊多有好评,读者来信似雪片飞来。我感到了一个作家的使命与责任。
《南京大屠杀》被评为《昆仑》文学奖和由《解放军报》组织评选的军版图书一等奖,接着,又被评为第二届全国图书金钥匙奖。
这是鼓励,我将继续努力。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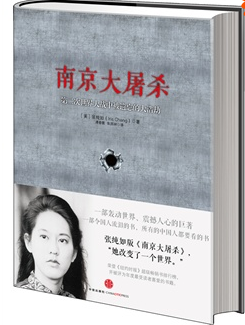 作者:张纯如(现代)
作者:张纯如(现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