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世界 第一部分
旅行(1)
1828年9月,这位国内最伟大的数学家多年来首次离开家乡,赴柏林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他本人当然不想去,拒绝了好几个月,但亚历山大·封·洪堡态度坚决,最后他一时心软,答应了,可内心里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高斯还躲在被窝里。当妻子明娜来叫他起床,说马车已备好、路程遥远时,他抱紧枕头,闭起眼睛,想让她离开。当他重新睁开眼,看到明娜还站在那里时,他讲她烦人,愚蠢,是他将来的灾星。由于这也没用,他只能掀开被子起床。他勉强洗漱了一下,怒冲冲地走下台阶。他的儿子欧根已经收拾好旅行包等在客厅里。高斯一见他就怒火中烧:他抡拳跺脚,砸碎了窗台上的一只罐儿。欧根和明娜分别将手搭在他的两肩上,保证他会得到好好的照顾,事情会像噩梦一样迅速结束,他很快又会回家来。但这样也无法让他安静下来。直到他的老母亲被喧哗吵醒、走出房间、捏住他的脸颊、问她从前的乖儿子哪儿去了时,他才平静下来。他冷淡地告别明娜和他的女儿,失神地摸摸小儿子的头,然后让人扶上马车。旅程难熬。他骂欧根是个没用的东西,拿走他的有节手杖,使劲捅他的脚。他蹙额望了会儿窗外,然后问欧根:他的姐姐到底啥时候嫁人,为什么没人娶她,问题在哪里?欧根向后抹一抹长发,双手捏着红帽子,不想回答。讲啊,高斯说道。老实说,欧根说道,姐姐不漂亮。高斯点点头,他觉得这答案可信。他向欧根索要一本书。欧根将自己刚打开的那本书递给他:弗里德利希·雅恩生于1778年,卒于1852年,德国教育家和政治家,德国体操运动之父,学生社团的先驱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的《德国体操艺术》。这是欧根最喜欢的图书之一。高斯读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抱怨马车的新式皮弹簧,说它让人比从前更难受。他声称有一种机器很快就会发明出来,以出膛子弹的速度将人们从一座城市运往另一座城市。到时候从哥廷根到柏林半小时就够了。欧根怀疑地摇摇头。某人在某个时间出生,不管他愿不愿意,都无法逃脱,高斯说道,这是多么奇怪和不公啊!这真是可怜的生存偶然性的一个好例子。命运让人在过去面前具有一种不恰当的优势,同时又让人成为未来的小丑。欧根困倦地点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或在奥里诺托河畔,高斯说道,就连他这样的人的智商都将一事无成。相反,两百年后,每个傻瓜都会取笑他,杜撰出有关他的无稽之谈来。他沉思着,又说了一回欧根是个没用的东西,埋头看起书来。在他阅读时,欧根使劲望着窗外,掩饰他因受辱和愤怒而扭歪了的脸。《德国体操艺术》介绍的是体操设施。作者详细介绍了他设计的可供人们在上面翻爬的器材。他将一种取名鞍马,另一种取名平衡木,还有一个取名山羊。这家伙疯了,高斯说道,打开窗户,将书扔了出去。欧根忙叫那是他的书。是疯了,高斯说道,合上眼睛睡着了。直到傍晚在边境上换马都没有醒过来。当换去旧马、套上新马后,他们坐在一家饭馆里吃土豆汤。店里除了他们只有一位客人,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的瘦子从邻桌悄悄打量着他们。高斯梦到了体操器材,他恼怒地说:身躯可能是所有沮丧的源泉,像他这种人的精神被关在一个孱弱的身躯里,而欧根这样的庸人却几乎从不生病,他一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典型的恶意幽默。欧根说他小时候患过严重的天花。他险些就活不下来。这里还能看到伤疤!对啊,高斯说道,他将这事忘了。他指指窗外的驿马说:富人旅行花的时间是穷人的双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嘲讽。谁使用驿站的马匹,可以每到一站就更换。谁使用自己的马,就得等它们体力恢复过来。欧根问那又怎么样。当然,高斯说道,一个不习惯思考的人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年轻人带手杖而老年人不带一样。大学生带有节手杖,欧根说道,一直就是这样的,这种风气还将保留下去。有可能,高斯微笑着说道。他们默默地喝汤,直到边防站宪兵走进来,要求他们出示护照。欧根递给宪兵他的通行证件:宫廷证书,证明他虽然是名大学生,但没有危险,可以陪父亲进入普鲁士。宪兵怀疑地打量他,查看护照,点点头,转向高斯。他啥都没有。连护照都没有?宪兵意外地问道,没有证明,没有印戳,啥都没有?高斯说他从没有需要过这种东西。他最后一次跨越汉诺威边境是在二十年前,当时他未曾碰上过麻烦。欧根想解释他们是谁、去哪里、又是谁要他们去的。宪兵不想听,他只要看护照。欧根说,自然科学家大会是由国王主持召开的。身为大会贵宾,某种程度上邀请他父亲的是国王。宪兵索要护照。他可能有所不知,欧根说道,他父亲名闻遐迩,备受尊敬,是所有学会的成员,年轻时就被称作数学王子。高斯点点头。据说拿破仑就是因为他而放弃了炮轰哥廷根的。欧根脸色发白。
旅行(2)
拿破仑,宪兵重复道。正是,高斯说道。宪兵提高了一点嗓门继续索要护照。高斯头趴在胳膊上,一动不动。欧根捅捅他,但没有用。高斯嘀咕说他无所谓,他想回家,他根本无所谓。宪兵尴尬地拉拉自己的帽子。这时坐在邻桌的那人出面干涉了。这一切终会结束!德国将变得自由,良民们将自由生活和旅行,身体和精神健康,不再需要证件。宪兵怀疑地要他出示证件。他指的正是这个证件,那人叫道,手伸进口袋里掏摸。突然,他跳起身来,撞翻椅子,冲了出去。宪兵盯着敞开的门愣怔了一阵,才醒悟过来,拔脚追出去。高斯慢慢抬起头来。欧根建议立即赶路。高斯点点头,默默地喝完汤。宪兵的小屋空着,两位警察追赶那位胡子去了。欧根和马车夫合力搬开拦在边境道上的横木,然后他们驶上了普鲁士的国土。高斯这下高兴了,几乎是兴高采烈。他谈微分几何学。他说几乎无法预料通向弯曲空间的道路还会通向哪里。他本人不久前才粗浅地弄懂了,欧根应该为自己的平庸高兴。有时候真让人害怕和胆怯。然后他讲他年轻时的辛酸。他父亲严厉、冷酷,对这一点欧根应该感到幸运。他学会讲话前就开始计算了。有一回父亲在点月薪时点错了,于是他在一旁哭了起来。父亲纠正错误后,他顿时就不哭了。欧根假装深受感动的样子,虽然他知道这故事不是真的,是他哥哥约瑟夫杜撰并传播开来的。父亲一定是听得太频繁了,如今连他自己也开始信以为真了。 高斯讲起偶然——他认为偶然是所有知识的敌人。从近处看,能看到每件事背后无穷的因果奥妙。如果退回得足够远,就会看见大的轮廓。自由和偶然是个中间距离的问题,是桩远近的事情。他理解吗?差不多吧,欧根看看他的怀表,困倦地回答道。它走得不太准,但现在一定是介于凌晨3点半到5点之间。但是,高斯双手按着发痛的腰,接着说道,概率的规则没有说服力。它们不是自然法则,可能出现例外。比如,出现像他这样智商的一名知识分子。无可否认常有笨蛋在赌博时赢到钱。有时他甚至猜测物理学原理也只有统计效果,允许例外:幽灵闪现或思想的传输。欧根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这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着,高斯闭上眼睛,又沉沉睡去。他们于次日傍晚到达柏林。成千上万的小房子,没有中心没有秩序,纯粹是欧洲沼泽最多的地方的一座扩散的住宅区。它刚开始修建宏伟的建筑:一座大教堂,几座宫殿,一座用来展示洪堡的伟大考察结果的文物博物馆。几年之后,欧根说道,这里将成为一座像罗马、巴黎或圣彼得堡一样的大都市。绝对不会,高斯说道。讨厌的城市!马车在很差的沥青路上颠簸。马儿被狗吠惊吓了两次,车轮三次在小道上几乎陷进烂泥里。他们的东道主住在帕克霍夫四号,在市中心,就在新博物馆工地背后。为了避免驶错方向,事先高斯用鹅毛细笔画了张很详细的位置图。一定有人老远就看到了他们,报告了,因为他们刚驶进院子没多久,大门就打开来,四名男子向他们跑过来。亚历山大·封·洪堡是位老先生,个子矮小、头发雪白。他身后跟着一位手拿打开的笔记本的秘书,一位穿着仆役制服的男仆和一名满脸络腮胡、抱着个装有一只木盒子的支架的年轻人。他们好像都演示过似的,摆好姿势。洪堡向马车门伸出双臂。 毫无反应。车内传出急促的话语声。
旅行(3)
不,有人叫道,不!一声闷响,然后是第三次:不!好一阵毫无动静。车门终于打开了,高斯小心翼翼地下来。当洪堡抓住他的肩,大喊不胜荣幸,说这一刻对于德国、科学和对于他本人是多么伟大的瞬间时,他吓得直后退。秘书记录,木盒子后面的那人低声叫道:准备!洪堡凝固了。这位是达盖尔先生,他嘴唇未动地低语道,是他的一位被保护人,他摆弄那台仪器,将瞬间摄录在一层感光的碘化银上,把这一刻从稍纵即逝的时间那里救出。请千万别动!高斯说他想回家。一会儿就好,洪堡低语道,十五分钟左右。已经相当进步了,不久前时间要长得多,最初试验时他认为他的背会受不了。高斯想挣脱,可那位小老头力气惊人地抓紧他,咕哝道:去报告国王!仆人一听就跑走了。然后,可能是因为他脑子里刚好想到了:请记录,检查在瓦奈门德养殖海豹的可能性,条件似乎有利,明天向我报告!秘书记录。直到这时欧根才一瘸一拐地跨下马车,为他们到得这么晚表示道歉。 这里没有什么早或晚的,洪堡含糊地说道。这里只有工作,会干完的。幸好还有灯光。别动!一名警察走进大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洪堡抿紧嘴唇低声叫等等,他会解释一切的!警察说没什么好解释的,这是聚众闹事。他们要么立即散开,要么他就公事公办。洪堡说他是宫廷总管。什么?警察向前侧过身来。宫廷总管,洪堡的秘书重复道。宫廷成员。摄像的达盖尔要求警察从取景框中消失。警察皱着眉退回去。第一,他说,人人都可以这么讲,第二,禁止集会适用于所有人。那一位,他指着欧根,显然是个大学生。这事会特别棘手。秘书说,他要是不立即离开,就会遇上他自己意想不到的麻烦。你不能这样对一位官员讲话,警察犹豫地说,他给他们五分钟时间。这可能会成为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洪堡抿着嘴唇低声道。高斯呻吟着挣脱开来。哎呀不要动,洪堡叫道。达盖尔直跺脚,这下机会一去不复返了!跟其他所有机会一样,高斯平静地说道。跟其他所有机会一样。果然:当天夜里,当高斯在隔壁房间大声打鼾,大得整座房子都能听到时,洪堡用显微镜检查曝光的铜板,他在上面什么都认不出来。好一阵之后他才感觉从中看出了一团貌似幽灵的混乱轮廓,某种像水下风景似的朦胧画图。中间有一只手,三只鞋,一个肩,一件制服卷起的衣袖和一只耳朵的下部。真是这样吗?他叹息着将那块板扔出窗外,听到它“嗵”一声落在大院的地面上,转眼就将它忘记了,就像忘记他没能做成的一切一样。
旅行(1)
1828年9月,这位国内最伟大的数学家多年来首次离开家乡,赴柏林参加德国自然科学家大会。他本人当然不想去,拒绝了好几个月,但亚历山大·封·洪堡态度坚决,最后他一时心软,答应了,可内心里希望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高斯还躲在被窝里。当妻子明娜来叫他起床,说马车已备好、路程遥远时,他抱紧枕头,闭起眼睛,想让她离开。当他重新睁开眼,看到明娜还站在那里时,他讲她烦人,愚蠢,是他将来的灾星。由于这也没用,他只能掀开被子起床。他勉强洗漱了一下,怒冲冲地走下台阶。他的儿子欧根已经收拾好旅行包等在客厅里。高斯一见他就怒火中烧:他抡拳跺脚,砸碎了窗台上的一只罐儿。欧根和明娜分别将手搭在他的两肩上,保证他会得到好好的照顾,事情会像噩梦一样迅速结束,他很快又会回家来。但这样也无法让他安静下来。直到他的老母亲被喧哗吵醒、走出房间、捏住他的脸颊、问她从前的乖儿子哪儿去了时,他才平静下来。他冷淡地告别明娜和他的女儿,失神地摸摸小儿子的头,然后让人扶上马车。旅程难熬。他骂欧根是个没用的东西,拿走他的有节手杖,使劲捅他的脚。他蹙额望了会儿窗外,然后问欧根:他的姐姐到底啥时候嫁人,为什么没人娶她,问题在哪里?欧根向后抹一抹长发,双手捏着红帽子,不想回答。讲啊,高斯说道。老实说,欧根说道,姐姐不漂亮。高斯点点头,他觉得这答案可信。他向欧根索要一本书。欧根将自己刚打开的那本书递给他:弗里德利希·雅恩生于1778年,卒于1852年,德国教育家和政治家,德国体操运动之父,学生社团的先驱者,1848年为法兰克福议会议员。的《德国体操艺术》。这是欧根最喜欢的图书之一。高斯读了一会儿又抬起头来,抱怨马车的新式皮弹簧,说它让人比从前更难受。他声称有一种机器很快就会发明出来,以出膛子弹的速度将人们从一座城市运往另一座城市。到时候从哥廷根到柏林半小时就够了。欧根怀疑地摇摇头。某人在某个时间出生,不管他愿不愿意,都无法逃脱,高斯说道,这是多么奇怪和不公啊!这真是可怜的生存偶然性的一个好例子。命运让人在过去面前具有一种不恰当的优势,同时又让人成为未来的小丑。欧根困倦地点头。在人类历史的早期或在奥里诺托河畔,高斯说道,就连他这样的人的智商都将一事无成。相反,两百年后,每个傻瓜都会取笑他,杜撰出有关他的无稽之谈来。他沉思着,又说了一回欧根是个没用的东西,埋头看起书来。在他阅读时,欧根使劲望着窗外,掩饰他因受辱和愤怒而扭歪了的脸。《德国体操艺术》介绍的是体操设施。作者详细介绍了他设计的可供人们在上面翻爬的器材。他将一种取名鞍马,另一种取名平衡木,还有一个取名山羊。这家伙疯了,高斯说道,打开窗户,将书扔了出去。欧根忙叫那是他的书。是疯了,高斯说道,合上眼睛睡着了。直到傍晚在边境上换马都没有醒过来。当换去旧马、套上新马后,他们坐在一家饭馆里吃土豆汤。店里除了他们只有一位客人,一个胡子很长、眼窝深陷的瘦子从邻桌悄悄打量着他们。高斯梦到了体操器材,他恼怒地说:身躯可能是所有沮丧的源泉,像他这种人的精神被关在一个孱弱的身躯里,而欧根这样的庸人却几乎从不生病,他一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典型的恶意幽默。欧根说他小时候患过严重的天花。他险些就活不下来。这里还能看到伤疤!对啊,高斯说道,他将这事忘了。他指指窗外的驿马说:富人旅行花的时间是穷人的双倍,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嘲讽。谁使用驿站的马匹,可以每到一站就更换。谁使用自己的马,就得等它们体力恢复过来。欧根问那又怎么样。当然,高斯说道,一个不习惯思考的人会觉得这是理所当然的。就像年轻人带手杖而老年人不带一样。大学生带有节手杖,欧根说道,一直就是这样的,这种风气还将保留下去。有可能,高斯微笑着说道。他们默默地喝汤,直到边防站宪兵走进来,要求他们出示护照。欧根递给宪兵他的通行证件:宫廷证书,证明他虽然是名大学生,但没有危险,可以陪父亲进入普鲁士。宪兵怀疑地打量他,查看护照,点点头,转向高斯。他啥都没有。连护照都没有?宪兵意外地问道,没有证明,没有印戳,啥都没有?高斯说他从没有需要过这种东西。他最后一次跨越汉诺威边境是在二十年前,当时他未曾碰上过麻烦。欧根想解释他们是谁、去哪里、又是谁要他们去的。宪兵不想听,他只要看护照。欧根说,自然科学家大会是由国王主持召开的。身为大会贵宾,某种程度上邀请他父亲的是国王。宪兵索要护照。他可能有所不知,欧根说道,他父亲名闻遐迩,备受尊敬,是所有学会的成员,年轻时就被称作数学王子。高斯点点头。据说拿破仑就是因为他而放弃了炮轰哥廷根的。欧根脸色发白。
旅行(2)
拿破仑,宪兵重复道。正是,高斯说道。宪兵提高了一点嗓门继续索要护照。高斯头趴在胳膊上,一动不动。欧根捅捅他,但没有用。高斯嘀咕说他无所谓,他想回家,他根本无所谓。宪兵尴尬地拉拉自己的帽子。这时坐在邻桌的那人出面干涉了。这一切终会结束!德国将变得自由,良民们将自由生活和旅行,身体和精神健康,不再需要证件。宪兵怀疑地要他出示证件。他指的正是这个证件,那人叫道,手伸进口袋里掏摸。突然,他跳起身来,撞翻椅子,冲了出去。宪兵盯着敞开的门愣怔了一阵,才醒悟过来,拔脚追出去。高斯慢慢抬起头来。欧根建议立即赶路。高斯点点头,默默地喝完汤。宪兵的小屋空着,两位警察追赶那位胡子去了。欧根和马车夫合力搬开拦在边境道上的横木,然后他们驶上了普鲁士的国土。高斯这下高兴了,几乎是兴高采烈。他谈微分几何学。他说几乎无法预料通向弯曲空间的道路还会通向哪里。他本人不久前才粗浅地弄懂了,欧根应该为自己的平庸高兴。有时候真让人害怕和胆怯。然后他讲他年轻时的辛酸。他父亲严厉、冷酷,对这一点欧根应该感到幸运。他学会讲话前就开始计算了。有一回父亲在点月薪时点错了,于是他在一旁哭了起来。父亲纠正错误后,他顿时就不哭了。欧根假装深受感动的样子,虽然他知道这故事不是真的,是他哥哥约瑟夫杜撰并传播开来的。父亲一定是听得太频繁了,如今连他自己也开始信以为真了。 高斯讲起偶然——他认为偶然是所有知识的敌人。从近处看,能看到每件事背后无穷的因果奥妙。如果退回得足够远,就会看见大的轮廓。自由和偶然是个中间距离的问题,是桩远近的事情。他理解吗?差不多吧,欧根看看他的怀表,困倦地回答道。它走得不太准,但现在一定是介于凌晨3点半到5点之间。但是,高斯双手按着发痛的腰,接着说道,概率的规则没有说服力。它们不是自然法则,可能出现例外。比如,出现像他这样智商的一名知识分子。无可否认常有笨蛋在赌博时赢到钱。有时他甚至猜测物理学原理也只有统计效果,允许例外:幽灵闪现或思想的传输。欧根问他是不是在开玩笑。这他自己也不知道,说着,高斯闭上眼睛,又沉沉睡去。他们于次日傍晚到达柏林。成千上万的小房子,没有中心没有秩序,纯粹是欧洲沼泽最多的地方的一座扩散的住宅区。它刚开始修建宏伟的建筑:一座大教堂,几座宫殿,一座用来展示洪堡的伟大考察结果的文物博物馆。几年之后,欧根说道,这里将成为一座像罗马、巴黎或圣彼得堡一样的大都市。绝对不会,高斯说道。讨厌的城市!马车在很差的沥青路上颠簸。马儿被狗吠惊吓了两次,车轮三次在小道上几乎陷进烂泥里。他们的东道主住在帕克霍夫四号,在市中心,就在新博物馆工地背后。为了避免驶错方向,事先高斯用鹅毛细笔画了张很详细的位置图。一定有人老远就看到了他们,报告了,因为他们刚驶进院子没多久,大门就打开来,四名男子向他们跑过来。亚历山大·封·洪堡是位老先生,个子矮小、头发雪白。他身后跟着一位手拿打开的笔记本的秘书,一位穿着仆役制服的男仆和一名满脸络腮胡、抱着个装有一只木盒子的支架的年轻人。他们好像都演示过似的,摆好姿势。洪堡向马车门伸出双臂。 毫无反应。车内传出急促的话语声。
旅行(3)
不,有人叫道,不!一声闷响,然后是第三次:不!好一阵毫无动静。车门终于打开了,高斯小心翼翼地下来。当洪堡抓住他的肩,大喊不胜荣幸,说这一刻对于德国、科学和对于他本人是多么伟大的瞬间时,他吓得直后退。秘书记录,木盒子后面的那人低声叫道:准备!洪堡凝固了。这位是达盖尔先生,他嘴唇未动地低语道,是他的一位被保护人,他摆弄那台仪器,将瞬间摄录在一层感光的碘化银上,把这一刻从稍纵即逝的时间那里救出。请千万别动!高斯说他想回家。一会儿就好,洪堡低语道,十五分钟左右。已经相当进步了,不久前时间要长得多,最初试验时他认为他的背会受不了。高斯想挣脱,可那位小老头力气惊人地抓紧他,咕哝道:去报告国王!仆人一听就跑走了。然后,可能是因为他脑子里刚好想到了:请记录,检查在瓦奈门德养殖海豹的可能性,条件似乎有利,明天向我报告!秘书记录。直到这时欧根才一瘸一拐地跨下马车,为他们到得这么晚表示道歉。 这里没有什么早或晚的,洪堡含糊地说道。这里只有工作,会干完的。幸好还有灯光。别动!一名警察走进大院,问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洪堡抿紧嘴唇低声叫等等,他会解释一切的!警察说没什么好解释的,这是聚众闹事。他们要么立即散开,要么他就公事公办。洪堡说他是宫廷总管。什么?警察向前侧过身来。宫廷总管,洪堡的秘书重复道。宫廷成员。摄像的达盖尔要求警察从取景框中消失。警察皱着眉退回去。第一,他说,人人都可以这么讲,第二,禁止集会适用于所有人。那一位,他指着欧根,显然是个大学生。这事会特别棘手。秘书说,他要是不立即离开,就会遇上他自己意想不到的麻烦。你不能这样对一位官员讲话,警察犹豫地说,他给他们五分钟时间。这可能会成为一张历史性的照片,洪堡抿着嘴唇低声道。高斯呻吟着挣脱开来。哎呀不要动,洪堡叫道。达盖尔直跺脚,这下机会一去不复返了!跟其他所有机会一样,高斯平静地说道。跟其他所有机会一样。果然:当天夜里,当高斯在隔壁房间大声打鼾,大得整座房子都能听到时,洪堡用显微镜检查曝光的铜板,他在上面什么都认不出来。好一阵之后他才感觉从中看出了一团貌似幽灵的混乱轮廓,某种像水下风景似的朦胧画图。中间有一只手,三只鞋,一个肩,一件制服卷起的衣袖和一只耳朵的下部。真是这样吗?他叹息着将那块板扔出窗外,听到它“嗵”一声落在大院的地面上,转眼就将它忘记了,就像忘记他没能做成的一切一样。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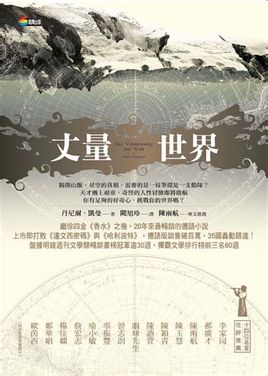 作者:丹尼尔‧凯曼(德)
作者:丹尼尔‧凯曼(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