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方山水
遊山玩水,於我固為探奇,也為延時消日徜徉不歸。愈得專心於形勢之奇風土之美,愈得流連忘返,將人事肩擔之愧索性拋卻。
十五年前登華山,由下至上,只一條路,“上者皆所由陟,更別無路”(酈道元語),級級攀高,促人直上峰頂。即“青柯坪”,亦狹窄不適盤桓,而千尺幢、百尺峽、蒼龍嶺皆是手扶鐵索速過之險徑,及抵峰頂,方得極目四望,令人心曠神怡,渭北樹、日暮雲,泛收眼下。
夜宿改自舊日石砌道觀之客棧,初秋天氣,寒不可當,倘院中賞月,如何可也?回想來路,並無村家聚落,也無曲溪回穀,有的只是石磴梯道及飛崖洞穴,於是知登華山純實崇高清旅也,斷非“言師采藥去”而你徘徊亭橋悠然林泉竟日不去的幽勝山谷也。
這種古畫中的山谷究在何處?
範寬《溪山行旅圖》的山水究在何處?他籍貫華原,是離西安北面不遠的耀縣,以耀州瓷名;郭熙《林泉高致》一書謂:“關陝之士,惟摹範寬。”或許範寬的山水正是關陝寫照。關陝風景之大者,終南、太華也。米芾謂:“範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這深暗晦暝,想必在大山深谷極幽處,似很符合秦嶺山脈中的終南山。而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言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這雪月徘徊,看來不易是華山。
世界山水,全有可看可歎者;然峰欲奇突、岫欲出雲、巒欲起伏、溪欲狹曲、松欲蟠蟠、橋欲孤短、樵欲匆過、屋軒欲偏小藏山側、瀧欲細練掩于深谷等古畫中山水,看來只能在中國求之。
十六年前因事道經河北保定去到完縣、唐縣一段之太行山,山雖不高,層層連綿不盡,土崗濯濯,間有樹點如畫中皴。偶有孔道,北方所謂峪也。可惜匆匆一停,不能多探太行山水之面貌,卻也不禁疑惑這南北綿延千里的山脈竟全是如此黃土漠漠嗎?
應當未必。須知古代曾有一段時間,北嶽並不設在我人素知的山西渾源之恒山,而設在唐縣南邊幾十裏的曲陽,亦處太行山脈中。既為五嶽之一,必為群山環拱,豈能如今日所見之勢?並且同行土著全不提一字,想來他們也不知道。返台後讀清人李雲麟一百多年前之《遊北嶽記》,他也說由保定向西“遍詢土人及士大夫,迄無知者”。搞不好這曲陽北嶽今日已荒湮了也不一定。
但看古人備稱清幽絕勝的林慮山,位於河南北方的林縣,亦在太行南脈,郭熙所謂“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李雲麟也遊過,他說在林慮觀黃華瀑時,恨不得見廬山;二年後親見廬山黃崖瀑,“尚不及黃華西簾之奇。始知黃華水簾實為北方第一!”
這林慮山我在古人遊記中多次見到,然今日從未聽人提起,連地圖上也不見標示,大約已不堪如古人文中所敘之幽美矣。頗思近日一去探看。
許多古時山水,今日已見不著,如“相看兩不厭”的敬亭山,今日全非昔日謝眺、李白、王思任所見景狀。何也?江河改道、水蘊不足,戰亂砍伐、土木蕩失、人煙耕種、文明洗刷………足使幽荒不存。且看一本《水經注》,歷代無數繼注者皆說出地貌遷變之無常與倏忽也。
敬亭山如今只測得324公尺,土頹山降矣。南麓的“雙塔寺”是惟一勝景,毫無遊人,靜可聞針落。無殿無廡,僅孤立宋時雙塔,亦可稱奇。山南的宣城,已無“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之致,乃它原來便不深蕪幽莽,維不了千年奇秀。城中心的開元寺塔,一樓還住著人家,燒飯炒菜可聞。
也曾溯富春江而上,抵建德,再穿千島湖,溯新安江,抵黃山腳下的深渡。這富春江兩岸草粗樹蓊,加以水滿不顯洲汀,全不是黃公望畫中瀟散磊遠景意。這卻又是上源水庫豐沛所造成之今古差異了。
大體言之,昔日之勝,往往今日淡頹平曠;而今日之奇景,常是昔日幽莽不堪攀探者。如黃山,如雁蕩,如桂林陽朔之奇峰如亂馬。甚或如張家界、九寨溝、神農架這等深之又深絕境。
倘要覓既非全然人跡罕至的洪荒古莽如神農架,又非平矮無奇的今日敬亭山,那樣一處山水,可以徜徉忘歸,可以盤桓經年,甚而可以終老一生,不知何處覓得?
流浪的藝術
純粹的流浪。即使有能花的錢,也不花。
享受走路。一天走十哩路,不論是森林中的小徑或是紐約摩天樓環繞下的商業大道。不讓自己輕易就走累;這指的是:姿勢端直,輕步松肩,一邊看令人激動的景,卻一邊呼吸平勻,不讓自己高興得加倍使身體累乏。並且,正確的走姿,腳不會沒事起泡。
要能簡約自己每一樣行動。不多吃,有的甚至只吃水果及幹糧。吃飯,往往是走路生活中的一個大休息。其余的小休息,或者是站在街角不動,三五分鐘。或者是坐在地上。能適應這種方式的走路,那麼扎實的旅行或流浪,才得真的實現。會走路的旅行者,不輕易流汗(" Never let them see you sweat!"),不常吵著要喝水,即使常坐地上、臺階、板凳,褲子也不臟。常能在較累時、較需要一個大的 break時,剛好也正是他該吃飯的時候。
走路是所有旅行形式中最本質的一項。沙漠駝隊,也必須不時下得坐騎,牽著而行。你即使開車,進入一個小鎮,在主街及旁街上稍繞了三四條後,你仍要把車停好,下車來走。以步行的韻律來觀看市景。若只走二十分鐘,而又想把這小鎮的鎮中心弄清楚,你至少要能走橫的直的加起來約十條街,也就是說,每條街只有兩分鐘讓你瀏覽。
走路。走一陣,停下來,站定不動,抬頭看。再退後幾步,再抬頭,這時或許看得較清楚些。有時你必須走近幾步,踏上某個高臺,踮起腳,瞇起眼,如此才瞧個清楚。有時必須蹲下來,用手將某片樹葉移近來看。有時甚至必須伏倒,使你能取到你要的攝影畫面。
流浪要用盡你能用盡的所有姿勢。
走路的停止,是為站立。什麼也不做,只是站著。往往最驚異獨絕、最壯闊奔騰、最幽清無倫的景況,教人只是兀立以對。這種流浪的藝術站立是立于天地之間。太多人終其一世不曾有此立于天地間之感受,其實何曾難了?局促市廛多致蒙蔽而已。惟在旅途迢遙、筋骨勞頓、萬念俱簡之後于空曠荒遼中恰能得之。
我人今日甚少兀兀的站立街頭、站立路邊、站立城市中任何一地,乃我們深受人群車陣之慣性籠罩、密不透風,致不敢孤身一人如此若無其事的站立。噫,連簡簡單單的一件站立,也竟做不到矣!此何世也,人不能站。
人能在外站得住,較之居廣廈、臥高、坐正位、行大道豈不更飄灑快活?
古人謂貧而樂,固好;一簞食一瓢飲,固好;然放下這些修身念頭,到外頭走走,到外頭站站,或許于平日心念太多之人,更好。
走路,是人在宇宙最不受任何情境韁鎖、最得自求多福、最是踽踽尊貴的表現情狀。因能走,你就是天王老子。古時行者訪道;我人能走路流浪,亦不遠矣。
有了流浪心念,那麼對于這世界,不多取也不多予。清風明月,時在襟懷,常得遭逢,不必一次全收也。自己睡的空間,只像自己身體一般大,因此睡覺時的翻身,也漸練成幅度有限,最後根本沒有所謂的翻身了。
他的財產,例如他的行李,只扎成緊緊小小的一捆;雖然他不時換幹凈衣襪,但所有的變化,所有的魔術,只在那小小的一捆裏。
最好沒有行李。若有,也不貴重。乘火車一站一站的玩,見這一站景色頗好,說下就下,完全不受行李沉重所拖累。
見這一站景色好得驚世駭俗,好到教你張口咋舌,車停時,自然而然走下車來,步上月臺,如著魔般,而身後火車緩緩移動離站竟也渾然不覺。幾分鐘後恍然想起行李還在座位架上。卻又何失也。乃行李至此直是身外物、而眼前佳景又太緊要也。
于是,路上絕不添買東西。甚至相機、底片皆不帶。
行李,往往是浪遊不能酣暢的最致命原因。譬似遊伴常是長途程及長時間旅行的最大敵人。
乃你會心係于他。豈不聞"關心則亂"?
他也仍能讀書。事實上旅行中讀完四五本厚書的,大有人在。但高明的浪遊者,絕不沉迷于讀書。絕不因為在長途單調的火車上,在舒適的旅館床鋪上,于是大肆讀書。他只"投一瞥",對報紙、對電視、對大部頭的書籍、對字典、甚至對景物,更甚至對這個時代。總之,我們可以假設他有他自己的主體,例如他的"不斷移動"是其主體,任何事能助于此主體的,他做;而任何事不能太和主體相幹的,便不沉淪從事。例如花太長時間停在一個城市或花太多時間寫 postcard或筆記,皆是不合的。
這種流浪,顯然,是冷的藝術。是感情之收斂;是遠離人間煙火,是不求助于親戚、朋友,不求情于其他路人。是寂寞一字不放在心上、文化溫馨不看在眼裏。在這層上,我知道,我還練不出來。
對"累"的正確觀念。不該有文明後常住都市房子裏的那種覺得凡不在室內冷氣、柔軟沙發、熱水洗浴等便利即是累之陳腐念頭。
要令自己不懂什麼是累。要像小孩一樣從沒想過累,只在委實累到垮了便倒頭睡去的那種自然之身體及心理反應。
常常念及累之人,旅途其實只是另一形式給他離開都市去另找一個埋怨的機會。他還是待在家裏好。
即使在自家都市,常常在你面前嘆累的人,遠之宜也。
要平常心的對待身體各部位。譬似屁股,哪兒都能安置;沙發可以,岩石上也可以,石階、樹根、草坡、公園鐵凳皆可以。
要在需要的時機(如累了時)去放下屁股,而不是在好的材質或幹凈的地區去放。當然更不是為找取舒服雅致的可坐處去迢迢奔赴旅行點。
浪遊,常使人話說得少。乃全在異地。甚而是空曠地、荒涼地。
離開家門不正是為了這個嗎?
寂寞,何其奢侈之字。即使在荒遼中,也常極珍貴。
吃飯,最有機會傷壞旅行的灑脫韻律。例如花許多時間的吃,費很多周折去尋吃,吃到一頓令人生氣的飯(侍者的嘴臉、昂貴又難吃的飯),等等。要令充饑一事不致幹擾于你,方是坦蕩旅途。坊間有所謂的"美食之旅";美食,也算旅嗎?吃飯,原是好事;只不應在寬遠行程中求之。美食與旅行,兩者惟能選一。
當你什麼工作皆不想做,或人生每一樁事皆有極大的不情願,在這時刻,你毋寧去流浪。去千山萬水的熬時度日,耗空你的身心,粗礪你的知覺,直到你能自發的甘願的回抵原先的枯燥崗位做你身前之事。
即使你不出門流浪,在此種不情願下,勢必亦在不同工作中流浪。
遊山玩水,於我固為探奇,也為延時消日徜徉不歸。愈得專心於形勢之奇風土之美,愈得流連忘返,將人事肩擔之愧索性拋卻。
十五年前登華山,由下至上,只一條路,“上者皆所由陟,更別無路”(酈道元語),級級攀高,促人直上峰頂。即“青柯坪”,亦狹窄不適盤桓,而千尺幢、百尺峽、蒼龍嶺皆是手扶鐵索速過之險徑,及抵峰頂,方得極目四望,令人心曠神怡,渭北樹、日暮雲,泛收眼下。
夜宿改自舊日石砌道觀之客棧,初秋天氣,寒不可當,倘院中賞月,如何可也?回想來路,並無村家聚落,也無曲溪回穀,有的只是石磴梯道及飛崖洞穴,於是知登華山純實崇高清旅也,斷非“言師采藥去”而你徘徊亭橋悠然林泉竟日不去的幽勝山谷也。
這種古畫中的山谷究在何處?
範寬《溪山行旅圖》的山水究在何處?他籍貫華原,是離西安北面不遠的耀縣,以耀州瓷名;郭熙《林泉高致》一書謂:“關陝之士,惟摹範寬。”或許範寬的山水正是關陝寫照。關陝風景之大者,終南、太華也。米芾謂:“範寬勢雖雄傑,然深暗如暮夜晦暝”,這深暗晦暝,想必在大山深谷極幽處,似很符合秦嶺山脈中的終南山。而郭若虛的《圖畫見聞志》言范寬“居山林間,常危坐終日,縱目四顧,以求其趣。雖雪月之際,必徘徊凝覽”,這雪月徘徊,看來不易是華山。
世界山水,全有可看可歎者;然峰欲奇突、岫欲出雲、巒欲起伏、溪欲狹曲、松欲蟠蟠、橋欲孤短、樵欲匆過、屋軒欲偏小藏山側、瀧欲細練掩于深谷等古畫中山水,看來只能在中國求之。
十六年前因事道經河北保定去到完縣、唐縣一段之太行山,山雖不高,層層連綿不盡,土崗濯濯,間有樹點如畫中皴。偶有孔道,北方所謂峪也。可惜匆匆一停,不能多探太行山水之面貌,卻也不禁疑惑這南北綿延千里的山脈竟全是如此黃土漠漠嗎?
應當未必。須知古代曾有一段時間,北嶽並不設在我人素知的山西渾源之恒山,而設在唐縣南邊幾十裏的曲陽,亦處太行山脈中。既為五嶽之一,必為群山環拱,豈能如今日所見之勢?並且同行土著全不提一字,想來他們也不知道。返台後讀清人李雲麟一百多年前之《遊北嶽記》,他也說由保定向西“遍詢土人及士大夫,迄無知者”。搞不好這曲陽北嶽今日已荒湮了也不一定。
但看古人備稱清幽絕勝的林慮山,位於河南北方的林縣,亦在太行南脈,郭熙所謂“太行枕華夏,而面目者林慮”,李雲麟也遊過,他說在林慮觀黃華瀑時,恨不得見廬山;二年後親見廬山黃崖瀑,“尚不及黃華西簾之奇。始知黃華水簾實為北方第一!”
這林慮山我在古人遊記中多次見到,然今日從未聽人提起,連地圖上也不見標示,大約已不堪如古人文中所敘之幽美矣。頗思近日一去探看。
許多古時山水,今日已見不著,如“相看兩不厭”的敬亭山,今日全非昔日謝眺、李白、王思任所見景狀。何也?江河改道、水蘊不足,戰亂砍伐、土木蕩失、人煙耕種、文明洗刷………足使幽荒不存。且看一本《水經注》,歷代無數繼注者皆說出地貌遷變之無常與倏忽也。
敬亭山如今只測得324公尺,土頹山降矣。南麓的“雙塔寺”是惟一勝景,毫無遊人,靜可聞針落。無殿無廡,僅孤立宋時雙塔,亦可稱奇。山南的宣城,已無“青山橫北郭,白水繞東城”之致,乃它原來便不深蕪幽莽,維不了千年奇秀。城中心的開元寺塔,一樓還住著人家,燒飯炒菜可聞。
也曾溯富春江而上,抵建德,再穿千島湖,溯新安江,抵黃山腳下的深渡。這富春江兩岸草粗樹蓊,加以水滿不顯洲汀,全不是黃公望畫中瀟散磊遠景意。這卻又是上源水庫豐沛所造成之今古差異了。
大體言之,昔日之勝,往往今日淡頹平曠;而今日之奇景,常是昔日幽莽不堪攀探者。如黃山,如雁蕩,如桂林陽朔之奇峰如亂馬。甚或如張家界、九寨溝、神農架這等深之又深絕境。
倘要覓既非全然人跡罕至的洪荒古莽如神農架,又非平矮無奇的今日敬亭山,那樣一處山水,可以徜徉忘歸,可以盤桓經年,甚而可以終老一生,不知何處覓得?
流浪的藝術
純粹的流浪。即使有能花的錢,也不花。
享受走路。一天走十哩路,不論是森林中的小徑或是紐約摩天樓環繞下的商業大道。不讓自己輕易就走累;這指的是:姿勢端直,輕步松肩,一邊看令人激動的景,卻一邊呼吸平勻,不讓自己高興得加倍使身體累乏。並且,正確的走姿,腳不會沒事起泡。
要能簡約自己每一樣行動。不多吃,有的甚至只吃水果及幹糧。吃飯,往往是走路生活中的一個大休息。其余的小休息,或者是站在街角不動,三五分鐘。或者是坐在地上。能適應這種方式的走路,那麼扎實的旅行或流浪,才得真的實現。會走路的旅行者,不輕易流汗(" Never let them see you sweat!"),不常吵著要喝水,即使常坐地上、臺階、板凳,褲子也不臟。常能在較累時、較需要一個大的 break時,剛好也正是他該吃飯的時候。
走路是所有旅行形式中最本質的一項。沙漠駝隊,也必須不時下得坐騎,牽著而行。你即使開車,進入一個小鎮,在主街及旁街上稍繞了三四條後,你仍要把車停好,下車來走。以步行的韻律來觀看市景。若只走二十分鐘,而又想把這小鎮的鎮中心弄清楚,你至少要能走橫的直的加起來約十條街,也就是說,每條街只有兩分鐘讓你瀏覽。
走路。走一陣,停下來,站定不動,抬頭看。再退後幾步,再抬頭,這時或許看得較清楚些。有時你必須走近幾步,踏上某個高臺,踮起腳,瞇起眼,如此才瞧個清楚。有時必須蹲下來,用手將某片樹葉移近來看。有時甚至必須伏倒,使你能取到你要的攝影畫面。
流浪要用盡你能用盡的所有姿勢。
走路的停止,是為站立。什麼也不做,只是站著。往往最驚異獨絕、最壯闊奔騰、最幽清無倫的景況,教人只是兀立以對。這種流浪的藝術站立是立于天地之間。太多人終其一世不曾有此立于天地間之感受,其實何曾難了?局促市廛多致蒙蔽而已。惟在旅途迢遙、筋骨勞頓、萬念俱簡之後于空曠荒遼中恰能得之。
我人今日甚少兀兀的站立街頭、站立路邊、站立城市中任何一地,乃我們深受人群車陣之慣性籠罩、密不透風,致不敢孤身一人如此若無其事的站立。噫,連簡簡單單的一件站立,也竟做不到矣!此何世也,人不能站。
人能在外站得住,較之居廣廈、臥高、坐正位、行大道豈不更飄灑快活?
古人謂貧而樂,固好;一簞食一瓢飲,固好;然放下這些修身念頭,到外頭走走,到外頭站站,或許于平日心念太多之人,更好。
走路,是人在宇宙最不受任何情境韁鎖、最得自求多福、最是踽踽尊貴的表現情狀。因能走,你就是天王老子。古時行者訪道;我人能走路流浪,亦不遠矣。
有了流浪心念,那麼對于這世界,不多取也不多予。清風明月,時在襟懷,常得遭逢,不必一次全收也。自己睡的空間,只像自己身體一般大,因此睡覺時的翻身,也漸練成幅度有限,最後根本沒有所謂的翻身了。
他的財產,例如他的行李,只扎成緊緊小小的一捆;雖然他不時換幹凈衣襪,但所有的變化,所有的魔術,只在那小小的一捆裏。
最好沒有行李。若有,也不貴重。乘火車一站一站的玩,見這一站景色頗好,說下就下,完全不受行李沉重所拖累。
見這一站景色好得驚世駭俗,好到教你張口咋舌,車停時,自然而然走下車來,步上月臺,如著魔般,而身後火車緩緩移動離站竟也渾然不覺。幾分鐘後恍然想起行李還在座位架上。卻又何失也。乃行李至此直是身外物、而眼前佳景又太緊要也。
于是,路上絕不添買東西。甚至相機、底片皆不帶。
行李,往往是浪遊不能酣暢的最致命原因。譬似遊伴常是長途程及長時間旅行的最大敵人。
乃你會心係于他。豈不聞"關心則亂"?
他也仍能讀書。事實上旅行中讀完四五本厚書的,大有人在。但高明的浪遊者,絕不沉迷于讀書。絕不因為在長途單調的火車上,在舒適的旅館床鋪上,于是大肆讀書。他只"投一瞥",對報紙、對電視、對大部頭的書籍、對字典、甚至對景物,更甚至對這個時代。總之,我們可以假設他有他自己的主體,例如他的"不斷移動"是其主體,任何事能助于此主體的,他做;而任何事不能太和主體相幹的,便不沉淪從事。例如花太長時間停在一個城市或花太多時間寫 postcard或筆記,皆是不合的。
這種流浪,顯然,是冷的藝術。是感情之收斂;是遠離人間煙火,是不求助于親戚、朋友,不求情于其他路人。是寂寞一字不放在心上、文化溫馨不看在眼裏。在這層上,我知道,我還練不出來。
對"累"的正確觀念。不該有文明後常住都市房子裏的那種覺得凡不在室內冷氣、柔軟沙發、熱水洗浴等便利即是累之陳腐念頭。
要令自己不懂什麼是累。要像小孩一樣從沒想過累,只在委實累到垮了便倒頭睡去的那種自然之身體及心理反應。
常常念及累之人,旅途其實只是另一形式給他離開都市去另找一個埋怨的機會。他還是待在家裏好。
即使在自家都市,常常在你面前嘆累的人,遠之宜也。
要平常心的對待身體各部位。譬似屁股,哪兒都能安置;沙發可以,岩石上也可以,石階、樹根、草坡、公園鐵凳皆可以。
要在需要的時機(如累了時)去放下屁股,而不是在好的材質或幹凈的地區去放。當然更不是為找取舒服雅致的可坐處去迢迢奔赴旅行點。
浪遊,常使人話說得少。乃全在異地。甚而是空曠地、荒涼地。
離開家門不正是為了這個嗎?
寂寞,何其奢侈之字。即使在荒遼中,也常極珍貴。
吃飯,最有機會傷壞旅行的灑脫韻律。例如花許多時間的吃,費很多周折去尋吃,吃到一頓令人生氣的飯(侍者的嘴臉、昂貴又難吃的飯),等等。要令充饑一事不致幹擾于你,方是坦蕩旅途。坊間有所謂的"美食之旅";美食,也算旅嗎?吃飯,原是好事;只不應在寬遠行程中求之。美食與旅行,兩者惟能選一。
當你什麼工作皆不想做,或人生每一樁事皆有極大的不情願,在這時刻,你毋寧去流浪。去千山萬水的熬時度日,耗空你的身心,粗礪你的知覺,直到你能自發的甘願的回抵原先的枯燥崗位做你身前之事。
即使你不出門流浪,在此種不情願下,勢必亦在不同工作中流浪。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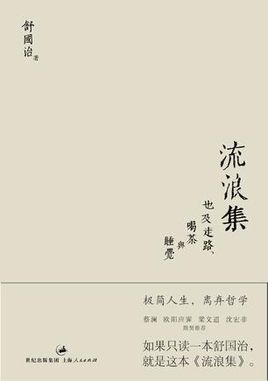 作者:舒国治(当代)
作者:舒国治(当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