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丹尼斯和格雷斯
本书写作的起因可以归到十年之前,当时我是英国谢菲尔德城市理工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在那里,我首次接触到当代欧洲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几位重要的理论家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此外,我的本科专业的兼容性使我得以对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大众传播等各个领域正在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广阔的背景基础上,我开始对语言、特别是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当我在卡本代尔的南依利诺依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受到了鼓励,尽管当时的方向还不很明确。在那里,在诸如斯坦·迪兹(Stan Deetz)、理查德·兰尼根(Richard
Lanigan)和汤姆·佩斯(Tom
Pace)(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们各自或许会把自己称为“诠释论”、“符号学”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等学者的指导下,我把四年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对现象学各种理论的攻读上,试图对语言和意义、体验、现实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看法,在此期间我收获颇多。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使我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特征以及有可能受到压抑的特征,而在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则使我高度意识到与传播研究相连的哲学传统理论。我想,确实可以这样说,本书代表了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探索的结合。因此,尽管本书从表面看来是关于组织传播的理论的,我更愿把它看做是对传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政治的角度对此关系进行审视而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的一篇论文。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很晚才转到组织研究这一方面来的事实即是一个证明。因此或许我可以说,研究重点向组织文化的转移给了我一个对传播-统治关系进行审视的便利而有用的工具。
第一章介绍的是把组织定义为文化所含的意义这一基本问题。意识形成、意义和符号形式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我提出,对组织传播和意义形成的关系的研究只有通过把权力和统治问题在概念上进行结合同化才能实现。我提出,组织意义尽管是在主体间形成的,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作为组织行为深层结构一部分的各种权力旨趣的产物。
第二章发展了上述观点,重点放在旨趣问题和对尤金·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研究成果的批评分析上。近几年来哈贝马斯越来越为传播学者所熟悉,但是他的观点的复杂和难以理解限制了他的传播理论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应用。因此我对他的研究项目做了一个带批判性的总体介绍,然后提出他的关于知识构成的旨趣的理论和普遍语用学理论对组织文化中的传播和统治研究可以提供什么信息。实质上,我想指出的是,他的旨趣理论显示了传播怎样能够起到压抑和解放的作用,以及一个适当的组织形成理论必须对传播和上述两个可能性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检验。
第三章讨论权力问题。我对几个权力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将此观点应用于组织形成过程的可能。根据传统的观点,权力被认为是组织形成的合法产物,而不是被视为压抑和统治手段的重复。因此我提出一个权力统治的观点,其含义是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把某些群体旨趣构建到组织活动中去来进行的。换言之,当由特定的组织旨趣界定组织形成过程时统治即出现了。
组织旨趣赖以构建的手段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同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反对把意识形态视为纯粹表意(即只是由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所构成)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扎根于社会行为者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我把意识形态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社会行为者受到质询(对话),他们对社会世界形成意识的手段得以构成。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在这之中矛盾和统治结构被模糊了,统治群体的特别旨趣被视为是普遍的旨趣,并得到积极支持,甚至包括被压迫群体的支持(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我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是会显露出来的,并主要通过各种推论行为得到表达,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必须明确揭示统治和含义体系之间关系的联系。
第五章继续上述论题,对含义的一种特别形式——组织叙述——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功能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提出,故事讲述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叙述的结构本身大大有助于某些意义形成的维持和再现。当这样的意义形成起到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再现同时却排除其他群体的利益时,于是叙述便在意识形态上发挥了功能。接着我对叙述本身的性质作了分析,并且讨论了这一特别的推论行为为什么不是中性的、简单的信息供应者;相反地,故事讲述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组织现实的再现有重要意义。在把我的理论观点付诸应用时,我举了一个组织故事作例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对此进行分析。尽管对脱离具体情境的一个故事进行分析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认识,即这样的分析对我们对组织传播和组织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
第六章提出了几个前面几章必然会提出的超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发现语言和意义之间是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构成“真理”?顺着罗蒂(Rorty)和伽达默尔(Gadamer)等思想家的思路,我对基要认识论的观点无法苟同,根据这些理论,真理是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同晶型性质而判断的。对真理的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把理论视为不同的话语,每一个都在人类的说话中争取自己的位置。最成功的理论不是依据它们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能力而决定的,而是依据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的程度范围,即使我们投入自我反思、并进而从推论封闭的状态中求得解放。对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的探讨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在理论和权力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最后,第七章通过对解释问题的讨论和对解释行为的有效性问题的分析,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总结。我提出,对无论是小说、电影、故事及其他等等的解释的评价不应该建立在作者的意图、实质的发现或任何其他的基本标准上。一个解释如果探讨的是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存在的分裂现象,那么它的有效性则要强的多。解释行为是一种解构和抵制行为,一个与文本试图强加于人的世界框架斗争的行为。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这一产生意义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和解释行为一样是政治性的。正是通过解释过程我们使得我们的世界有了意义,也正是通过这同一过程我们的社会世界得以再现。因此,意义和解释,统治和话语,是错综复杂,密切相联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数位人士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它是以我在卡本代尔南依利诺依大学在斯坦·迪兹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在过去的七年里,斯坦在我的学业和生活中担当了好几个角色——是导师,又是同事,朋友和知己——而且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和同情。他的思想的清晰和深度,他的坚实有力的指导是对我的鼓舞的源泉。我对理查德·兰尼根和汤姆·佩斯深表感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给了我深邃的洞察力。戈登·中川(Gordon
Nakagawa)和朱莉·威廉姆斯(Julie
Williams)是我的“养父母”,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我的亲密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智慧和情感上的帮助。我要感谢拉特格斯大学传播系各位同事,他们提供的友好气氛激励了本书的写作。最后,我要对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hristi-na
Gonzalez)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深表谢意。
献给我的父亲和母亲丹尼斯和格雷斯
本书写作的起因可以归到十年之前,当时我是英国谢菲尔德城市理工学院的一名本科生。正是在那里,我首次接触到当代欧洲的社会理论,尤其是几位重要的理论家如安东尼奥·葛兰西(Antonio
Gramsci)、路易斯·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和斯图尔特·霍尔(Stuart
Hall)等。此外,我的本科专业的兼容性使我得以对文学批评、社会语言学、心理语言学和大众传播等各个领域正在探讨的主要问题都有所了解。正是在此广阔的背景基础上,我开始对语言、特别是对语言和意义的关系产生了兴趣。
当我在卡本代尔的南依利诺依大学读研究生时,我在这方面的兴趣受到了鼓励,尽管当时的方向还不很明确。在那里,在诸如斯坦·迪兹(Stan Deetz)、理查德·兰尼根(Richard
Lanigan)和汤姆·佩斯(Tom
Pace)(如果一定要说的话,他们各自或许会把自己称为“诠释论”、“符号学”和“存在主义’的现象学家)等学者的指导下,我把四年中的许多时间都花在对现象学各种理论的攻读上,试图对语言和意义、体验、现实等之间的关系形成一种看法,在此期间我收获颇多。我在本科阶段的学习使我意识到了语言的政治特征以及有可能受到压抑的特征,而在研究生阶段的研究则使我高度意识到与传播研究相连的哲学传统理论。我想,确实可以这样说,本书代表了我个人在这两方面的研究探索的结合。因此,尽管本书从表面看来是关于组织传播的理论的,我更愿把它看做是对传播和意义之间的关系以及从政治的角度对此关系进行审视而产生的结果进行探讨的一篇论文。我在研究生学习阶段很晚才转到组织研究这一方面来的事实即是一个证明。因此或许我可以说,研究重点向组织文化的转移给了我一个对传播-统治关系进行审视的便利而有用的工具。
第一章介绍的是把组织定义为文化所含的意义这一基本问题。意识形成、意义和符号形式问题都有所涉及,而且我提出,对组织传播和意义形成的关系的研究只有通过把权力和统治问题在概念上进行结合同化才能实现。我提出,组织意义尽管是在主体间形成的,但并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作为组织行为深层结构一部分的各种权力旨趣的产物。
第二章发展了上述观点,重点放在旨趣问题和对尤金·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的研究成果的批评分析上。近几年来哈贝马斯越来越为传播学者所熟悉,但是他的观点的复杂和难以理解限制了他的传播理论在我们这一领域的应用。因此我对他的研究项目做了一个带批判性的总体介绍,然后提出他的关于知识构成的旨趣的理论和普遍语用学理论对组织文化中的传播和统治研究可以提供什么信息。实质上,我想指出的是,他的旨趣理论显示了传播怎样能够起到压抑和解放的作用,以及一个适当的组织形成理论必须对传播和上述两个可能性之间的联系进行分析检验。
第三章讨论权力问题。我对几个权力观点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将此观点应用于组织形成过程的可能。根据传统的观点,权力被认为是组织形成的合法产物,而不是被视为压抑和统治手段的重复。因此我提出一个权力统治的观点,其含义是权力的行使是通过把某些群体旨趣构建到组织活动中去来进行的。换言之,当由特定的组织旨趣界定组织形成过程时统治即出现了。
组织旨趣赖以构建的手段在第四章进行讨论,同时提出了意识形态的概念。我反对把意识形态视为纯粹表意(即只是由个人的信念和价值观所构成)的看法,我认为它是扎根于社会行为者的日常实践活动中的。我把意识形态视为这样一个过程,在其中社会行为者受到质询(对话),他们对社会世界形成意识的手段得以构成。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形成一种关于世界的意识,在这之中矛盾和统治结构被模糊了,统治群体的特别旨趣被视为是普遍的旨趣,并得到积极支持,甚至包括被压迫群体的支持(葛兰西的“霸权”概念)。我进一步提出,意识形态是会显露出来的,并主要通过各种推论行为得到表达,对意识形态的分析和批判必须明确揭示统治和含义体系之间关系的联系。
第五章继续上述论题,对含义的一种特别形式——组织叙述——在意识形态上发挥功能的方式进行了详细的分析。我提出,故事讲述的行为本身并不具有内在的意识形态属性,而是叙述的结构本身大大有助于某些意义形成的维持和再现。当这样的意义形成起到使某些群体的利益再现同时却排除其他群体的利益时,于是叙述便在意识形态上发挥了功能。接着我对叙述本身的性质作了分析,并且讨论了这一特别的推论行为为什么不是中性的、简单的信息供应者;相反地,故事讲述的行为是一种政治行为,它对组织现实的再现有重要意义。在把我的理论观点付诸应用时,我举了一个组织故事作例子,用意识形态的功能发挥对此进行分析。尽管对脱离具体情境的一个故事进行分析有相当的局限性,但它确实给了我们一个明确的认识,即这样的分析对我们对组织传播和组织意义之间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可以提供怎样的帮助。
第六章提出了几个前面几章必然会提出的超理论问题。如果我们发现语言和意义之间是有问题的话,那么我们怎么知道是什么构成“真理”?顺着罗蒂(Rorty)和伽达默尔(Gadamer)等思想家的思路,我对基要认识论的观点无法苟同,根据这些理论,真理是以语言和现实之间的同晶型性质而判断的。对真理的更有说服力的概念把理论视为不同的话语,每一个都在人类的说话中争取自己的位置。最成功的理论不是依据它们对客观现实的反映能力而决定的,而是依据对我们提出的挑战的程度范围,即使我们投入自我反思、并进而从推论封闭的状态中求得解放。对意识形态和统治问题的探讨要求我们超越传统实证主义社会理论在理论和权力关系问题上的局限性。
最后,第七章通过对解释问题的讨论和对解释行为的有效性问题的分析,我对自己的观点作了总结。我提出,对无论是小说、电影、故事及其他等等的解释的评价不应该建立在作者的意图、实质的发现或任何其他的基本标准上。一个解释如果探讨的是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存在的分裂现象,那么它的有效性则要强的多。解释行为是一种解构和抵制行为,一个与文本试图强加于人的世界框架斗争的行为。读者/听众和文本之间的这一产生意义的辩证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和解释行为一样是政治性的。正是通过解释过程我们使得我们的世界有了意义,也正是通过这同一过程我们的社会世界得以再现。因此,意义和解释,统治和话语,是错综复杂,密切相联的。
本书在写作过程中得到了数位人士的帮助、支持和理解。它是以我在卡本代尔南依利诺依大学在斯坦·迪兹指导下完成的博士论文为基础写成的。在过去的七年里,斯坦在我的学业和生活中担当了好几个角色——是导师,又是同事,朋友和知己——而且在各个方面都给予了支持和同情。他的思想的清晰和深度,他的坚实有力的指导是对我的鼓舞的源泉。我对理查德·兰尼根和汤姆·佩斯深表感激,他们以不同的方式在语言和意义问题上给了我深邃的洞察力。戈登·中川(Gordon
Nakagawa)和朱莉·威廉姆斯(Julie
Williams)是我的“养父母”,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我的亲密朋友,在我需要的时候给了我智慧和情感上的帮助。我要感谢拉特格斯大学传播系各位同事,他们提供的友好气氛激励了本书的写作。最后,我要对克里斯蒂娜·冈萨雷斯(Christi-na
Gonzalez)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给予我的爱和支持深表谢意。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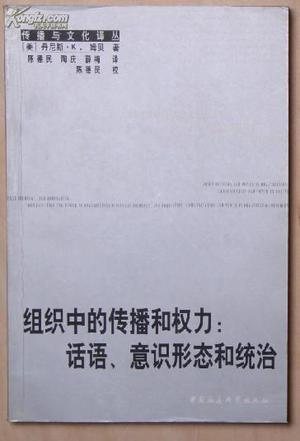 作者:丹尼斯·姆贝(英)
作者:丹尼斯·姆贝(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