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写的是癌症的历史,讲述了一种古老疾病的变迁——它曾经是私密的、需要小声说出的疾病;后来,它变形成一种致命的、形式多变的实体,具有强烈的隐喻性,并且在医学、科学和政治方面具有强大的穿透力,以至于癌症往往被描述为“我们这一代的典型瘟疫”。这本书定名为癌症的“传记”,是名副其实的。我试图进入这种“永生的疾病”的头脑深处,去理解其人格、祛除其行为的神秘色彩。但是,我的终极目的,是提出一个超越“传记”本身的问题:在未来,癌症有可能终结吗?是否可能从我们的体内和社会中,彻底根除这种疾病?
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而超越于这种生物学共性,它们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主题,贯穿于癌症的几种化身形式——这表明了对它们进行统一性的论述,乃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考虑每一种癌症变形的故事,但是,我试图强调贯穿于这4000年历史的大主题。
很明显,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它始于一件不起眼的工作。2003年夏天,我完成了住院医生的医学实习和癌症免疫学方面的研习员工作,开始了在波士顿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与麻省总医院的癌症医学(内科肿瘤学)的高级培训。刚开始,我打算从癌症治疗的实战观点出发,为那一年写部癌症医疗日志。但是,这一追求很快就扩大成了一次广袤的探索之旅,不但把我深深地引入了相关的科学和医学世界,也包括文化、历史、文学和政治领域,跨入了癌症的过去和未来。
有两个人物,站在我们故事的中心。他们两个是同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美国战后科技大繁荣的产儿。他们犹如被催眠了一般,陷入旋涡,执迷地追求,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抗癌战争”。第一个人是“现代化学疗法之父”——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他偶然地发现,维生素的一种类似物是强大的抗癌化学制品,于是他梦想能够找到一种治愈所有癌症的药物。第二个人是曼哈顿的社会名流玛丽·拉斯克(Mary·Lasker),她具有传奇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她加入了法伯的旅程,一起走了几十年。在4000年来的抗癌战斗中,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贡献了勇气、想象力、发明创造和乐观精神——法伯和拉斯克,仅仅是他们中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军事史——但敌人无影无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里同样有胜利与失败、有连绵的战役、有英雄人物也有傲慢之徒、有劫后余生也有旧病复发;并且不可避免地,有人受伤、有人被诅咒、有人被遗忘、有人死亡。最终,癌症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像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我要发布一条“免责声明”:在科学与医学中,一项发现的权威具有极其重大的分量,只有科学家和研究者才可以授予发明人或者发现者这样的“王冠”。虽然在本书中有许多关于发现和发明的故事,但是这些都不能在法律上确立某一项发现或发明的主张权。
这本书的创作极大地依靠了相关的书籍、研究、期刊论文、回忆录和采访;同样,个人、图书馆、藏品、档案和论文也为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在本书的结尾处,都有文字致谢。
但是,有一项鸣谢却不能放在最后。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癌症过往的探访之旅,也是我作为癌症研究者的个人“成年之旅”。而如果没有那些病人,这第二段旅程也是不可能成行的。他们,超越了所有的贡献者;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教导我、启发我。我永远都欠他们一份情、一笔债。
这笔债是名副其实的。本书既要讲述这其中的故事,又要保护这些病人的隐私和尊严——这是一大挑战。在疾病的情况已经为公众所知的例子中(比如之前有过采访或文章报道),我用的是真实姓名。在疾病的情况尚不为公众所知,或受访者要求保护隐私的情况下,我使用了化名,并且故意混淆了他们的身份,让人们不能去追踪他们。不过,他们都是真实的病人和真正的遭遇者。我促请我所有的读者,尊重他们的身份、保持应有的界限。
引子
癌症起于人,亦止于人。科学的抽象概念,有时候可能会使人忘记这样一项基本的事实——医生治疾,但也治人。而有时候,他们职业的这一前提,会同时把他们往两个方向推。
——古德·菲尔德(June·Good·field)
2004年5月19日上午,在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维奇(Ipswich),卡拉·里德(Carla·Reed)从头痛中醒来。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30岁,幼儿园老师。她后来回忆,“那不是普通的头痛,而是脑袋的一种麻木。这种麻木立即告诉你,发生了某种可怕的疾病”。
这种可怕的疾痛,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4月下旬,卡拉发现了背部的少量瘀伤。它们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像奇怪的皮肤红斑,在后来的一个月中,扩大,然后消失,在她的背上留下了地图一样的瘢痕。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她的牙龈开始渐渐地变白。卡拉曾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活泼女子,习惯于每天花几个小时和五六岁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追闹。但是,到了5月初,她几乎连走上楼梯都很困难。有些早晨,她精疲力竭,无法站起,只能四肢着地,在自家的走廊里爬行,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她每天要断断续续地睡上12到14个小时,醒来时仍感觉到压倒性的疲惫,只得把自己再拖回到沙发上补觉。
在这四个星期里,卡拉和她的丈夫一共去看了两次全科医生(和护士),但是她每次去医院,都没有进行检查,医生也没有给出任何诊断结果。幽灵般的疼痛在她的骨头上出现,又消失。医生笨拙地摸索了一些解释,也许是偏头痛,并要求卡拉试一试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反而加重了卡拉的白牙龈出血。
卡拉性格开朗、合群、热情洋溢。对于自己疾病的起伏,她感到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担心。她从小到大,未患过重病。医院对她来说,是一个抽象名词;她从来没有看过或咨询过专科医生,更不用说咨询一位肿瘤学家了。她想象和编造了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症状——过度劳累、抑郁、消化不良、神经衰弱、失眠。但是最终,一种本能的意识——一种“第七感”——告诉卡拉,一场急性的灾难,正在她的体内酝酿。
5月19日下午,卡拉把她的三个孩子托付给邻居,然后自己开车再次来到诊所,要求进行验血。医生开单进行常规检查,查她的血球计数。化验师从她的静脉抽出一管血,仔细地看了血的颜色,显然很关注。从卡拉的静脉中抽出的血液泛着水色、苍白,如同稀释过了一样,已经不像血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就是等待,但没有任何消息。第二天早上,卡拉在鱼市接到了电话。
诊所的护士在电话中说:“我们需要再抽一些血。”“我什么时候去?”卡拉一边问,一边盘算着忙碌的一天。她记得自己曾注意过墙上的时钟,一块半磅的鲑鱼鱼排正在她的篮中融化,如果她离开太久,恐怕就会变质了。
最后,一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弥补了卡拉对疾病的回忆:时钟、安排拼车、孩子们、装满苍白血液的试管、没有来得及洗澡、阳光下的鲑鱼、手机里急促的声调。护士说了些什么,卡拉已经大部分都记不得了,似乎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催促。她回忆护士说:“现在就来,现在就来。”
5月21日上午7时许,我听说了卡拉的情况。当时,我正在波士顿,坐在从肯德尔(Kendall)广场到查尔斯街之间飞驰的列车上。我的寻呼机上短信闪烁,隔断的文字冷漠地告诉我,有急诊。“卡拉·里德/白血病新患者/14层楼/到后请速来。”列车冲出幽长的隧道,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玻璃塔楼突然跳进视野,我看到了14楼的房间窗户。
我猜,卡拉正独自坐在其中的一个房间,体验着惊恐与孤独。房间外传来疯狂忙乱的嘈杂声。装有血液的试管,在病房和二楼的实验室之间穿梭。护士带着化验标本奔走,实习医生在为早间报告收集数据,蜂鸣器不停地闪烁,报告、表单被送出来。在医院深处的某个地方,一架显微镜在上下调节,镜头聚焦于卡拉血液中的细胞。
我能相当肯定地感觉到这一切,这是因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到来,会为“医院的脊椎”注入一阵战栗。从楼上的癌症病房,到深埋在地下室的临床实验室,无不随之颤抖。白血病是白细胞发生的癌症——癌症最具爆发性、暴力性的化身之一。病房护士往往会提醒她的患者,得了这种病,“即使是被纸划伤也很危险”。
对于在培训期的肿瘤学家来说,白血病也是一种特殊的癌症化身。它的恶化速度、严重性和无法阻挡的癌细胞扩散程度,往往逼人做出快速、极端的决断。罹患这种疾病非常可怕,观察与治疗这种疾病,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一旦白血病入侵,身体就被推到脆弱的生理极限——体内每一个系统(心脏、肺、血液)的运行,都游走在刀锋边缘。护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做了补充:医生进行的血液检查显示,她的红细胞指标严重不足,不到正常的1/3。她的血液中充斥着数以百万计的恶性白细胞,而不是正常的白细胞——用癌症的术语来说,叫“母细胞”。卡拉的医生,终于跌跌撞撞地做出了正确的诊断,把她送到了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癌症不是一种疾病,而是许多种疾病。我们把它们统称为“癌症”,是因为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特征——细胞的异常增长。而超越于这种生物学共性,它们还具有深刻的文化和政治主题,贯穿于癌症的几种化身形式——这表明了对它们进行统一性的论述,乃是合理的。我们不可能考虑每一种癌症变形的故事,但是,我试图强调贯穿于这4000年历史的大主题。
很明显,这是一项庞大的工程,但它始于一件不起眼的工作。2003年夏天,我完成了住院医生的医学实习和癌症免疫学方面的研习员工作,开始了在波士顿的达纳-法伯癌症研究所与麻省总医院的癌症医学(内科肿瘤学)的高级培训。刚开始,我打算从癌症治疗的实战观点出发,为那一年写部癌症医疗日志。但是,这一追求很快就扩大成了一次广袤的探索之旅,不但把我深深地引入了相关的科学和医学世界,也包括文化、历史、文学和政治领域,跨入了癌症的过去和未来。
有两个人物,站在我们故事的中心。他们两个是同代人,都是理想主义者,都是美国战后科技大繁荣的产儿。他们犹如被催眠了一般,陷入旋涡,执迷地追求,要开展一场全国性的“抗癌战争”。第一个人是“现代化学疗法之父”——西德尼·法伯(Sidney·Farber)。他偶然地发现,维生素的一种类似物是强大的抗癌化学制品,于是他梦想能够找到一种治愈所有癌症的药物。第二个人是曼哈顿的社会名流玛丽·拉斯克(Mary·Lasker),她具有传奇性的社会能量和政治能量;她加入了法伯的旅程,一起走了几十年。在4000年来的抗癌战斗中,一代又一代的男男女女贡献了勇气、想象力、发明创造和乐观精神——法伯和拉斯克,仅仅是他们中的代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一部军事史——但敌人无影无踪,无时无刻、无处不在。这里同样有胜利与失败、有连绵的战役、有英雄人物也有傲慢之徒、有劫后余生也有旧病复发;并且不可避免地,有人受伤、有人被诅咒、有人被遗忘、有人死亡。最终,癌症真实地浮现出来,正像一位19世纪的外科医生曾在一本书的扉页上写下的——众病之王,恐怖之君。
我要发布一条“免责声明”:在科学与医学中,一项发现的权威具有极其重大的分量,只有科学家和研究者才可以授予发明人或者发现者这样的“王冠”。虽然在本书中有许多关于发现和发明的故事,但是这些都不能在法律上确立某一项发现或发明的主张权。
这本书的创作极大地依靠了相关的书籍、研究、期刊论文、回忆录和采访;同样,个人、图书馆、藏品、档案和论文也为本书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些在本书的结尾处,都有文字致谢。
但是,有一项鸣谢却不能放在最后。这本书,并不仅仅是对癌症过往的探访之旅,也是我作为癌症研究者的个人“成年之旅”。而如果没有那些病人,这第二段旅程也是不可能成行的。他们,超越了所有的贡献者;在我的写作过程中,他们不断地教导我、启发我。我永远都欠他们一份情、一笔债。
这笔债是名副其实的。本书既要讲述这其中的故事,又要保护这些病人的隐私和尊严——这是一大挑战。在疾病的情况已经为公众所知的例子中(比如之前有过采访或文章报道),我用的是真实姓名。在疾病的情况尚不为公众所知,或受访者要求保护隐私的情况下,我使用了化名,并且故意混淆了他们的身份,让人们不能去追踪他们。不过,他们都是真实的病人和真正的遭遇者。我促请我所有的读者,尊重他们的身份、保持应有的界限。
引子
癌症起于人,亦止于人。科学的抽象概念,有时候可能会使人忘记这样一项基本的事实——医生治疾,但也治人。而有时候,他们职业的这一前提,会同时把他们往两个方向推。
——古德·菲尔德(June·Good·field)
2004年5月19日上午,在马萨诸塞州的伊普斯维奇(Ipswich),卡拉·里德(Carla·Reed)从头痛中醒来。她是三个孩子的母亲,30岁,幼儿园老师。她后来回忆,“那不是普通的头痛,而是脑袋的一种麻木。这种麻木立即告诉你,发生了某种可怕的疾病”。
这种可怕的疾痛,已经持续了近一个月。4月下旬,卡拉发现了背部的少量瘀伤。它们在某一天的早晨突然出现,像奇怪的皮肤红斑,在后来的一个月中,扩大,然后消失,在她的背上留下了地图一样的瘢痕。几乎在不知不觉中,她的牙龈开始渐渐地变白。卡拉曾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活泼女子,习惯于每天花几个小时和五六岁的孩子们在课堂上追闹。但是,到了5月初,她几乎连走上楼梯都很困难。有些早晨,她精疲力竭,无法站起,只能四肢着地,在自家的走廊里爬行,从一个房间爬到另一个房间。她每天要断断续续地睡上12到14个小时,醒来时仍感觉到压倒性的疲惫,只得把自己再拖回到沙发上补觉。
在这四个星期里,卡拉和她的丈夫一共去看了两次全科医生(和护士),但是她每次去医院,都没有进行检查,医生也没有给出任何诊断结果。幽灵般的疼痛在她的骨头上出现,又消失。医生笨拙地摸索了一些解释,也许是偏头痛,并要求卡拉试一试阿司匹林。但是,阿司匹林反而加重了卡拉的白牙龈出血。
卡拉性格开朗、合群、热情洋溢。对于自己疾病的起伏,她感到更多的是困惑,而不是担心。她从小到大,未患过重病。医院对她来说,是一个抽象名词;她从来没有看过或咨询过专科医生,更不用说咨询一位肿瘤学家了。她想象和编造了各种理由来解释自己的症状——过度劳累、抑郁、消化不良、神经衰弱、失眠。但是最终,一种本能的意识——一种“第七感”——告诉卡拉,一场急性的灾难,正在她的体内酝酿。
5月19日下午,卡拉把她的三个孩子托付给邻居,然后自己开车再次来到诊所,要求进行验血。医生开单进行常规检查,查她的血球计数。化验师从她的静脉抽出一管血,仔细地看了血的颜色,显然很关注。从卡拉的静脉中抽出的血液泛着水色、苍白,如同稀释过了一样,已经不像血了。这一天余下的时间就是等待,但没有任何消息。第二天早上,卡拉在鱼市接到了电话。
诊所的护士在电话中说:“我们需要再抽一些血。”“我什么时候去?”卡拉一边问,一边盘算着忙碌的一天。她记得自己曾注意过墙上的时钟,一块半磅的鲑鱼鱼排正在她的篮中融化,如果她离开太久,恐怕就会变质了。
最后,一些习以为常的细节弥补了卡拉对疾病的回忆:时钟、安排拼车、孩子们、装满苍白血液的试管、没有来得及洗澡、阳光下的鲑鱼、手机里急促的声调。护士说了些什么,卡拉已经大部分都记不得了,似乎只是一般意义上的催促。她回忆护士说:“现在就来,现在就来。”
5月21日上午7时许,我听说了卡拉的情况。当时,我正在波士顿,坐在从肯德尔(Kendall)广场到查尔斯街之间飞驰的列车上。我的寻呼机上短信闪烁,隔断的文字冷漠地告诉我,有急诊。“卡拉·里德/白血病新患者/14层楼/到后请速来。”列车冲出幽长的隧道,马萨诸塞州总医院的玻璃塔楼突然跳进视野,我看到了14楼的房间窗户。
我猜,卡拉正独自坐在其中的一个房间,体验着惊恐与孤独。房间外传来疯狂忙乱的嘈杂声。装有血液的试管,在病房和二楼的实验室之间穿梭。护士带着化验标本奔走,实习医生在为早间报告收集数据,蜂鸣器不停地闪烁,报告、表单被送出来。在医院深处的某个地方,一架显微镜在上下调节,镜头聚焦于卡拉血液中的细胞。
我能相当肯定地感觉到这一切,这是因为,急性白血病患者的到来,会为“医院的脊椎”注入一阵战栗。从楼上的癌症病房,到深埋在地下室的临床实验室,无不随之颤抖。白血病是白细胞发生的癌症——癌症最具爆发性、暴力性的化身之一。病房护士往往会提醒她的患者,得了这种病,“即使是被纸划伤也很危险”。
对于在培训期的肿瘤学家来说,白血病也是一种特殊的癌症化身。它的恶化速度、严重性和无法阻挡的癌细胞扩散程度,往往逼人做出快速、极端的决断。罹患这种疾病非常可怕,观察与治疗这种疾病,也同样令人毛骨悚然。一旦白血病入侵,身体就被推到脆弱的生理极限——体内每一个系统(心脏、肺、血液)的运行,都游走在刀锋边缘。护士把卡拉病例中不清楚的部分向我做了补充:医生进行的血液检查显示,她的红细胞指标严重不足,不到正常的1/3。她的血液中充斥着数以百万计的恶性白细胞,而不是正常的白细胞——用癌症的术语来说,叫“母细胞”。卡拉的医生,终于跌跌撞撞地做出了正确的诊断,把她送到了到马萨诸塞州总医院。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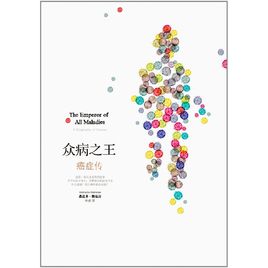 作者:悉达多·穆克吉(美)
作者:悉达多·穆克吉(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