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一个新体制的崛起
多年来我一直心存遗憾,担心自己错过了生命中最宝贵的一次机会。那是在1996年,提供这一宝贵机会的是当时世界最有权力的人物之一: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
江主席在北京中南海与我进行了私人会谈,具体地点就在毛泽东当年的会客室。江主席之所以邀请我是因为我在1982年所写的一本书:《大趋势》。它分析的是美国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变革。该书雄踞《纽约时报》畅销书排行榜两年之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排在第一位,在全球范围内该书的销量也甚佳。《大趋势》一书甚至还进入了中国,令我惊讶的是我得知该书在中国的销量可能达到了2000万册,不过都是盗版,这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现象。文革后成长起来的一代刚刚大学毕业,急切地想要了解西方。"你都不知道你自己在中国名气多么大,"这就是江主席的开场白。
在访问北京之前我还在台北逗留了几天。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的关键期。在中国向台湾水域发射导弹之后,克林顿总统立刻派出航空母舰到达该区域。中美两国在台湾海域的战争一触即发,因此台湾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很快也就成为我们两小时会谈中的话题。从1967年开始,我曾多次访问中国大陆和台湾,亲眼目睹了两边的巨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具有一定的发言权。我觉得对于台湾的良好宣传和中国大陆的低调态度不吐不快,于是说,"江主席,台湾是个小故事,但它讲得很好。大陆有个大故事可讲,可惜讲得很糟。"
江主席沉思了一下说,你为什么不来讲这个故事呢?
尽管这一盛情邀请让我心动不已,但是无法欣然接受。因为当时我正忙于其他事情,而且--由于种种原因--我还没有做好准备。
10年后,这一机遇再次冲我招手,所不同的是,这次的邀请来自中国的商界。那时我正在与一位中国商人王巍录制一期电视节目,王巍是中国首批并购公司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全国工商联并购公会的会长。他曾在纽约学习、工作过一段时间,于1992年回国。在录制节目的间隙,我们很快展开了对中国及其未来的热烈讨论。王巍告诉我,他在1982年就读过《大趋势》,并且受益匪浅。几天后我接到了他的一封电子邮件。
"关于中国的历史、中国的崛起以及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前景的书籍简直是不计其数。但是我们真正需要的是您在《大趋势》一书中所做的那种分析。现在连我们中国人都还无法理清中国纷繁复杂的现状与未来方向。您为什么不探讨一下这个问题,写一本关于中国大趋势的书呢?"
这一次我已经做好了准备,而且还有了一位亲密的伴侣与我一起努力--我的妻子多丽丝。在过去10年中她一直陪伴在我左右,我们也曾多次访问中国。我们共结连理是在2000年,在此之前她是我的德语出版商。事实证明我们真乃天作之合。我们一起环球旅行、一起研究、共同分享目睹中国巨变的喜悦。我们还一起结识了王巍--我们的益友、可靠的合作伙伴。
就在与王巍的第一次会面几个月之后,我们同另外一位中国合伙人一起成立奈斯比特中国研究院。这是一家独立的研究所,得到了南开大学和天津财经大学(我也在这两所大学担任教授)的大力支持。我们的宗旨就是抛开西方人的视角和态度,用中国人的眼光看待中国。正视中国的短处,但是绝不根据我们自己的价值观和标准评价中国。
开始的时候,我们需要搜集大量关于基层的消息,于是与工作人员频繁会面。我们的工作团队由28名来自于天津两所大学的本科生和研究生组成,一些中国企业家和知识分子负责指导。我们简要告诉他们我们所需要的信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他们只负责搜集事实,也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计划、宣言之类的信息。他们最需要习惯的一点就是我们并没有给出一个框架,因为任何框架都会限制研究的方向,那样我们会很难发现新信息。
这一过程对于深受中国思维影响的他们来说非同寻常。而且,他们还需要把从媒体上挑选出来的文章进行整编、翻译。和我们的这个团队一起工作的确是件令人开心的事情,与中国其他地区的学生交流也是如此。
在监测中国地方媒体的同时,我和多丽丝游走于中国各地,采访企业家、知识分子、官员、艺术家,乃至持不同政见者和在华外国人士。我们一直提醒自己,不要像近一时期大多数关于中国书籍的作者一样,以外来者的眼光审视中国。
我们探寻的是中国大趋势。我们明白,自己所关注的是一个区域发展各异、各种变化纷繁复杂的国家。我们所寻找的是一种中国模式,只有把一系列的单一事件放在这个模式中来观察才有意义,并勾勒出一幅新中国的图画,就像1982年我写《大趋势》时对美国所做的分析那样。
但事实证明,我们所了解到的信息的复杂性和重要性远远超出了预期。我们所重点关注的是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生活中的显著变化,但很显然,这些变化的背后有着另外一些更深层次的因素,这些因素影响着这些变化,却令我们难以界定。不过在北京的一天下午,我们恍然大悟,并且惊讶于自己先前的迟钝。1982年美国所发生的变化都是在一个既定的体制内,而2009年中国却在创造一个崭新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体制,它的政治模式也许可以证明资本主义这一所谓的"历史之终结"只不过是人类历史道路的一个阶段而已。。
约翰•奈斯比特
2009年5月
导言
下载地址:
点击下载TXT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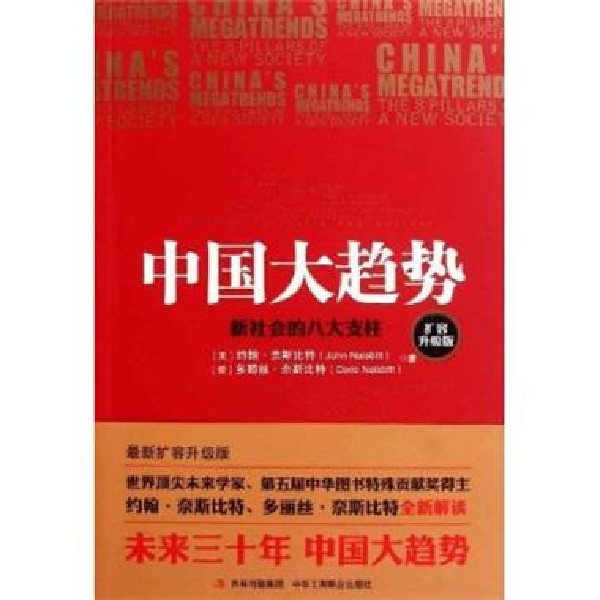 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美)
作者:约翰•奈斯比特(美)